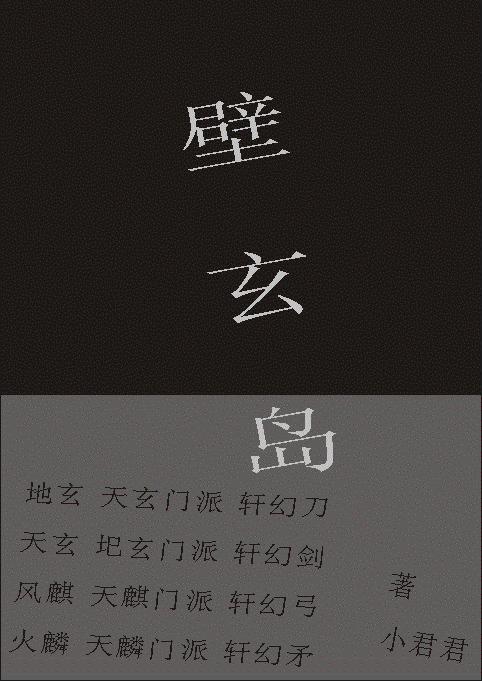记忆的群岛-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记忆的群岛第二部分(2)
在这堵墙与过去之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窗户,而它既不与光线对抗,也不与我的目光相对抗,但经常困扰光线和目光,在被分开之后,光线与目光都开始变得模糊。我经常害怕树全消失了,害怕在我满含信任地透过窗户看的时候,我只能看到毫无差错地画在地面石板上的空空的天空。可它们为什么会消失呢?现在它们既然有了树叶,不再是枯树,还有谁可以决定砍掉它们?我不相信园丁们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做出如斯决定,至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也不相信一个如此野蛮的想法可以出现在一些孩子的脑海中,哪怕是些很不幸的孩子。我最担忧的,还是风。有时,它吹起来之后的力量是令人惊讶的。将枝条弯曲得看不见为止,将它那种焦虑的骚动传染给树叶,让树叶发出一种断断续续的、令人心碎的呻吟声。于是,我努力地去想树木面对外力时那种非常巨大的抗力。我说服自己,即便有一阵旋风将它的力量与水平的空气移动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可以折断一根树的树干,那也不可能有一股旋风可以有足够的能量与覆盖面,可以将它们全部折断。但是,无论我如何推断,每次听到一扇门的碰击声,我就害怕。
是否是这种害怕的经常出现,久而久之地使我的目光变得模糊?一切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的,都那么模糊。我可以确定这一点了。鸟儿与云彩曾让我长时间地怀疑这一点。它们飞快地穿过窗户的空间,从取景中不可预料的一点,到达让人无法预测的下一点。它们就这样不断地出现、消失,其运动是如此的突兀,以至于让我相信,是我意欲抓住它们的目光的缓慢,才使它们显得是模糊的。但这不是真的。早晨我很好地观察了叶子,那时候非常清楚,而且没有风。它们也是模糊的。所以,问题就出在我的目光上,要么是因为它失去了敏锐度,要么就是它已经无法再与光线产生同步。
二、记忆的群岛第二部分(1)
在窗户的视框中出现的世界是模糊的,但从墙壁与它上面的污迹和斑点中出现的世界却一点也不模糊,随着光线而变化。相反,它有时过于锐利,让我感到难受。我会有一种被一队我无法摆脱的人群占据的感觉,而且他们总是毫不顾忌地渐渐占据整个空间。在这队人群中,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独特的、清晰的,我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关注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去探究他的面孔和动作,也无法得到回答,而且动作越来越快,直到产生焦虑。在那种时候,闭上眼睛一点儿也没有用,夜晚的降临同样没有用。必须等待每一个人物的轮廓在目光的注视下渐渐模糊,而这有时需要很长时间。就这样,这群人会慢慢变小,变得苍白,到最后在一种淡红色的雾中消失,伴随着一种弥漫的痛苦,消融掉一切感觉,一切知觉,一切欲望,而之前一直存在我的头脑之中的痛苦越来越充溢,无法遏制,以一种光滑的、原始的、略微发亮的、褐色的、绝望的泥土覆盖住整个空间。
说到底,惟有现时,透过窗户,才是模糊的。每当我的目光固定在过去之上,一切都重新变得清晰。大街,大道,书店,以及那条街的三段,我都可以非常精确地描写它们,还有成为废墟的教堂。我看见它们,虽然是带着那么大的距离,却像它们就在我眼皮底下一样清晰,就在现时中。世界也许对我来说变的,颠倒了,让现时变得不可触及,而让过去马上触手可及。也许我的目光分成了两道,已经对现时厌倦,总是在寻找将要来临的,而这只是一种将来的假象,只是过去的重复。于是,解决我无穷忧虑的办法可能不是窗户,而是墙,而且从此以后,我只能希望,光线来自墙。
我真想将那些总在不停地呢喃、进食的鸽子的脖子砍下。它们可以连续几小时地进食、呢喃,就像是没有调好的、永不疲倦的机器,带着一种顽固、缓慢的愚蠢,让人怀疑欲望,而当它们终于带着一种既巨大又可笑的努力飞起来,好像还是需要好几个小时,遗忘才会起作用,它们那粗俗的呻吟声的痕迹才会消失。我只喜欢那些紧挨着地面、偶尔传来的几声燕子的叫声。它们让夏天、让黄昏充满魔力。它们凝聚了对夏天与黄昏的怀念与自我的释放,成为无序的、希望的结晶体,人的头脑中的汁液需要慢慢地化解。它们在痛苦中产生回声,它们在黑夜中消失,它们穿越黑夜。它们就像是挂在两个白天之间的黑色的线。
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形体足够小、足够快速,可以在运动中成为一个笼统形状的鸟儿才可以被我接受。大的鸟儿,那些可以很容易就看出脑袋、啄、爪子和肚子,尤其是眼睛的,总是显示出一种深深的愚蠢与残酷。它们的目光比其他部位都要可怕,动作急促而断断续续,为它周围的世界带来一种无法探究的恶意和恐惧:在看到它时,我内心的恐惧开始膨胀,直到我皮肤潮湿的极限处,到最后,如果我不做强烈的努力,来摆脱它的空虚,就可以将我也转变为一只惊恐万状的鸟儿,一下子打破时间在我头脑的混杂状态中织起的保护层。必须戳瞎那些大鸟的眼睛,除非可以确定,永远也不与它们的目光相遇,永远不靠近它们;但最能令人放心的,假如有足够的力气与勇气的话,还是戳瞎他们的眼睛。
而鸽子嘛,为了终止它们通过声音来表达自己永不满足的交配欲望的行为,还需要割断它们的嗓子。所以,还不如索性就完全割去它们的脖子。
雨滴从黄昏酝酿风暴的云层里解脱出来,击打在温热的大地上。气味一下子传来。我一直在等待着这种气味,就像是在几小时难受的封闭状态之后的解脱。在那种状态里,有一种确信在渐渐形成,我会在令人晕眩的灰色的铅与蓝色的氧的混合中不可避免地窒息。气味中蕴涵着纯洁的泡沫,在很远的地方,仿佛被密集的斜雨焊接在地面上,通过重复的褶子,上升到天空的无垠之中,有时,还可以让人偶尔看到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过于柔和的蓝色的天空的星状斑点。今晚,在我的梦的轰鸣声中,所有这些色彩都重新回来了。气味通过一条马上就自我封闭上的道路,渗透进了我的房间,在它平淡的宁和中带来被遗忘的欲望,打乱我对虚无与缺失的忍让。风带来的灰土,堆积在窗户角落折起的百叶窗上,它的灰色,以及花粉的黄色,从墙壁的一些锈烂的孔洞中爬出的平平的昆虫的红色与黑色的快速爬动,阳台上的石头,起先还是热得冒烟的,后来又被淋湿了:气味带来了所有这些,将回忆与梦混合在一起,外面的暴雨与里面的睡眠,同时还有那时的期待——一种不明确、却肯定会来的快乐,将要改变对时间的计量,给它带来一个新的源头——,以及现在的期待,只希望时间流逝,与院子中的雨与水一起流走。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记忆的群岛第二部分(2)
暴雨彻底降临时的气味,对我来说,是一个身体的味道,而且,更多的是,在我的无知中,是一个身体所能唤起的最隐私的东西。气味从大地巨大的身体中升起,就像是一种显示,没有任何怀疑、任何潜在的过错可以玷污这一显示,它像一种快乐一样升起,当这种快乐还是未知的,还是没有完成的,雨水将它带来,给人一种奇特的困扰,仿佛可能的欲望与快乐都将延续下去。暴雨在变得激烈的时候伴随着幽暗,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在闪电大量的苍白和轰鸣的消耗之后,自我消融,化为一个没有乌云、绿色的天空。我睡意上来,打着哈欠,脑袋往后倒下。
在这片与它折射出的天空几乎无法区分的灰色、明净、延伸着的地面上,人们在移动,沿着一些看不见的道路。他们好像是在浮动,自己本人不动,僵直地,被他们的脚与倒影联系在一起。远远地,一座很小的钟楼从水中冒出来,为他们指路。但是,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看见它,因为他们的运动,也就是说在我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看到的,使他们离它越来越远。当大海带着它缓慢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升潮,在这些因距离与死水而变得那么小的人们的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被淹没,成为来到这一什么也不存在的地方的奇特欲望的牺牲品?因为不论是天空,还是在地上的倒影,除了有时会有一个钟楼,倾斜的,被人遗忘的,随时都可能倒下的,或者一条章鱼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这里什么也没有。总之,我不记得,在水与房子相接,从而将他们身边的淤泥激活的时候,有任何人在里面游泳。
他们为什么要来?是什么将他们引到了这一沙漠,是出于什么欲望?是否可能,他们是毫无理由地来到的,而能够行动就是为了这个:可以毫无理由地去任何地方,甚至在那里被淹死?
行动,也就是说可以走遍街道形成的沙漠而永不穿越它。于是,它们就不再是些零零星星的线条,显得比时间还要缓慢,而是带着无神目光的匆忙人群,可能还被一道闪电弄瞎了眼睛——但闪电的原因依然没有人知道——,被他们紧紧握在手中的五颜六色的机器弄得昏昏沉沉,而且从机器中出来两根线,伸向他们的耳朵,还钻进去。他们行走其中的城市具有一种思想的形式,只有缓慢的形状才可以被看到、被理解,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总是迷失,根本不在乎。对他们来说,每道光线,每个声音,都只是多了一件事情,没有什么重要性,只是糟粕而已,以至于最后城市消失,而且只能靠一种理性推理而得到重生。我无法知道,这一理性推理运用的是一种新的想象力,抑或只是对失去了的记忆的重新整理。我多次回味这一理性推理中的第一句话,从它清晰的含义中,等待第二句话,然后是第三句,此时又需要重复,它才会带有光明,可以在昏沉中,甚至在睡眠中,找到下面的一句。
要么是一座将两条河流区分开来的空地上的城市,被两排与两条河流形成的角的平分线相平行的街道分割成两个相等的矩形。河流是必需的。它们必须足够宽,免得城市跨越它们。这样,哪怕最小的街道,也有了与树林和草地足够近的地平线。相反,最大的街道一直延伸,没有尽头,而且从不朝向那里,除了朝向自己。必须让人们无法一直到达河岸,不论采用何种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水的温度是那么的高,走向河岸很快就会让人觉得筋疲力尽。但是其他任何逻辑的理由也都是可以的。重要的,而这是很容易就可以明白的,河那边的风景只能分开地、一段一段地被看到,在它们之间留出一些无法看见的地方,让人的脑子可以根据某种延续性与相似性,试着将线条与色彩延伸,进行构造。但是,这样一件对一个监狱中一动不动地透过窗户的铁条看风景的犯人来说非常容易的事情——即使那些铁条非常粗——,在这个城市里成了一种复杂的记忆努力,因为人们永远无法同时看到一段以上,总有一段长长的走路时间在目光中将一段街区与它的两个相邻街区分开来。然而,如果努力地做这样一个尝试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想象一个自然的风景,或者更确切地说,面对面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