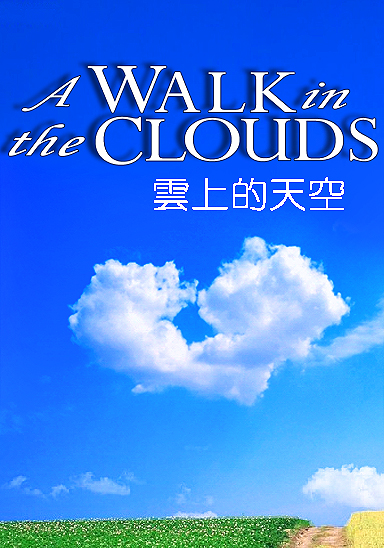天空中下着比风雪更骤的沙-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富裕点了。
1981年,我正读高中,继而读大学,在家呆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每当放星期回到家或放假回到村,刚进套门,喊过一声“妈,我回来啦!”还未落座,母亲就连忙上前探问“娃,饿了吧!妈给你炒馍花去”,而那时的农村生活,炒馍花无疑是又快捷又省事的饭食。
再后来,我的孩子先后出生了。
1995年,我们在城里的事业刚刚起步,儿子仅仅三岁而无人照管,加之岳母刚刚过世,在求助无门的 情况下,只好将儿子送回了老家,母亲沿袭照顾我饮食的方法饲养儿子,于是,炒馍花也成了儿子的最爱。
1996年农历3月初二,女儿哭叫着来到人世间。
母亲在老家临时帮我们将女儿带到一岁三个月。
1997年7月,我们把母亲接来城里住了大半年,主要是照看女儿,那时的母亲,背已经很驮了,她不能抱,只能背着,女儿在母亲似弓的背上睡的很舒服,而一天天长大的女儿也喜欢上了炒馍花。
后来,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在她的一篇习作《品尝幸福》中写道:“你们可不要小瞧我爸爸,他做的最拿手的就是炒馍花。”
她谁成想这道手艺,还是从她奶奶那里流传下来的。
又是一年母亲节。
母亲在十年前的母亲节后被抬进了村东地头。
母亲走啦,带着她的炒馍花的清香走啦!如果她真的在天有灵,她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因为她的儿子传承了她的炒馍花并将其给予了她的后代。
母亲走啦,带着她对孙子孙女的牵挂走啦!如果她真的在天有知,她是不会感到孤独的。
因为我的儿女依然能够品尝到她传承下来悠长的炒馍花。
母亲手中的线断了,但我对母亲的那份怀念和那份牵挂却永远不会断。
5。大舅
我有三个舅舅,时下就数大舅风光。
在村里,大舅的风光仰仗的是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亲表哥。
在厂子,大舅的二儿子、二舅的二儿子和三舅的儿子,凭借的都是大舅长子的提携。
村里人都说:生子当如我表哥。大舅听后心里美滋滋的。
大舅生养了四个孩子,二男二女。现都成家立业,生活宽裕。
大舅比我母亲小五岁,年轻时候家境贫寒,加上儿女们又多,仰仗我父母亲的接济。尽管当时我家里也不富足,但父亲毕竟是公家人,好赖每月还有几十元的收入。
大舅是个吃苦耐劳的人。
1971年,我家在屋后自家的园子里划了块宅基地,准备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座院子。
听我父亲讲,当时大舅负责运输盖房的木料,从50里开外的永济栲栳镇拉上木料,赶着拉木料的马车,来回上百里的路程,待拉回木料,已是后半夜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舅为我家大兴土木确实立下汗马功劳。
大舅是个特别搞笑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年放寒假回到村里,母亲让我去探望大舅。我装了瓶从省城买的老陈醋,外包装跟酒似的,大舅看见外甥看他,心里特别高兴。取出我带给他的礼物,坐在屋里的炕沿上,来不及我细说,打开瓶盖喝了一口,这才发觉味道不对劲,酸的大舅呲牙咧嘴,逗的我心里直发笑。
大舅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我一年到头在省城打拼,平素很少有时间回老家走走。1998年,母亲病逝后,父亲续了玄,大舅念念不忘当年父亲对他的好,每年逢年过节都要亲自登门,拜访探望他的姐夫,且每次都不空着手来。有次,姨姨家里急需几包棉花,大舅让我表哥从河津采购下,并派他二儿子专程送了过来。
父亲常常向我念叨着大舅对他的好。
大舅是个乐善好施的人。
2005年4月,二舅家嫁到张包的大姑娘,比我大一个月的表姐,在运城博爱医院做了个妇科手术,术后须要省肿瘤医院复查。在我准备好住院的前期工作后,大舅动用儿子的社会资源,将二舅、表姐和表姐夫派车亲送省城,他不放心还亲自作陪。
表姐住院第二天,他仍念念不忘老家的亲戚,让我陪他去找找我老姑家的大姑娘,结果两个人在省邮电住宅小区转了一大圈,好不容易打听到老姑家的女婿,我上大学期间特别关照过我,无奈上的二楼,死按门铃,却无人言声,听邻居家的人讲,老俩口溜弯去了。难得老人有这份心情,难得大舅有这份亲情。
尽管探访没有结果。
2007年冬天,大舅妈终因长期患糖尿病,不幸离开了人世间。而此间病倒的好多年,都是大舅手把手照顾着。十几年的辛勤伺候,个中的酸痛苦辣,只有大舅一个人心里清楚。
家里人考虑到我工作忙,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而是事后姨姨家的表弟,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从而错失了与大舅晤面的机会。
过后一个多月,也就是2008年元旦,外甥子娶亲,当舅的披红。在外甥的婚宴上,我见到72岁的大舅,院子里的丝丝寒风中,挡不住我们的温情,我看到大舅明显苍老了许多。我手捧酒杯,斟满白酒,敬酒三杯,算是给他老人家赔个不是,更是抚慰我愧疚的心灵。
大舅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一个让我又牵挂又怀恋,又可亲又可敬,又感激又内疚的人。
6。 姨姨和姨父
阳间厮守,阴间相随。
姨父和姨姨是前后脚走的,俩人告别人世的方式相同,时间相仿,先后相差仅仅三个月零二天。
姨父是临猗县东张镇兴善村人,当地人称此村为过村,意即八仙之一的张果老经过的村子。邻村即为张仙村,传说是张果老出生的地方。
姨姨是同乡的西寺后村人,以区别于卓里乡的东寺后村。至于何年何月何日嫁给姨父,嫁到张家,我早已无从知晓,因为我属于晚辈,姨姨和姨父从没在我面前提及此事,而我更没有亲眼见证他们结婚的喜庆场面。
姨姨和我母亲贼象,言谈举止,行为动作,只要我闭上眼睛,那生动鲜活的形象就会立马浮现。
姨姨和姨父一共抚养了三个孩子。大女儿是从坡上的角杯村抱养的,至今还有往来;二女儿是他们夫妇亲生的,现已另立门户;最小的、唯一的儿子是从中连村抱养的,中间人是我母亲,因为儿女们之间常闹矛盾,姨姨姨父偏袒儿子,这一直成为我母亲心中的痛。
1981年5月,我高考前在预选时不幸落马。
回到村里,心情不佳,重的体力活又干不动,正好赶上姨姨家此时盖房。于是,我骑上自行车独自去了姨姨家。
姨姨家当时修建的是西厢房,在她家的老宅院。从打地基搬砖块开始,到在房屋顶接瓦结束,这一干就是多半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姨姨家的邻居们和盖房子的泥瓦匠都混得非常熟悉。
自打出了学校的门,我还没受过这份苦,待两间新房修缮完毕,我骑车返回家里,在炕头一躺就是一天一夜,这可急坏了母亲,等第二天晌午醒来,母亲特意做了好吃的犒劳我。
后来,我回村里的次数少啦,自然上姨姨家的次数也少啦,但每次回村里,只要时间允许,我总要上姨姨家看看。
2005年清明节前,大约是3月20日,我和妻子一道开车,返家探望父亲,第一天下午到家,看到父亲大人一切安好,我们顿时放下心来,闲聊之中,听三姐说姨父近来常犯病,身体不是很好,我听后心里一沉,连忙与妻商量,决定第二天去姨姨家走走。
翌日下午,三姐、三姐夫、妻子和我一路赶到姨姨家,在二姑娘住的院子里,找见了在偏房椅子上斜坐的姨父,或许是犯病初愈,只见姨父目光呆滞,神志不清,聊会话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待邻居从地里头寻回正下地干活的姨妹,仔细打听才知姨姨去了大姑娘家。
寒暄几句,马不停蹄。我们又驱车赶到冯留村,冯留是个大村子,有好几个自然村。问过之后才找到家里,大姑娘家刚刚重修过正房,人还未搬进居住。在西边侧房里,等见姨姨回来,一番亲切交谈,知道了姨父的病情和她的身体状况。
待我们返至街上停车的地方,姨姨一直相送我们到巷口。当我们黄昏时分离开村子的时候,从汽车的后视镜远看,姨姨伫立在那的背影,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人还未回到省城,电话却打到了老家。
有客户从京都来,催我们快返回受命。
在那个春寒料峭的下午,阳光时隐时现的下午,老天爷让我最后看了姨父和姨姨一眼,谁知那竟成为我们亲人之间的永别。
从老家返城不到半年,三姐的电话里,相继听到了姨父、姨姨下葬的消息。
2005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九,姨父在病魔里过去。
2005年9月17日,农历八月十四,姨姨又在病魔中倒下。
2006年春节,我们一家四口回老家过年。
正月初二,当地习俗为上坟祭祀的日子,为那些死去的亲人们。
三姐、弟弟和我,还有儿子、女儿,抱着对姨姨姨父的挂念,我们匆忙赶赴坟地,大队人马已烧纸回返,顾不上和他们打声招呼。
在冷风嗖嗖的阴阴春日,我匆忙来到坟头,为姨姨和姨父磕了九个响头。
8。 三姐
上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篇《三姐》,20多年过去了,文中的部分内容,我却依然历历在目。
三姐比我年长4岁,育有二女,长大成人。一个在县城做小学老师,一个在省城学医师护理。
三姐在本村读完初中,就回队务了农。在我的记忆里,她那时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无奈,当时时兴推荐上大学,而当老师的父亲,又不大愿意求人,导致三姐再没有继续读书。待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年届17岁的她,却当了3年多农民,没有读过高中的她,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机会。
在生产队里,三姐号称“铁姑娘”,田间的农活,麦场的夏收,都留下了她忙碌的身影,长年的辛勤劳作,风吹雨淋,使一个大姑娘原本细嫩的皮肤变得粗燥,如此的劳动付出,也给她赢得了无数的荣誉称号,并数年担任队里的妇女队长,直到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毕业的我高考落选,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着新的选择:要么继续复读,要么回乡务农。这时,尚未出嫁的三姐,勇敢地站了出来。
记得1982年有天响午,我和三姐在田间除草,炎炎烈日炙烤着我煎熬的心,学业失意的我,就象地里没有浇过水的庄稼——蔫啦。这时,三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搁下农具,促膝交谈。好象就是那一个下午的那一刻,年幼无知的我终于开了心窍。
回到家里,我重拾英语课本,从初中一册开始自学。待9月份开学后,我远赴孙吉中学,踏上了复读之路。10个多月的复读生活是枯燥的,10个多月的复读心情是难熬的,10个多月的复读成绩是增长的,10个多月的复读前途是幸运的。
1983年高考,竟过预选,当我以总分450分,班级第13名的成绩,高出录取分数线30多分,被省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