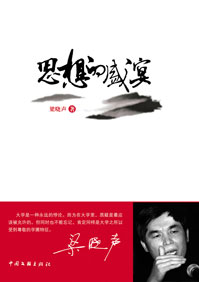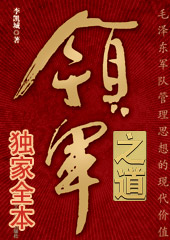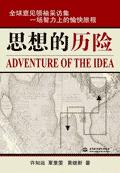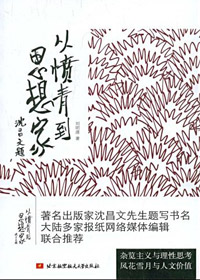从愤青到思想家-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轨的浪漫(2)
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时无刻地感受到了我们与罗伯特·金凯那个52岁的美国牛仔的共同之处:我们也同样憧憬着浪漫的爱情故事。我只能这样认为,罗伯特·金凯是幸运的;而我们则有的幸运,有的不幸运。幸运的永远是世界上的少数人,多数人的命运则会是平平淡淡。罗伯特·金凯的旅行发生了奇迹,而我的旅行没有奇迹发生。于是如我一样没有奇迹发生的、平平淡淡的大多数人,涌进了电影院,欣赏罗伯特·金凯的爱情奇迹;捧起了小说,阅读罗伯特·金凯的幸运人生。
无庸讳言,小说中最让我感动的人物还不是罗伯特·金凯这个浪迹天涯的摄影师、孤独的远游客、饱经沧桑的最后的牛仔。对于他,我在充满了许多羡慕的同时,也不免有几丝妒意——他实在是太幸运了。最让我感动的毫无疑问是弗朗西斯卡·约翰逊,对于这个风韵犹存、善良、温柔的农夫之妻,我不仅抱以深刻的同情与理解,而且充满了敬意。
作为一个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中年男人,我愿意惭愧地承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女人永远比男人更痴情。
我并不否认男人也会痴情,但男人痴情的对象,并不总会是一个女人,比如罗伯特·金凯。从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他旅行的时候,他曾经想起了玛丽安——同他结婚五年之后便离婚的民歌手妻子;他还想起了西雅图广告公司与他约会的女导演;另外,还有一个到了巴黎的女模特也令金凯无法释怀。当然,金凯自遇到弗朗西斯卡之后,尽管依然是自由身,却不再与别的女人往来,只钟情于弗朗西斯卡一人了。所以,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金凯是这世间不可多得的痴情男人。
女人则是不一样的,女人一生中更容易对一个男人痴情。尽管女人也可能恋爱多次,结婚多次,甚至于发生“出轨”和“婚外情”的情况,但她真正痴情的却常常是同一个男人。我不否认这世间永远有所谓的“水性杨花”的女人存在,但毕竟那不是女人的主流。弗朗西斯卡·约翰逊便是一个令人真正感动的痴情女人,同时她又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女人。
她的痴情首先在于她的主动。女人一般是不爱主动的,而弗朗西斯卡却没有这样所谓的“女人的矜持”。当她第一次遇到金凯向她询问去廊桥的路时,她先是礼貌地告诉了他方向、距离,“然后,在20年的封闭生活中,长期遵循乡村文化所要求的克制、含蓄、不苟言笑的行为准则的弗朗西斯卡·约翰逊忽然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领你去。’这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如此看来,弗朗西斯卡本来应当是被动的,然而她却“可爱”地主动了。他们从廊桥拍照回来之后,又是弗朗西斯卡主动邀请金凯到家里“喝冰茶”;主动留他在家吃晚饭……当然最主动的还是在她的推动下,她与金凯在不到24小时里成为亲密无间的情侣。
她的痴情还在于她的情调。弗朗西斯卡并不是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少女,而是一个在美国乡村社会中生活了20年,为*、为人母的,40岁上下的中年女人。但是她却以她特有的魅力征服了摄影师兼作家的罗伯特·金凯,更征服了作为广大读者的我们。从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遇到金凯的时候,弗朗西斯卡的脸上刚刚开始出现了第一道皱纹,但却还是滋润和美丽的;她的头发也是黑的,身材丰满而有活力,套在牛仔裤里正合适。很显然,弗朗西斯卡时值女人最成熟的时候,而成*人的魅力是年轻女人所不具备的。另外,弗朗西斯卡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之妻,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在故乡意大利获得过比较文学学位,因此她的生活情调与精神追求,即使经历了20年乡村生活的冲洗也无法泯灭掉。于是,我们看到了那样一幅令人心醉的画面:温馨的厨房,朦胧的烛光,酒杯相碰,目光交融,弗朗西斯卡觉得心里又有了能跳舞的天地。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这话实在不错,因为这“出轨的爱情”、“出轨的浪漫”,弗朗西斯卡成为上世纪许多男人心目中最美丽的女人形象之一,当然也包括不再年轻的我。
她的痴情更在于她承受的痛苦。弗朗西斯卡在这样一场“出轨的浪漫”中,付出的代价是深重的,她的巨大痛苦也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罗伯特·金凯永远地走了,却在她的心底永远地驻扎下来;而她的丈夫与孩子们参加完伊利诺依州博览会,则不会再走,并且一如既往地与她生活在一起。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她如何继续扮演她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然而她竟然勇敢地、自愿地承受了一切,直至告别尘世。
弗朗西斯卡·约翰逊实在又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女人。因为,她既懂得追求自己真正的爱情,也懂得一个真正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她是个勇敢的女人,也是个柔情似水的女人。也许前卫人士认为她没有能够打破家庭束缚,思想不够解放;而保守人士又认为她行为“出轨”,不够贞洁;但是,我却以为弗朗西斯卡·约翰逊式的“出轨”行为才是真正代表了我们一个时代的情感价值取向。
正如上面我已经指出过的,“出轨”实在与个人的品性无关,只要你不是“游戏人生”,而是真正地生活。如果我们今天仍然以一个人是否从一而终而评判其个人品质,那实在说明我们今天的社会没有任何进步;相反,如果我们把“出轨”视为一件十分随随便便的事情,甚至将男女的性行为与情感截然分开,采取杯水主义的态度,我同样不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
“出轨的浪漫”之所以成为浪漫,成为经典,并不在于“出轨”本身,而在于相爱的人们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亲手创造出了自己幸福的爱情。
(2003年1月17日)
媚与女人味
我喜欢“媚”这个美妙的词汇。一看到她便让人想起美女的眉毛,想起美女的眼神,更想起美女的“媚”来。如果这个“媚”仅仅代表了女人的姿色,婀娜的身体、姣好的容颜还不够令人满意,让人真正喜欢的是“媚”中蕴含的女性魅力。
“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玉环能够在唐王李隆基的六宫粉黛中脱颖而出,独享荣耀,靠的是姿色吗?我当然相信杨小姐肯定是个美貌佳人,但能入皇宫的女子哪一个不是有着“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杨小姐的美丽指数就一定远高过其他的宫中佳丽吗?我却是不敢肯定的。其实杨小姐真正的杀手锏是她的“媚”,“回头一笑百媚生”,不仅让“六宫粉黛无颜色”,更是彻底征服了*皇帝李隆基,也征服了我们的大诗人李白。
明人李渔曾经对女性之媚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女人如果只有美丽的容貌,而没有“媚态”是不能打动人的。他甚至举这样极端例子来说明:当让六七分姿色但没有媚态的女子与三四分姿色但有媚态的女子站在一起时,人们会喜爱后者而不是前者;当让二三分姿色但没有媚态的女子与全无姿色但有媚态的女子站在一起时,人们还是会抛弃前者选择后者。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在发现女性之美、女性之媚的杰出人士中,现代诗人徐志摩应该是最当之无愧的一个。徐诗人在其短短的一生中先后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多位著名的美丽女性发生了爱情故事: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这三个女人都是天生的美人胚子,恐怕说不上谁比谁更漂亮,可是最终俘获诗人之心的却是有些“风尘味”的陆小曼。我借用“风尘味”这个词,当然包含指责陆小曼不守妇道、抽大烟的意思;同时更重要的是想说明,陆是一个解风情,懂得施展女性“媚”力的女人。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有与李渔、志摩先生同样的发现:有的虽然是相貌平平的女子,但由于拥有特殊的“媚”力,因此其身边总是不乏男人众星捧月般的包围;而有的女子尽管相貌出众,正当年华,却总是“门前冷落鞍马稀”,成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究其原因恐怕还是缺乏“女性之媚”的缘故。
在我看来,“媚”与“女人味”一样更多于地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与女人的聪明智慧有关,与女人的悟性有关。没有“媚”力的美女,只是徒有其表,不过是花瓶而已,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美女”;而有了“媚”力的女人,即使外表不漂亮,仍然可以成为响当当的“美女”。这或许就是今天的网络世界更喜欢把“美女”称之为“美媚”的真正原因吧?回想历史上的著名“美媚”,不管是西施、貂蝉、杨玉环,还是徐诗人的三位情侣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哪一个不是拥有冰雪聪明般的智慧?即使是那位令徐诗人命陨蓝天的“坏女人” 陆小曼后来也居然修身成长为一个令人钦佩的画家和作家呢!
我由此推论,女人之媚最根本的来源是女人的聪明才智。所以古人所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纯粹是个骗人的谎言。“才”对于女人与男人同等重要。有了才智,才会有“媚”力,“才”是让女人美丽加分最好的方法。美丽是天生的、父母的遗传、上天的恩赐,可“才”却是可以后天修成的,“媚”也是可以后天修成的。
我的最终结论是“美媚”来自于教育,来自于修养。
(2006年5月14日)
真诚的世界与虚伪的爱情
年轻的时候,不经事的我总是抱着怀疑的眼光看世界,所以世界在我的有色眼镜中是虚伪的,不可信的。而那时唯一相信的便是爱情,这也许是所有年轻人必经的过程吧!时至今日即将告别自己的青年时代,蓦然回首,才发现世界从来就是如此的真诚,尽管有时是那样的冷酷;而虚伪的恰恰是爱情,尽管她常常以温暖的面目示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固然与自己平凡但不平坦的人生经历有关,但实在也与自己读过一本小书有关。
这本名为《爱经》(又译《爱的艺术》)的小册子,著者是古罗马四大诗人之一的奥维德(公元前43年…公元18年,其他三位分别为贺拉斯、卡图鲁斯和维吉尔);中文译者更为我们所熟知——以“雨巷”一诗闻名中外的大诗人戴望舒(1905…1950)。我看的本子是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根据戴望舒先生上世纪30年代初的译本重新整理的;并由著名诗人也是戴的好友施蛰存先生作了“新版序”,著名学者彭燕郊教授撰写了“重印后记”。此书历来被认为是古罗马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部十分独特的书。由于书的内容惊世骇俗,是以传授男女爱情(*)之术(爱术)为主旨,所以此书连同奥维德的其他著作一起,在其在世时便遭罗马当局禁止,奥维德本人也被流放到罗马寒冷的北方,多瑙河口的一个小城托米,并死在那里。据闻,此书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后世大诗人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的创作均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我最早读到《爱经》是1987年的夏天。那时尽管自己也已经不再是个风华正茂的翩翩少年了,而且常常喜欢用北岛的一句诗“我不相信”以自醒;但是对于爱情,对于生活,对于人生仍然充满着无限的期冀与向往。因此,当我读了《爱经》以后,竟没有被其惊世骇俗的内容所震撼,甚至反而有一些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