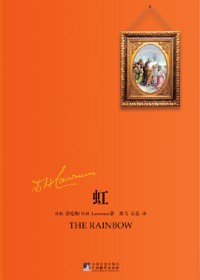青年文学·第二期-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爷爷第一次看到了火葬,回来后,爷爷脸色铁青。爷爷说,火葬真的吓人呢,把人的脑袋都掏空了,脑浆流了出来,还送到火里烧几个小时,烧到成了骨灰。爷爷说得我都害怕了,我拉着爷爷的袖子说,爷爷,你不要说了,我怕。
爷爷坐在凳子上,愣了许久。对于原先不知情而说下的“豪言壮语”。他好像有些后悔了。而我所不知道的是,那个傍晚,夕阳斜斜地照着祥安火葬场,芳草凄凄,风吹动着爷爷的头发。他站在那里冥想自己的后事。周青海就这样离开他了。走得一声不响,现在又变成了骨灰,一辈子的时间在几小时之内被统统压碎。
镇上唯一没有出席周青海葬礼的是孙婆婆。她搬着一张小板凳,痴痴地坐在诊所的门口,今天没有人来问病,孙婆婆倒是可以清静下来了。她抬头看了看门口的大榕树,她看到夕照落在榕树的枝桠上,接着又漏下来,夕照很柔和,并不刺眼。孙婆婆又将视线转到了清水河上。清水河上有一座桥,但这座桥后来在一个暴雨天被冲垮了,孙婆婆凝视着那座桥,她觉得自己看到的不是桥,而是一条连接生和死的通道。她眯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女人的身形,她穿着旗袍,水蛇腰,脚步轻盈地走过桥,孙婆婆又看到自己的母亲了,这一次,女人没有跟她说话,她还是三十来岁的样子,很年轻,可是孙婆婆自己已经这么老了,她突然觉得,看见的并不是母亲,而是母亲的鬼魂。她闭上眼睛,再一次睁开的时候,她看到父亲孙海涛走了过去,孙海涛佝偻着背,一边走路一边咳嗽,他咳嗽的声音很响很响,清水河的水波都被他震起来了。孙海涛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桥的尽头,接着,第三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周青海,周青海还是和生前一样,清癯的身体,他穿着土灰色的中山装,孙婆婆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么穿呢,周青海穿起中山装来显得很精神,他站在桥上往后看,因为背着光,孙婆婆看不到周青海的表情。她多想和周青海说说话啊,可是她就是开不了口,只能坐在板凳上这样看着。周青海朝她挥了挥手,没走进步,就消失了。眼前的世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孙婆婆知道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她总能够看到死人,看到死人也就意味着她和死人离得不远了。
平凉·旧爱(15)
孙婆婆觉得浑身发毛,骨头发出鞭炮一样的响声,她想要站起来的时候,桥上亮起了一束灯光。灯光从桥的一端朝她照射过来,一点一点照亮了清水河,又越过清水河,照在了孙婆婆的脚上。灯光好像长了眼睛,顺着孙婆婆的脚一点一点往上爬,先是她的腰,接着是她的脖子,最后,灯光落在了她的眼睛里。她受不了这样的灯光,马上闭上了眼睛。这一幕多么熟悉,孙婆婆想起来了,她用手撑着板凳站了起来,她认得这束光,这是徐方裘的手电筒发出的光。徐方裘——孙婆婆叫了一声,徐方裘你在哪里?
可是徐方裘并没有回答他,她朝桥上看过去,却什么也看不到,再看看脚上,灯光已经消失了。
徐方裘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又不知道消失在何方了。孙婆婆难过地捂住脸,呜呜呜地哭出声来。
10
孙婆婆病了,她好多年没有生过病了,以往生了病,都是自己开药方,自己取药。这一次,她病得连动都不能动了。孙婆婆是被路过的庄稼汉发现的。庄稼汉那时候正从田里干活回来,经过诊所的时候想买一碗凉茶喝,没想到就看到倒在地上的孙婆婆。他叫了邻居,帮忙把孙婆婆抬回到屋子里。孙婆婆只是暂时昏了过去,片刻之后她醒了过来,看到屋子里已经围满了人。
你们……这是怎么了?
孙婆婆,你刚才晕倒了,是他们把你抬进来的。
我晕倒了?
是啊,你就好好躺着休息吧。
孙婆婆挣扎着想要起来,可是她发现自己浑身乏力。屋子里的人议论纷纷,我爷爷当时刚从周青海的葬礼上回来,一听到孙婆婆出了事,他马上让我爸爸骑着自行车送他过来。
爷爷说,孙婆婆是平凉镇唯一的大夫,现在大夫生病了谁来医她?
孙婆婆眼睛模糊一片。她只看到满屋子的人,却看不清楚任何一个人的表情。
但他唯独认出了爷爷的声音,她说,老林,我写个条子,你们谁帮我到平溪镇去,找姓周的大夫吧。
孙婆婆卧病在床的日子里,邻居们轮换着护理她。平溪镇的周大夫来了之后,开了几帖药,吩咐邻居们按时煎了给孙婆婆喝下。邻居问周大夫,这孙婆婆得的什么病?
周大夫说,气血攻心,是心病啊!
而孙婆婆何尝不知道,这些年来压在心头的痛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折磨着她。夏夜的时候,她就搬一张凳子,坐在榕树下,看看天空,看看清水河,许多往事就这样一件一件,像河里的木头一样,浮了上来。现在,她只能长时间躺在床上,偶尔下来走动也仅限于屋子里。她突然想起了孙海涛,想起孙海涛生病时的样子。孙海涛已经那么老了,老得好像一截脱水的竹笋一样,皱巴巴,没有一点生机。有那么一瞬间,她看到孙海涛变成了一个无助的小孩。这使得她认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是会倒退的。她在屋子里踱着步,很缓慢的,地板这段时间被很多人踩过了,还来不及拖干净。孙婆婆的脚就踩在地板上,木质的地板踩起来有种不一样的感觉。有些沙砾硌到她的脚,她踱到门后,拿了扫把和簸箕,将地板扫了一边,扫出来的,尽是沙子。她动作如此慢,慢得好像被什么给粘住了。她的腰很酸,腿也不利索,她干脆坐下来,把堆在一起的沙子捧在手里,然后举起来,握住,让沙子顺着手的缝隙一点一点往下渗。沙轻飘飘地落下来,很快就漏光了,她又继续捧起一把沙。如此重复,怡然自得。
平凉·旧爱(16)
孙婆婆觉得,现在她变成了一个孩童了,原来传说中的鹤发童颜就是这个样子啊。她看着沙子笑了起来。沙子往下流动,窸窸窣窣的,孙婆婆说,人就是这么走的吧。然后她就看见徐方裘了。徐方裘从漏下的沙子中间露出脸。他还是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样子,下巴爬满了胡渣,穿着一件左袖有洞的军装。
孙婆婆想对徐方裘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忽而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便弯下腰,在床底下拉出一个藤箱。打开来,藤箱底下压着的,是徐方裘的军衣。孙婆婆抱着军衣,就像年轻时候抱着徐方裘一样,军衣散发出男人身上特有的气息,这种气息从尘封已久的箱底发出,穿梭了久远的时光。清晰如昨。纵然他和她相隔千山万水,相隔了四十年的时间,但那是的刻骨铭心,就像军衣袖子上的补丁,时间无法消磨,任何人都无法除去。
11。
隔天天还没有亮,孙丽芳就起床了。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盖着徐方裘的军衣。孙海涛还躺在躺椅上睡觉。孙丽芳怕惊动了他,蹑手蹑脚地洗漱,然后找出针线盒,一针一线地给徐方裘缝起了军衣。这是她第一次为除了父亲之外的男人缝衣服,她觉得每一针、每一线,都是为了幸福而缝补,她找了颜色和军衣相近的布料,用剪刀裁剪出比衣服上的洞略大的补丁,然后按住,将针穿了过去。天微亮,榕树过滤了阳光。麻雀在榕树枝上跳着叫着,一个美好的清晨又开始了。
孙海涛发现了女儿的异常,他醒来后,颤颤巍巍地走到孙丽芳的房间里。孙丽芳还沉浸在美好的幻想里,并不知道孙海涛在她身后站了多久。直到孙海涛咳嗽了几声,她才惊惧地转过头来,不小心扎到了手。
孙海涛说,是谁的?他的语气里容不得半点欺骗和狡辩。
孙丽芳老老实实说,是……是徐连长的。
徐连长?徐连长是谁?!
志愿军。
好哇,你背着我跟志愿军搞在一起……
孙海涛的话还没有说完,就顺手拿了挂在门边上的鸡毛掸。孙丽芳从小到大受尽了无数次鞭打,现在她长大了,可是孙海涛还当她是个孩字,动不动就要打。
孙丽芳把军衣紧紧抱在怀里,她扬起下巴,看着孙海涛。姿态里尽是挑衅。
孙丽芳说,你打啊,从小到大你就知道打我!从来不关心我是死是活,我跟志愿军怎么了?我跟志愿军也不愿一辈子呆在这个晦气的地方!
孙海涛已经气到不行了,孙丽芳还是第一次这么公然顶撞他。他挥起鸡毛掸,朝着孙丽芳就是重重的一鞭。孙丽芳没有想到,抱病的父亲一旦动怒,还能爆发出这么惊人的力量。鸡毛掸落在她的手上,火辣辣生疼。但她咬住牙齿,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隔了这么久,再一次被孙海涛打,孙丽芳心里的委屈无从诉说。孙海涛打得那么用力,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显然,他有些力不从心,他停下来,把手放在膝盖上,气喘吁吁。孙丽芳狠狠地盯着孙海涛,她把自己的嘴唇咬破了,血流了出来。
你打啊,打死我算了,打死你就开心了!
你……犯贱!
对,我犯贱怎么了?
孙丽芳十几年来挤压在胸腔里的愤怒和委屈一下子爆发出来了。她想不到自己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她闭着眼睛不让自己去想任何有关伦理道德的字眼,不让脑海里闪过纲五常仁义忠孝。这些,统统是骗人的幌子。这一次,她铁了心要和这个家决裂,这个时刻她等了好久好久,久到令她厌倦。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平凉·旧爱(17)
父亲的脸色铁青,他被女儿的话惊呆了,又气又恨。举着鸡毛掸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了。
给我滚出去!孙海涛几乎整个人咆哮了起来。
孙丽芳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拼命忍住没有让它流出来。她不能哭的,一哭就彻底妥协了。她抱着军衣,捂住被父亲鞭打致伤的手臂,眼里含着泪。头也不回地冲出家门。
孙海涛手里握着的鸡毛掸忽然掉下来,鸡毛掸落在地板上,上面土灰色的鸡毛参差不齐,好像刚刚遭受了一场蹂躏。孙海涛整个身体在发抖,越抖越厉害。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控制不了手,控制不了脚,控制不了他的意志。孙海涛用手按住额头,一瞬间,他整个灵魂都被抽空了。
窗外的麻雀还在叫嚣,阳光很好地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孙海涛看了看窗外的一切,顿觉眼前模糊起来。一个趔趄,轰的一声,重重地倒在地板上。
12。
一九五三年的夏末,秋天错在拐角处静静伺伏。清晨的平凉镇还处于苏醒的过程中。黑的黄的土狗在大街上溜达,时而在路边撒尿,时而互相追逐着。孙丽芳来不及看这些,因为跑得匆忙,她只穿着一件单衣。她怀里抱着徐方裘的军衣,军衣在平凉镇的晨光中跳跃着,袖子呼呼作响,好似要飞起来一样。孙丽芳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不停地超前跑。她的布鞋踩在石板街上,因为跑得太快,不小心滑了一跤。但她没有在意,在半路停了一下,又继续跑起来。
平凉镇的人第一次看见孙丽芳如此张惶。这个清晨,人们所见的孙丽芳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提着一桶衣服要到清水河洗衣服的妇人吓得停在路上。孙丽芳苍白的脸宛如一张皱皱的纸一样飘了过去。
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指引她,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