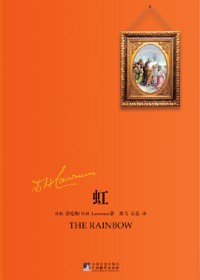青年文学·第二期-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明明喜欢她的恭维,笑道:“我也喜欢这幅夜色,晚上都舍不得拉窗帘的。这么好的风,这么好的月亮,框在窗户里。”
“月光下是万家灯火,深圳多么壮观啊”朱姝一扬眉:“我就喜欢这样的城市,万人如海一身藏。”
“我似乎是不行的。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不敢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明明期期艾艾地。
月明荞麦花如雪(31)
“为什么?”
“也是你说的,万人如海。我不敢的。”明明嗫嚅:“住得再久,也是个路人甲。”
“唔,我喜欢这种新鲜和疏离的感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心灵碰撞。”朱姝怜悯地,伸手抱抱她:“你前世是一个相府家的小姐呢,养在深闺里的,是不是这一回投胎不曾喝够孟婆汤?所以你这么老派、怯弱?”
“哟,你当我不认识你?你前世,分明是相府绣楼上的梁上君子。惯于偷香窃玉的。”
俩人相视哈哈大笑起来,心里都觉得窘,喜悦。
而司哲呢,也是旧梦缠绵里,被朱姝拽到明明跟前的。那天,在一个派对的夜宴上,朱姝心事重重,三杯两盏便喝得满面酡红,对明明说:“你想不想陪我去见一个人?”
“男人么?”明明道:“不是你先生么?为什么不独自去赴约呢?我陪你去岂不是很碍手碍脚?”
朱姝吃了讥讽,饮下一盏香槟,纳纳地启齿:“其实,我不敢……我不敢断定,他见到我是不是会高兴。”
明明便省下了她那溜到嘴边的讥讽,随着朱姝离开喧喧的人群,坐到车上。车经过流光溢彩的静静的大街,夜风灌进窗内,明明看一眼朱姝,风吹得她脂浓粉腻的脸,黑发飞舞,象午夜里的艳鬼。这城市的海滨区,明明从来不曾来过,朱姝却是驾轻就熟的,车顺着一条灯火灿烂的寂静长街开过去,灯光里是婆娑的椰子树,飒飒地舞。汽车拐进一片公寓区,午夜里的灯火阑珊。朱姝说:“喂!这儿可是我当初置下的婚房呢!九十九平米。在第八层楼。”她数着数,伸手指一道阳台给明明看。
明明说:“好吧,就算陪着你死也让我明白待会儿会死在谁手里。你要来看的这人是谁呀?”
“我的初恋。哼,我可不是来看他的。我是来祭坟的。好歹这坟当初我也置下过砖瓦木头的。”
明明笑道:“和演鬼片一样,瞧你!”心里亦大致明了是怎样的一片情愫,随着朱姝踏进了门厅,上电梯。入目所见的皆是这幢公寓的洁净雅致,典型的中产小康风雅,虽然朱姝后来嫁的是豪门,然而,当初为她置下婚房的人,一定是用心的。她感觉得到朱姝的身子,颤颤地打抖她是怕的。即便朱姝今夜喝多了酒,满腹的酸楚,满腹的不甘,不撒手,然而,明明明了:这故事的打底,一定是她,负了当初的那个人。
出得电梯,敲响一扇公寓门,朱姝生怯地转身,退到明明身后,门里很静,朱姝小声嘀咕道:“走吧,早没人住了。”
明明没有出声,身后的那个女子,热热地挨着她,害怕的,散发着酒和脂粉、香水的香,这么个热烘烘的小东西,令她觉出爱怜、不忍落。门内有光了,有脚步走过来的声音,明明伸手扣扣门。门打开了,里头探出一张脸,令明明眼前顿时一片光芒浩然。是一个修长的男子,剑眉星目,高贵的直鼻,骨感的脸,疑惑地看着她,微微地,唇红齿白地一笑:“哦,你敲错门了吧。” 明明一惊,心跳几乎跃然,她认得这张脸,他是去桥梁事务所采访时见到的那个工程师,司哲。也许是夜深的灯光,也*明喝多了,他的那张脸,迥异于在办公室看见的平淡。那男子瞅着她,一边诧异着,一边疑惑着眼熟。明明瞠目结舌地,移开一步,将身后的朱姝让出来。门里的人看见朱姝,瞬间石化,明明看见他又笑了,不是方才那种犹如初阳的微笑,却笑得更好看了,一边的嘴角扬起,戏谑地,疲倦地,不伤心地,好笑地笑着自己的午夜际遇,也笑这午夜的两个艳鬼。他头往里一扬,示意这两只女鬼进来。
月明荞麦花如雪(32)
明明走进来,客厅亮着一盏落地灯,照出一小片光来。将光的外围扩开得无限广阔。里头倒有一间房漏出另一些光和唱片的声响,明明听出来,是埙,那种古老的,近乎绝迹的民间乐器吹出来的浑厚、忧伤的曲子,无名无调里也有无限的夕阳残照,故国家园的凄凉意。明明回过头来,只见朱姝蹿起身,抱住那男子的脖子,只这一眼,她赶紧往开着门的房里避进去,顺势紧掩上门。这是一间书房,果木色木地板,四壁都是书,偌大的一张书桌,居然排开文房四宝。案头一盏夜读的灯,照着一本摊开的书,一杯茶,桌面很洁净,明明很震动,因为方从声色歌舞场退下来,也油然令她想到,在事务所看见的,他端坐窗前的那一幕。她走到书架前,一排排浏览起来,她看见书架上一本图文版的童话书,《木偶奇遇记》,旧旧的,书页都泛软发黄了,
外头闹起来了,两人推拉的动静,然后,发出声音了。朱姝在哭泣,她一再扑上去搂住男人,又被他迅即地推开以后。她感觉他双臂的动作一次比一次有力,越来越恼怒。她终于不扑了。象从前那样,*了他,就呜呜地哭起来。她哭的是真的,泪音不加掩饰地,越哭越伤,越哭越痛,她嫁人有几年了。在这样一个子夜,她喝多了才敢来找他 她的双臂攀着他的脖子,紧紧地贴紧他,面颊挨着他颈脖、肩膀上的皮肤,然而,他僵硬的身体,在她躲不开的双臂之间,固执扬起的脖颈,紧闭的双唇,这无动于衷,是她陌生的。这面前的是另一个男人,铁石心肠的陌生男人……她终于惊愕地收住了眼泪。
明明握了那本书,适时地从书房里走出来,司哲此时也认出了明明,是在采访场合见过面的。明明向他善意地一笑,点点头。朱姝眼巴巴的样子,并不欲离开。张嘴道:“我饿了,一晚上喝了那么多酒,明明你饿么?”
司哲黑的脸色和缓了一些,起身去厨房捧出果酱,饼干,将牛奶和红茶倒进电茶壶里,煮茶招待她们,烤热面包片。朱姝眼睛红肿,接过涂了橘子果酱的土司片,吃起来,小兔子吃萝卜似的。仰起脸来,甜蜜的眼波自明明的脸上流到旧日男友的眼睛里,娇滴滴地道:“他晓得我就喜欢吃橘子味道的果酱。”
明明笑微微地示意自己的感动,司哲递给她一片蓝莓土司,又倒一杯红茶,将方糖罐子递过来。她手里捧着书,低头看着,尽量地不在空气中占面积,让他们尽量忽视她。
朱姝吃完了面包,起身去各个房间巡视起来,哑着哭过的嗓音,不时地问道:“这盏灯是不是我带过来的?还亮不亮?”
“还是从前的小洗衣机是不是?洗出来的衣服湿淋淋的,这洗衣机不好甩水。”
“我从前买的那套英国瓷呢?你怎么不拿出来喝茶?”
明明听得很难过,朱姝竭力地想要在这里多流连一会儿,她兀自嘟嘟囔囔说下去,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在曾经的小屋里,一样样家什摸过去。司哲抬起手腕,看看表上的时间,微蹙了一下眉。他一直是克制的,冷清的,却愈发落实了他曾经的身份。明明看着他,灯光下他的脸,骨感的腮,殷红的唇,很好看的一张脸。
男人转头她手上的书,不由地好笑起来,明明捧着一本《木偶奇遇记》,在这客途秋恨、冲突的夜晚,看这么一本书,可真是淘气的。明明也觉得其间的滑稽,赶紧捧着书捂着脸。只有封面上的那只歪荸荠帽,长鼻子的木偶娃娃,随着她一起笑起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月明荞麦花如雪(33)
司哲问道:“你喜欢这本书?”
明明点点头:“我一直相信,有那么一个遥远的地方,屋顶圆圆的,窗户象小橘子。小木偶生活在那里。”
司哲笑笑,颇有同感地点点头。明明问道:“那么,你知道大海里最有礼貌的哲学家是谁吗?”
他愣了一下,愈发笑起来,反应敏捷地反问:“你知道大海里最羞涩的鱼叫什么名字?”
明明被笑声吸引过来,从情天恨海的卧房里走出来:“你们在笑什么呢?司哲说什么了?”
男子闻声,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好吧,该走了。我送你们下楼吧。”
他这般不留情地将朱姝的午夜梦回里的旧梦,给梦完了。他很明白她她只是,喝多了,发发癫。然而,他是个温和的男孩子,帮着女孩子开门,按电梯,先板着电梯门、公寓楼大门,好让女士通过,下台阶的时候,他的声音温和地提醒,小心。看着她们俩上车,明明隔着窗,向那男孩子小小地一摇手。他敲敲窗户,拿着手机对明明说:“不冒昧的话,我想记下你的手机号码。”
后来,他写短信给她,一直称呼她为小木偶。那样温和,喜爱的口气。”
那夜她们又一起守了通宵,一个银白的圆月亮,灯笼一样地挂在露台外的天空里,逼得那样近,人在这样的夜晚,说的都是掏心置腹的话语。朱姝说的最多的,当然是司哲。她是她先生,从司哲手上硬夺过来的。司哲是他先生公司里的得力干将,他很爱护他,见过他的女友,也很*。他的才华,他的女友,这一切都令这个中年男人爱慕。而她,朱姝,一边和司哲分手,一边有条不紊地试婚纱、挑钻戒、珠宝。司哲放手得很平静,他离开公司,去国外读了三年书,再回到深圳,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还会回到这个城市,他是个很优秀的建筑师, 大抵在这里可以做很多事。
明明听着这个冷飕飕的故事,月亮下刮的大风,全是阴风,一阵阵的阴风。她说:“你没有恨过你先生么?为你和司哲。”
朱姝听着这样纯情的提问,轻蔑地一笑:“有一种人就是卓越的,超凡脱俗的。他象神,你遇见他,天生注定,只可诚服于他。”
那天,她们聊到天明,上街去茶楼,遍地的晨光,风吹着勒杜鹃的红花,车经过海边的大道,一轮红日正从海面升起,她们到了食肆,天亮时的茶楼前泊着跑车,一看就是那种冶游客,喝过早茶好睡觉。盛妆倦容,坐在堆满小笼点心和茶壶的桌前。朱姝和明明坐在一张桌前,商量着吃什么。清早的茶楼,这一拨客人,都是夜晚剩下来的。喝过早茶,朱姝赶回去上班,明明一个人沿着清晨的街,散步。心里觉得累过了的解脱,兴尽了的松弛。
每日每日,明明依然在等待雷灏来到。说到底,她是信任雷灏的,凭着他和她之间,这些年,彼此的这份心,她不信,雷灏会将她抛闪下。无论如何,她和他之间,会有一个结果。
雷灏再来的时候,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前来安置明明的。大局已定,他无需再儿女情长。他这样说:“明明,我从此不能再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明朗,这样冷静地说出来。将料理的后事一一铺陈:深圳的房子是明明的,不会再有变故。另外,他还在银行里给她立了帐户,放了一笔钱。
明明木然地看着他,一时间找不到话语。过了好久,张张嘴,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还没开口就已然虚弱了,因为她了解这个男人,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不会这样说,且,他这样说了,必然这样做。这样一念,已经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