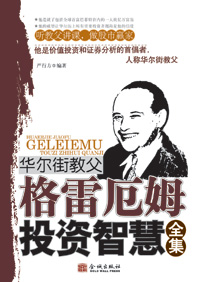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约束着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大人在客厅里见面时,彼此都彬彬有礼地谈话,虽然住得近在咫尺,但在三年生活中相互从不跨进对方的门槛——除了我们搬走以前一两个月的一次例外。弗米利家邀请我的母亲、莫里斯舅舅、伊娃舅妈上他们家去喝茶。回来后,莫里斯舅舅说,他们确实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可惜在我家快要离开时两家才相互了解。弗米利家的这一次好客是不是因为隔壁犹太人邻居即将搬走了呢?
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拔拳动武就是与年幼时的约瑟夫·弗米利打架。我不记得是如何打起来的,但是我俩正在家门前的街道上,我的哥哥、表弟洛和其他小孩团团围着,怂恿我们进行较量。对峙可能持续了一两分钟,我们用力挥拳出击,但也许一拳也没有打下去。大人来了,打架就停止了,我们两个11岁的孩子松了口气,而观众却觉得大倒胃口。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如何能做到避免打架的呢?令我自豪的是这不是因为我逆来顺受,或被赶出争斗之外,或乞求饶恕。那是由于我生性极其温和,从来不挑起事端。但是为什么别人避免向我挑战呢?事实也许是我一生都很幸运,其次可能的解释是,在我的童年——好打架的时期——我几乎总是与年龄和身材都比我大的孩子在一起,大孩子和小孩子打架是违背年轻人要有骑士风度的原则的(“为什么你不与和你同样大小的孩子打?”这是在场的人总要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第三个解释是——听起来有点高深莫测——我的某种气质保护我不会碰到别人的敌对行动。几乎人人喜欢我,甚至庇护我,他们觉得我确实不属于那帮淘气的孩子。
3在公立学校(4)
我有个朋友是我家马路对面一个裁缝的儿子,名叫卡夫曼。他常在自己店铺橱窗上贴一两张关于附近戏院最近或将要举办的演出广告。因此他得到两张免费入场券。好几次,小卡夫曼邀请我与他一起去看星期六的日戏,因此看戏成了我生活中的大事。但是当家里大人知道我和裁缝的儿子交往时,他们有点皱眉头。虽然我的家庭不大买得起贵的东西,可是嫌贫爱富的情绪总是那么强烈。
还有一个故弄玄虚、十分富裕的男孩——我哥哥维克多的朋友——常常到我们公寓来玩。他有一个继父——在我们眼里简直是一头奇怪的动物——而且口袋里总是装着许多硬币。我记得他坐在床上或椅子里,把一大把硬币掷向空中,撒落在房内地板上,脸上流露出恩赐的神情,喊着:“抢吧!抢吧!”我们三个男孩伸出双手,跪在他的面前,尽快把这些恼人的硬币拾拢来——钱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一天他给我讲孩子怎么出生的;他敞开衬衫,给我们看肚脐以下一大块地方,他说母亲就是打开这块肚皮,让孩子出生的(按他私下所说,所有孩子都是像尤利乌斯·凯撒一样诞生的)。这个家伙——我已忘记他的名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过很大的冒险。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圣诞节,纽约市民主党的坦慕尼协会在托尼·帕斯特戏院(就在14号街坦慕尼协会总部的隔壁)为穷苦儿童举办庆祝会,把一棵大圣诞树上的玩具分送给每一个参加者。他说可以为我们三个人弄到入场券。但是母亲会允许我们去参加盛大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吗?当时和以前,所有犹太人惯常都是怀着不满和害怕而不是妒羡的心情看待圣诞节的。可是母亲竟然极其宽容,我们获准去了!关于这次圣诞庆祝会,我清楚地记得的一个重要时刻是我们在戏台前走过,索取挂在巨大的圣诞树上或放在树下的一件玩具。我拿到了一个“灵活的飞鸟”牌小雪橇——这是我做梦都未想到的意外收获。
唉!命中注定我不能长久享受这件极好的礼物。1月份下起第一场大雪时,我带着小雪橇到莫宁赛德公园附近长长的滑雪道去。滑雪道从莫宁赛德高地很高的地方开始向西伸展——大约在113号街——然后突然左拐到110号街,转向下面的莫宁赛德车道,然后再朝左急转弯,到达地面的一个街区。
滑了几圈后,身后一辆坐着六个大人的长雪橇撞倒了我。我肯定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知觉。当我苏醒时,似乎没有任何人关注我,我的小雪橇也无影无踪,虽然我在山坡上爬上爬下无数次拼命地找,可是再也没有看到它。我回到家里时,几乎已泪流满面了。
除了圣诞节——当时花钱比现在少——还有三个节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7月4日独立日。这一天人们欢乐地不断喧闹,频频开枪,为此甚至有人伤亡。黎明时我们被街道上左轮玩具手枪断断续续的射击声惊醒。每个够格的青年都有一把22毫米口径或比较显眼的32毫米口径的小手枪,还有大量空壳子弹供节庆使用(有些傻瓜吹嘘他们发射的全是真子弹)。到了下午,街道上到处是子弹壳,一片杂乱,我们在街道上尽量捡弹壳,口袋里能装多少就捡多少(捡弹壳做什么?我记得把一只弹壳夹在两个手指的指关节之间,然后适当地对着弹壳吹,可以产生极响的哨声)。年龄太小的孩子不能用左轮手枪,就用盖帽玩具手枪(有的枪帽里藏有很多火药)。他们还有各种爆竹,包括中国制造、称为鞭炮的100响小炮仗串。这些小炮仗捆在一起出售,只要1分钱。通常炮仗串作为一个单位燃放,可以显示一下放炮仗者的勇敢。但是对于必须掰着手指花钱的人来说——即对利昂、维克多和本尼来说——他们会把1英寸长的鞭炮从一串上拆下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一个个地燃放。有一种我们喜爱的玩法是用旧报纸制作一个小盒子,把点燃的爆竹塞入盒内,把盒子掷出窗外或者从屋顶上掷出去。那种爆炸声是十分扣人心弦的。
3在公立学校(5)
此外还有一些海报宣布,在某时某地——通常在125号街上——某家商号主办燃放“世界上最大的爆竹”。我们挤在围成一大圈的人群中,戴着高高头盔的警察把大家与爆竹隔开一段距离,以保安全。我们好奇地盯着有一根细绳似的导火线的大纸筒看,既欣喜若狂,又有点担心地等待着震耳欲聋的响声。有时发生火灾,就会出现很多马拉的消防车,几个或几十个孩子在后面追逐,但是大多数火灾太小,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观看。大多数家庭购买一些晚上观赏的花炮——“火箭”啦、“罗马蜡烛”啦、“圣凯瑟琳车轮”啦,五花八门——黑夜一来临,他们就从公寓窗户或在街上放烟花。今天,所有的烟花都由领有执照的专业人员施放,并受到政府当局的严格控制。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爱怀旧,但已不为伟大、光荣的7月4日所发生的大火灾而真正感到遗憾。家破人亡这个代价确实太高。已远远超过了五彩缤纷的礼花怒放和狂欢作乐的意义了。我是带着复杂的心情写这一点的,因为在1928年我当上了美国最大的烟花制造公司的董事和(名义)副总经理。不少年里,我灰心地看到我们的业务迅速受到所谓过一个“安全健康”的独立日这个简洁口号的损害。
至于鬼节,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节的真正内容。我们从未听到别人称它为“万圣节”。当时对我们来说,如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小孩来说一样,这一节日与图上画的女妖、巫婆和挖空了瓤、芯子里点上蜡烛的南瓜相关——可是这些东西实际上从未进过我们犹太人的家。在我们的生活中,鬼节的真正意义是许多小孩子傍晚在街上漫游,把他们的上衣反穿,拎着塞满了面粉的长统袜,以此相互攻击或袭击附近的其他人,使受到攻击者的衣服上留下很难擦掉的白色条纹。
每年11月有一个“选举夜”(因为纽约市市长两年一任,逢奇数年份选举)。对年轻人来说,选举活动的最重要方面是举行大篝火会。一堆堆篝火是各帮青少年聚集的领域,他们当时给警察带来的麻烦比以后的青少年要少得多。在选举日之前,各帮青少年收集各种木料——主要是从杂货铺收集的空包装箱——然后把它们贮存在地窖里或某个空地的角落,等待大篝火熊熊燃烧之夜的到来。如果秘密的藏木地点给另一帮少年知道了,就会带来一场大破坏。“第110街那帮人偷去了我们的木料”,这是一个最令人心疼的消息。“选举夜”来到了,每隔几个街坊的中央及时地堆起了木头,点上了火,熊熊燃烧很长时间,周围是一大群入了迷的观众。
20世纪初纽约街道上的感恩节,是小孩子穿上大人的衣服,在街上讨钱的一天。“感恩节,给点吧?”是向每一个过路人提出的节庆套语式的问题。我们不准参加这种化妆假扮乞丐向路人要求施舍的活动,这与我们可尊敬的资产阶级地位不相称,尽管我们一贫如洗。而今这个习俗的时间变了,假扮乞丐乞讨的活动不是在感恩节而是在万圣节出现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3在公立学校(6)
当时和以后的年月里,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做家庭作业。我是一个好学生,为了学到知识而在读书上全身心投入,并且怀有取得突出成绩的勃勃雄心。家庭作业量很大,但是我做得很快,而且利用了各种零星时间。母亲常常夸张地说,她不明白我如何会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因为从表面上看,我总是在做除了家庭作业以外的事情——通常在读一些并不要求读的书。
当我在校第6年的时候,纽约市各学校发生了一件称之为“马克斯韦尔考试”的重大事件。这些学校的总监是一个叫做马克斯韦尔博士的可怕家伙,他宣称他不满意纽约市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学术能力。他亲自出了一系列英语和数学试卷,要让每个小学生做。各个年级的考题都极难,打分也很严格。我很失望地获悉自己的英语成绩才68分,但成绩第二名的孩子只得了42分,我的分数看起来仍比较突出。然而数学考试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在正面黑板上写着5道题目,看来并不难,我很快做完交卷,走出教室,这时其他人还在考试。后来著名的伯京斯博士——第十公立小学无数毕业生都记得他——把我叫进校长办公室去。
他说:“本尼,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答最后两道题呢?”你可能猜得到其中的原委。第6题和第7题竟写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我未看到,也没听到教师讲。我圆满地回答了前5道题,所以得了70分——这是我校最好的成绩了。伯京斯博士遗憾地摇着头对我说:“要是你把另外两道题也答了,本来会使你自己以及我们学校出名的。”
当我进入第十公立学校7A级“分科制班”时,我的学校生活真正变得津津有味了。不过我体面地升入这个班级的第一天却根本不体面。学期开始后不久,我突然从6B级提升到7A级(每年分成两个不同的级别)。由于这是我第四次跳级,刚刚10岁,校长助理领着我和其他几个孩子到新的班级去。这个班40多个小学生全是男孩,他们看了我一眼,就爆发出哄堂大笑。在这些12岁的男孩中,我没有像他们一样穿着诺福克套装,而仍旧穿着象征小男孩的水手式连衣裤。他们把我看成某种怪物,我也开始极其不喜欢自己的模样。当天下午我在家里大吵大闹,搞得母亲无可奈何地带我到第125号街科克服装店,给我买了第一套诺福克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