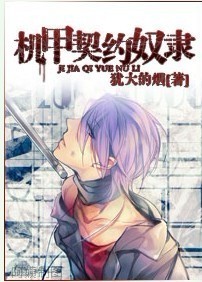荷尔蒙的奴隶-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智玩命逃过抓捕,但没跑出多远就又灵机一动踅身拐了回来,并以各种障碍隐身藏形回到断墙边,潜伏在墙头向货场里窥探,直到看准王力被抓进了那座木屋。
天傍亮时,几个值勤人员将王力锁在木屋里,相继离开回宿舍睡觉去了。一直趴在墙头观察的王智,见他们渐渐走远了,便学爸爸常夸耀的和电影里演得侦察兵的样子,匍匐在地,顺墙根连滚带爬接近了木屋,和王力里外协同连拉带撞拆断门锁,双双趁着黎明前的黑暗逃遁。临逃离的那一刻,胆大包天的王力顺手牵羊拿走了屋里的一个挎包和一件棉大衣……
(四十九)
母亲心情不好,姐执意要留下来多陪她几天,张先只好一个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黄海边儿。张母听儿子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后,宽慰儿子道:“咱能办到的都办了,剩下只能看天意啦!”
张先觉得也只好如此了,便沉下心来和村里几个铁哥们傍着去偷海,昼伏夜往,没日没夜,想多挣点钱将来结婚好用。
姐陪母亲在丹城连续数日四处寻找王智、王力仍无果,母亲心情愈发变得焦躁,早把姐和张先的事情抛在了脑后。眨眼已进了腊月,姐想回黄海边去找张先商量是否该回北大荒去过年?恰在此时,她竟有了妊娠反应!
母亲发现了,便又想起了这件难心事,她一度大发狼烟,要姐或去医院打掉孩子,或去法院状告张先,姐都坚定地予以拒绝了。
姐对母亲说:“我可不能再像你,离了狗窝却进了狼窝,我认命了!”
母亲见无力回天,也只好顺水推舟,全身心放到寻找王智、王力哥俩的事情上。
王智、王力俩从货车场逃出来,在车站附近接连流浪了好几天。白天野逛,晚上睡票房,很感惬意。
王智有感而发:“从今以后,再也不用被爸那个老*灯管制啦!”
王力随声附和:“也再不用上课写作业了呀!”
“哈哈,哈哈……”哥俩同声同气地开怀大笑起来。
王智也曾担心过,总在车站附近转悠,恐怕会被货场的人发现抓着,但一时又不知该往哪儿去,只好一天天在站前捱了下来。
不知不觉,从家里偷出的钱和粮票全花光了,哥俩就只好重操旧业。掏包、去食品摊上打劫,哥俩一个掩护,一个行动,就像老练的游击队员,侦察兵和特工一样,竟令俩人屡屡得手。然而,就在哥俩得意忘形之际,却被公安民警逮了个正着……
这个时候,新中国建立后遭遇的特大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已近尾声。全国广大城乡基本生活资料短缺,已相对得以缓解,特别是食物已渐渐丰富起来。当人们期盼已久的大年一天一天地临近时,整个社会和几乎所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少有的喜气。
姐怀孕的消息令张家母子亦喜亦忧,为掩人耳目,避免麻烦,姐实逼无奈,只好同意按渔村习俗,不去登记,先结婚。张先迫不及待地跑去县城给爹发电报,说姐病情加重,要爹速来,爹接到电报的第二天就只身匆匆往丹城赶来。
爹到来后,得知事情原委,见生米已煮成熟饭,只好默认张先提前操办婚事。
时值特殊时期,又因没有登记,只能一切从简,悄没声地摆了几桌席,由主持人和双方父母说了几句话,就算举行了婚礼。
由于临近年关,时间紧迫,爹在姐结婚的第二天,就匆忙离开黄海沿儿,赶往北部山区的老家去了……
王智、王力很快便被移送到丹城市公安部门,又经学校、街道等部门反复磋商,最终决定将他二人送工读学校接受教育和改造。
王智、王力被送往工读学校的那天,正巧是姐结婚的日子,百感交集、苦不堪言的母亲,既不愿去送两个儿子,又没心情前去参加女儿的婚礼,只好一个人躲在家里默默饮泣。
爹在老家只短暂逗留了两日,与兄嫂们聚了聚,又去给祖坟填了填土,便马不停蹄地离开了老家,离开了丹城。
夜晚,当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困倦之中的时候,爹风尘仆仆地走进了火车站候车室。他翘首张望,四处撒目了良久,才又风风火火地向一位正趔趄在墙旮旯打瞌睡的年轻女人走去。
爹柔声细语中杂糅着焦躁:“喂,喂!我说,快别睡啦!马上就要开车了呀!”
那女人冷丁打了个寒噤,猛然从困盹中转来,急忙抖身站起来:“啊?我,我们没晚点吧!”
“噢,还没有,咱们赶紧上车去。”爹说完扭头便走。
那年轻女人麻利地收拾了一下身边的行囊,匆忙跟上爹向检票口走去。
这女人看上去大约有三十岁,偏高个头,瘦长的脖颈上挑着个黑月亮般的发髻儿,一件缀了补丁的旧花袄,像挂在衣架上似的,随着身体的移动,一摇一摆的,下身一条肥肥大大的,因退色而显蓝白相间的棉裤,在步履的交错前进中,若两面被风吹动着的旗帜,有节奏地发出“呼呼啦啦”的声响……
爹和这女人一脚前一脚后地刚上车,车便缓缓地启动了。爹在车厢中找到座位,让那女人坐到靠窗处,那女人一边就坐,一边嗔怪道:“你可真有抻头,人家都快被你急死啦!”
爹边坐下来边道:“我也是不得已呀,这好几十里的山路,一步步量过来……”
“哎呀,你咋不堵辆车呢?”那女人不等爹把话说完,急切地抢话道。
“唉,这么晚了,哪还有车啊!”
“那你干啥不早点儿动身?”
爹瞥了一眼正在瞅着自己的那女人没吱声,却不自禁地向外边移了移身体。
不料,那女人却又向爹身边凑了凑,将嘴巴贴近爹的耳朵悄声道:“我俩的事儿没人察觉吧?”
爹不禁一怔:“我俩?什么我俩的事儿?”
“哦,”那女人翻了翻白眼儿,“就是,就是我跟你跑北大荒的事啊!”
爹不禁叹了口气:“唉,要不我咋让你白天先走,我晚上才赶着离开呢?说啥也不能让人们怀疑了啊!”
那女人忽然沉默不语起来,两只深陷在眼窝中的大眼睛,迷惘地望着车厢顶棚,一张白里透黄的脸上渐渐堆起了僵滞、木讷的表情……
(五十)
夜愈发地深了,车窗外已不再有朦朦胧胧的灯光和城市迷迷茫茫的轮廓及景色,夜完全变成了漆黑一片的大幕。
列车突然加速了,车轮碾过铁轨发出的“呼隆”“呼隆”的节奏声,仿佛如爹的心跳,直到这时候,他才似乎感觉到自己有了正常的心律!
大概过了好久,爹才扭头冲那女人道:“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不管咋样,总算平平安安走出来了。”
那女人听了不禁凄然一笑:“啊,真是谢天谢地,真是感谢吴哥呀,吴哥的大恩大德我终生难忘啊!”
“唉唉,你就别再这么外道了,咱们乡里乡亲的,我也实在看不过眼儿去,能帮就帮你一把吧!”
“哎哟,吴大哥,你真是个大善人哪,这次要不是遇到你,我真就没心思活了!”那女人将身子向爹靠了靠,又接着说道,“过去那些年,我因为有那个孩子,啥苦啥罪我都能遭,啥怨啥屈我都能受,可如今孩子去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啊?何况还要整日看人白眼,受人歧视和管制!”
“噢噢,我说大妹子,大妹子……”爹警觉地向周围扫视了几眼,想看看有没有人注意他俩的谈话,一时嘴里竟不知说什么好。
她似乎注意到了爹的表情,也不禁变得警惕起来,说话的声音立刻变成了低八度。
她把嘴巴凑近爹的耳边窃窃私语着,爹却似乎不知不觉地入了梦乡,夜已很晚了,爹早已疲惫不堪。
车厢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脸的困倦,唯有她仍显得激动和兴奋,她瞥瞥爹那副昏昏欲睡的样子,一种母性怜爱的表情掠过眉头,她伸展双臂搂住爹的肩膀,轻轻将爹的身子和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她自己则仰靠在椅背上,继续想心思,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进行着憧憬……
爹带个年轻女人来家,令吴为惊喜交集,哥的反响也不小。爹让吴为和哥叫她表姑,并说表姑要在家里呆好长时间,就像一家人那样子生活。吴为背地里问哥:“咋从来没听爹说有这么个姑姑呢?”哥的表情怪怪的,眼睛里充满了困惑和疑虑,他悄声地对吴为说:“等姐回来问问姐就知道了!”
爹让吴为和哥跟表姑睡一铺炕,自己搬到对面炕和库塞一起睡。吴为不乐意地嚷起来。他说自己从小就一直跟爹睡一个被窝儿,爹不搂他怕睡不着。表姑也不乐意,她极力支持吴为不让爹上对面炕去睡,要爹和吴为和她睡一铺炕,让哥和库塞睡一起。
哥冲表姑瞪了半天眼珠子,忽然大声质问她道:“那你咋不跟傻库塞睡?偏叫人家!”
爹听了不禁怒喝道:“铁柱,你少教!”
哥脾气近一两年变得越来越倔,爹的斥责反使他火气更盛,他不管不顾地喊叫:“那,那你们三个在一铺炕上咋睡?”
爹、吴为和表姑一时都为哥的表情和质问而愣住了。
爹的脸倏地红到了脖子根儿,吴为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只把一双迷惑的小眼睛在爹和表姑的脸上扫来扫去。
“嘿哟,铁柱,你这孩子咋突然关心起这事儿来啦?这还不简单嘛,我和你爹睡炕头炕稍,双柱睡中间,这样你爹不就可以继续搂双柱睡了吗?哦,如果你实在不愿意过去睡,咱一家四口就在一铺炕上睡,挤就挤一点吧!”表姑的表情轻描淡写,谈笑风生。
“谁,谁和你是一家人?你又不是我妈!”哥嘟囔道。
“铁柱,你找揍是吧?咋能这么跟姑姑说话!”爹立瞪起眼睛。
“哼,反正我不跟傻库塞睡,谁爱谁去!”哥愈发地犟。
吴为见状,懂事地道:“要不,我过去跟库塞睡吧!”
爹说:“不行,库塞睡觉毛愣,动不动就打把式,别砸着你。噢,还是我过去睡!”
爹说着便动手搬行李。吴为抱起爹的枕头道:“爹,要不咱俩都搬那炕睡呀?”
“算啦,你还是留这炕吧,库塞睡觉地方得大点,你过来就挤了!”
“那,那谁搂我呀?”吴为不禁撒娇。
“我搂你呗!”表姑一把将吴为拽进自己怀里。
吴为鼻子、嘴巴埋进表姑的胸膛,不禁被一股温暖、柔软的感觉所迷醉。他对这感觉感到朦胧、遥远、陌生。因此,似乎特别充满渴望和迷恋。他不自禁伸出双臂将表姑的腰搂住,鼻子、嘴巴不由得想往她的*里拱,想往她的乳峰上撞,但刹那间他却坚强地忍住了,他以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挣脱表姑的怀抱,模仿着大人的口吻坚定不移地道:“我长大了,我要自己睡!”
爹高兴地抚摸着他的头笑笑道:“呵呵,好小子,是该像个男子汉的样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