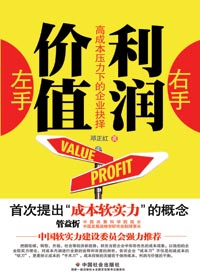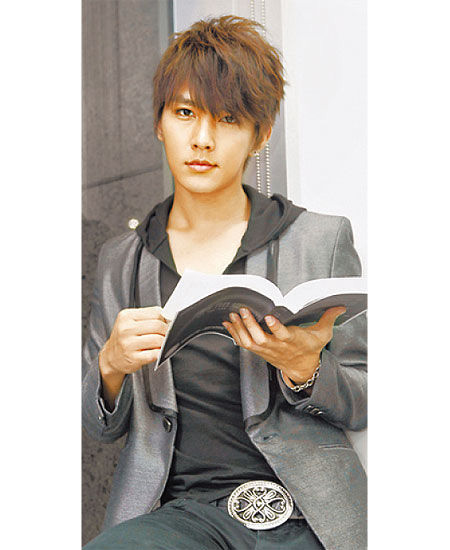左手倒影,右手年华-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叫莲花。
天 下(3)
我在十五岁之前杀人用的武器都是银针,淬过红莲汁液的剧毒。每次我用那些毒计划破对手颈部的动脉,然后我就会看见血喷洒而出的情景,像是风中弥漫的红色的尘埃,一点一点洒落在沙漠的黄沙之上,然后迅速被风吹干,被流沙淫没,没有痕迹。我曾经问过我的父亲,我说,父亲,我可以用银针轻易结束那些人的性命,为什么还要在针上淬毒。父亲望着地平线的方向,缓缓地说,因为不要给对手留下任何还手的余地,要置对方于死地。
父亲总是在黄昏的时侯弹奏他那张落满尘埃的六弦琴,声音苍凉深远,荡漾在暮色弥漫的大漠上,有时候会有远方的骆驼商旅的队伍经过,驼铃声从远方飘过来,同悠扬的琴声一起纠缠着在风中弥散。我问过父亲那是什么曲调,他告诉我那是我母亲写的词,曾经用江南丝竹每日每夜在他耳边弹唱。父亲总是用他苍凉而又有磁性的声音唱着那首江南小调:灯影桨声里,天犹寒,水犹寒。梦中丝竹轻唱,楼外楼,山外山,楼山之外人未还。人未还,雁字回首,早过忘川,抚琴之人泪满衫。扬花萧萧落满肩。落满肩,笛声寒,窗影残,烟波奖声里,何处是江南。
每次父亲唱着这首词的时侯,他总是泪满衣襟,我一直没有问他,他为什么不回到江南去,回到那个碧水荡漾的水上之城。我只知道父亲总会唱到太阳完全隐没在黄沙堆砌的地平线下,他才会小心地收好古琴,可是依然不擦去上面柔软的灰尘。然后他会在月光下舞剑,寂寞,可是梁驾;那些剑式他从来没有教过我,我看到月光下的父亲飞扬的黑色长袍和黑色凌乱的头发破口同一只展翅的鹰,月光沿着他脸上深深的轮廓流淌,弥漫在他的胸膛,腰肢;握剑的手指,最终融化在他黑如金墨的瞳仁中。
父亲告诉我,这个大漠看似平和,其实隐藏了太多的风浪。有太多杀手和刀客藏身于这个沙漠之中。我见过父亲说的那些沉默无语的刀客,他们总是蒙着黑色的头巾,孤独地穿行在这个滚烫的沙漠之上烈日之下,像是孤独但架驾的狼。他们的刀总是缠在黑色的布匹之中,背在他们身后。我曾经看见过一个刀客的刀法,快如闪电,而且一招毙命。那个刀客在对手倒下之后抬头仰望着天空,然后看到飞鸟疾疾掠过天空,杀,杀,杀。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个刀客,我想到我的父亲,花巫。
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他们的刀法全部没有来历,父亲对我说,因为他们的刀法和你的剑法——样,没有名字没有来历没有招数,只有目的,就是杀人。所以他们是这个沙漠中最危险的动物。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叫我去杀一队经过这片沙漠的刀客,七个人,全部是绝顶的高手。父亲把他的葬月剑给我,然后带我去了黄石镇,这个沙漠边唾惟一的小镇。
当我走在飞沙走石的街道上的时候,我感到一丝恐惧。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我从小就和父亲一起长大。没和第二个人有过语言上的接触。父亲将路边的小贩,老娘,f丐,垂望童子一指给我看,告诉我他们中谁是、杀手,谁是剑客,谁是平民。其中,父亲指着一个八岁左右的小男孩对我说,他是南海冰泉岛的小主人,中原杀手的前五十位。
当那条街走到尽头的时侯,我看到飞扬肆虐的黄沙纷纷扬扬地沉淀下来,黄沙落尽的尽头,是一家喧嚣的酒楼,我看到里面的七个刀客,其中最中间的一个,最为可怕。
父亲对我说,莲花,上去,然后杀死他们。
父亲说这句话的时侯像是对我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满脸平静,没有波澜。
后来那七个人全部死在我的手上,都是被我一剑划开了血管,鲜血喷洒出来。最后死的那个刀客是个面容瘦削的人,他一直望着我,在最后的时刻,他问我,花巫是你什么人。我在他的咽喉上轻轻放下最后一朵莲花,然后对他说,他是我父亲。然后我看见他诡异的笑容,这个笑容最终僵死在他的脸上,永远凝固了下来。
那天我和父亲离开的时候那家酒楼重新燃起了灯火,红色的灯笼在棍满黄沙的风申摇晃,父亲对我说,莲花;现在你是大漠中最好的杀手了,除了我,也许没有人可以再杀死你。
我望着手中的葬月剑,它雪白的光芒映痛了我的眼睛,它上面没有一滴鲜血,光洁如同像牙白的月亮,那么满那么满的月亮。
父亲离开黄石镇的时候将腰上的一块玉佩给了路边的一个小乞丐,我知道那块玉佩是上古的吉祥物,曾经被父亲用五干两银子买下来。我间父亲他为什么要给一个小乞丐。父亲对我说,因为他是个真正的乞丐。
天 下(4)
那天晚上回到家之后,父亲又开始抚琴,然后舞剑,黑暗中我可以听到剑锋划破夜色的声音,短促尖锐如同飞鸟的破鸣。那天晚上我又听到父亲在唱那首词:
灯影奖声里,天犹寒,水犹寒。梦中丝竹轻唱,楼外楼,山外山,楼山之外人未还。人未还,雁宇回首,早过忘川,抚琴之人泪满衫。扬花萧萧落满肩。落满肩,笛声寒,窗影残,烟波桨声里,何处是江南。
在我十八岁那年父亲对我说,我们离开大漠。
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要离开,离开他守望了十八年的飞鸟和荒漠;离开他的莲池,离开这里登峰造极的杀手地位。我对父亲说,父亲,我们离开就要放弃一切,你决定了吗?
父亲点点头,他说,因为我们要去找你娘,还有你哥哥。他的名字;也叫莲花。
父亲望着漆黑的天空说,因为那个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总是喜欢在莲调山庄内看扬花飘零的样子,无穷无尽,席卷一切。那些绵延在庄园中的细小的河流总是照出我寂寞的身影,其实很多时候我想找人说话,可是我每次接触陌生人的时候,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死他们。
每次当我用剑刺破他们的咽喉,我都很难过,像是自己在不断地死亡。
其实人不是到了断气的时候才叫做死亡的,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己经死亡,我像是木偶,破剪断了身后银亮的操纵我的丝线。
我总是梦见我的父亲,他和我的妹妹一起在大漠申生活,我梦见他英俊柴驾不驯的面容,黑色飞扬的长袍,和他凌乱的头发,如同我现在的样子。还有他身后的那把用黑色布匹包裹着的明亮长剑葬月。还有我的妹妹,莲花。她应该有娘年轻时倾城的容颜,笑的时候带着江南温柔的雾气,可是杀人的时候,肯定和我一样果断而彻底。
我的梦中有时候还有大火,连绵不断的大火烧遍了莲游山庄的每个角落。我在漫天的火光中看不到娘看不到我的唱月剑看不到山庄看不到江南,只看到死神步步逼近。
每次我挣扎着醒莱,总会看见婆婆慈祥的面容,她总是对我微笑,不说话。
婆婆陪我在莲调山庄里长大,小时候我就一直睡在婆婆的怀抱中。可是婆婆不会说话,她总是一直一直对我笑,笑容温暖而包容一切。我喜欢她的头发上温暖的槐花味道,那是我童年中掺杂着香味的美好记忆。
其实当我第一次用唱月剑的时侯我总是在想娘会不会要我杀婆婆,不过娘还是没有。也许因为婆婆不会武功,不能对我有所提高。
我总是对婆婆不断地说话,她是惟一个可以听我说话的人,因为她不能说话。很多次我都难过地抱着婆婆哭了,她还是慈祥地对我笑,我仿佛听见她对我说,莲花,不要哭,你要成为天下第一的剑客,你怎么可以哭。
婆婆教给我一首歌谣,她写在纸上给我看:
灯影奖声里,天犹塞,水犹寒。梦中丝竹轻唱,楼外楼,山外山,藏山之外人未还。人未还,雁字回音,早过忘川,抚琴之人泪满衫。扬花萧萧落满肩。落满肩,笛声塞,窗影残,烟波奖声里,何处是江南。
我不知道这首歌谣怎么唱,只是我喜欢把它们念出来,我总是坐在河边上,坐在飘飞着扬花的风里面念这首歌谣,它让我觉得很温暖。
从我十八岁开始,母亲总是在说着同一句话,她说,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
每次我间她约定是什么,她总是摇摇头,然后我就看见她深不可测却又倾国倾城的笑容。
天 下(5)
那天我去繁华的城市中杀一个有名的剑客,那个剑客是真正的沽名钓誉之徒。所以当我在客栈的酒楼上看见他的时候,我走过去对他说,你想自尽还是要我来动手杀你。那个人望着我,笑声格外嚣张,他说,我活得很好,不想死,而且还可以让像你这种无知的毛孩子去死。
我叹息着摇头,然后用桌上的三支筷子迅速地插人了他的咽喉。我看见他死的时候一直望着我身后的剑,我笑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想间我为什么不用剑杀你?他点点头。我说,因为你不配我的剑。
我又问他,你是不是很想看看我的lu?
他点点头,目光开始涣散。
于是我拔出了剑,白色如月光的光芒瞬间照亮了周围的黑色。然后我听见他喉咙中模糊的声音在说,原来你就是莲花。
我笑了,我说,对,我就是莲花。然后我将唱月剑再次刺进了他的咽喉,因为母亲告诉过我,不要给对手任何余地。当我看见他的血被红莲的剧毒染成碧绿之后,我将一朵红色的西域红莲放在他的咽喉上,转身离开。
当我走下采的时候我看到庭院中的那个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子,两个人都是黑色的长袍,飞扬的头发。那个男的柴驾不驯,那个年轻的女子背上背着一把用黑色布匹包裹的长剑。直觉上我知道他们的身分,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杀手。而且是一流的杀手。
我安静地从他们置之度外边走过去,然后我听到那个男人在唱一首词,就是婆婆教我的那首,我终于如道了这首词的唱那段旋律弥漫了忧伤,我仿佛看到江南的流水百转干回。
回到莲满山庄的时侯我看见母亲站在屋糖下,她望着s屋糖上的燕子堆起的巢穴,露出天真甜美如少女的笑容。呼唤她,我叫她,娘。
那天晚上我很久都没有睡着,我一直在想那个男人和,女子,我觉得我应该见过他们,因为他们的面容是那么熟可是我想不起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见过。那天晚上我唱起'个男人所唱的那首小调,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莲调山庄宙木和回廊间寂寞地飘扬,然后我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我们,看见母亲惊恃的面容,她望看我,急促地问,谁教的这首歌?她一把抓住我的衣襟,问我,告诉我,是谁?
我说,我不知道。
那天母亲离开的时侯,我听见她小声的低语,她说,乡的时间已经到了,原来你己经回来。
那天婆婆不知道是什么时侯站在我们身后的,当我转5时侯我就看见了她慈祥的面容,可是我第一次从她的面容看到无法隐藏的忧伤。
婆婆,你在担心什么呢?
父亲告诉我,其实现在的天下,只有江南和塞外这两1方,才有最好的杀手,所以我们要回到江南,而且,我N那里等我,还有我的哥哥,莲花。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娘,我哥哥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而且。我们彼此都没见过。父亲总是喜欢摸着我柔软的劈头发对我说,莲花,你娘和你一样漂亮,她的名字叫莲桨。
当我们到达江南小镇的时侯,己经是黄昏,有细雨开天空缓缓飘落。江南的雨总是温柔得不带半点萧杀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