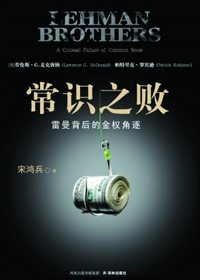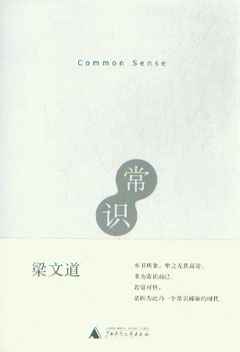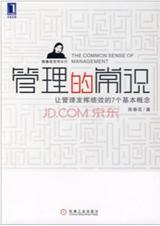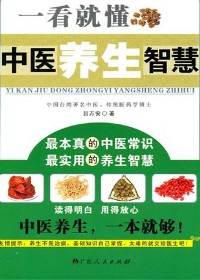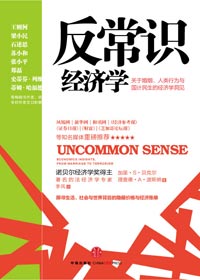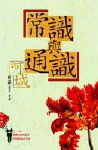常识-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叫不叫民主呢?假如我们宽泛地把民主界定为一种集体决策的方式,那么全民公投当然是民主的。这又算不算是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呢?那就要看它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了。如果这个社区的公投结果出来了,五成多的居民都选择了自杀,剩下那四成多的居民是否也该遵照民主原则跟着去死呢?当然不能,因为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再怎么讲究民主,也不能让其他人替我决定做人活着到底还有没有意义。这个例子当然很极端也很荒谬,现实里不可能有机会出现。可是我想用它说明的道理却适用于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上,那就是北京酒仙桥“危改拆迁”的全民公投事件。
居民迁拆是近年中国面对的一大社会问题,许多矛盾和冲突都来自政府和发展商的权力过大,而最受到影响的居民则根本没有说话表态的机会。其实整部人类城市空间发展史就是一个权力分配与斗争的历史。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笼罩下,哪些建筑应该拆掉建新楼,哪些人可以住进城中心,几乎全是国家机器由上而下的“神目式”(God'sview)规划观与资本的逻辑来决定的。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居民参与的规划方式开始在西方兴起。许多城市都有过成功的经历,既能民主地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也能在维护老区和城市更新之间找到平衡之道。今天的中国,最宜大规模地引进这套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规划方式。
然而在酒仙桥这个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改拆迁”工程里,发展商和当地政府部门却破天荒地想到了“全民公投”这一招,让居民决定要不要接受当局提出的方案,是该搬还是不搬。很多人都说这只是“表面民主”甚至“假民主”,把原以为会博得一片掌声的当局骂得十分不堪。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民主真假的问题,而是投票这种决策手段适用范围的问题,例如个人房产的归属到底可不可以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集体来决定呢?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更深层也更根本的概念,那就是权利了。现代权利观其实包括了一揽子的基本人权,其中最核心的自然是一个人对自身生命和身体的自主权,由之派生的最重要权利则是财产权了。但在现代民主运动史上,财产权起到的作用反而更大。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构思的契约论,就是假设人民为了维护自己身家性命和产业的安全,才愿意把部分权力让渡给君主与国家。
而在实践上,现代民主强调的人人平等则是来自罗马法有关财产的规定,中古封建时代延续了这套规定,保证有田土的领主也拥有相应的司法地位和政治权利,使得后来迫使英国国王签署《大宪章》的贵族们有理有据。总而言之,财产权是一种核心人权,不能被人用“民主”
的方式削夺,因为它正是民主的基础之一。
因此,用公投决定一个区的居民接不接受拆迁,其荒谬程度仅次于用公投来决定大家要不要自杀。酒仙桥“危改拆迁”事件是一个上好的教科书案例,可让大家上一堂人权课。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6月21日投票(二):不是民意的表达,而是民意的决定平均一个星期就会接到一次这样的电话录音:“你好,我们是××报业的调研中心,现正进行一次电话民意调查……”每一次我都立刻挂机。如果是真人打来的,我也总是有现成的理由拒绝:“对不起,我在媒体工作,按照问卷调查的常规,是不能接受访问的。”
活在香港,有哪一个人没碰到过这类调查?香港人每天都在发表意见,而且是对每一项事物都有意见。民意调查已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这周日就是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日。据调查显示,这一届的投票率有可能会比上一次低。一位茶餐厅的茶客告诉我:“那是因为民意调查做得太多。既然我们的意见早就被反映过了,干嘛还要去投票呢?”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教书时,一个学生的疑问:“如果民意调查做得够科学,那种针对单项议题的公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其实,各国大选的票站出口调查早就准确得渐渐迫近真实的选举结果,会不会真有这么一天,民调成为民主制度的主要工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绕个大弯,谈谈所谓的“网络民意”。
近年来,内地许多政府部门纷纷在网络上公开征求人民的意见。各地各级官员领导,也不时上网会会网民,回答几条网友提问。我真心相信,他们平常有空是会上网的,浏览各大论坛,看看热议话题,观察网友的思绪和倾向。这是不是件好事呢?当然是好事。只不过,所谓的“网友热议”其实也可能是个迷思。网络论坛里往往是看的人多,留言的少;而且是极少。且以知名博客和菜头为例,他说:“以我的Blog为例,日均访问量是一万个独立IP,这意味着每天有一万个人来访问。在这一万人里,回帖发表意见的人有多少?平均每天不超过100帖,也就是说只有1%不到的人会参与讨论。”如果仔细查看所有网络论坛上最受追捧最受争议的帖子,我们将不难发现部分网民其实都是沉默的潜水艇。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但是他们不说话。潜水艇为什么不浮出水面呢?有可能是觉得想说的话都已经被别人说完了,也有可能只是没兴趣,或者懒得打字。至于那些留了言的,不管他是片言只语还是长篇大论,则一定是比较有情绪有意愿也比较有闲的人。真能把后者的话当成前者的心声,以部分网民的留言为全体网民的民意吗?然而,我们还是很笼统地说“网民认为××××”。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找出一套工具去精准地分析网民留言,从里头萃取出全民的意志。也许有一天,民意调查的方法已经进步到了误差极少极少的地步,不用投票,我们就知道选举的结果。
即便如此,选举还是必要的。因为投票和民调的分别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本质的。人的意见浮动不居,今天喜欢吃苹果,说不定明天就爱吃橘子了。对于一项公共议题,刚开始,我可能有一个粗糙的感觉,所以我的反应也是初步的。等到后来消息更多,所知更全,我的立场可能就不同了。而民意调查总是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至于投票,则是这个过程的决断时刻。面临一次投票,我必须很自觉地主动搜集资讯主动思考辨析,因为我知道它不是简单的意见表达,而是一次决定性的抉择。餐馆点菜,餐牌刚到手,你大可以左挑右选自言自语,但是当侍者记下菜名转身而去时,一顿饭的好坏就这么定下来了。菜不好吃可以退回去,但选出来的人不理想,就只能等下回了。
马英九现在的民意再低,台湾人也不能叫他随便下台;当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不顾高达七成的反对民意,悍然出兵伊拉克,英国人能奈他何?除非发动罢免,而那是另一次的决断了。为什么选票常被认为是“神圣”的?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你必须承担后果的决定,它不是你兴之所至的一句感叹一则留言。“尊重民意”和“人民决定”的政治之不同,就在于前者的人民其实不必负责,后者的人民却要背上千斤重担。
尊重民意的施政当然很民主,但它和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恐怕还是不同的。所以我对那位声称不必投票的茶客说:你这周日还是要去投票的,除非你觉得不用负责的人生真是幸福真是轻松,只想当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看客;又或者你认为代议政制还不够民主,那么就该站出来大声要求更激进的民主实践。
原题为“投票不只是为了表达民意”,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4日27历史:一种中国式宗教的衰亡中国国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等八项教条在内的“八荣八耻”,目的是要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一时之间,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八荣八耻”这个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这样的道德信条,学习这样的“中央精神”,背景当然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得可以;为官的欺上瞒下,贪污不过百万不成新闻;经商的不信不实,伪劣仿冒几如必然常态;至于所谓的“重大”工业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征地,更是无日无之。“旧社会”的四维八德和各种传统宗教给摔了个稀巴烂,“新中国”倡导的马列主义价值观则沦为口号,中国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闻了。
美籍印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曾在其名着《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有自己的文化网络,调节了各方的权力,维持了民间村社的自行运转。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深入拓展到各个地方,却出现了“政权内卷化”的现象;也就是国家政权愈是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地方的社会愈是破败,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网络失效,政府的威权取代了传统士绅族长赖以维持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比如说关帝。崇拜关帝不只是民间的“迷信”,也是传统帝国认可的行为;对种地的农民来说,关帝可保风调雨顺;对皇权来讲,关帝是忠君价值的终极体现。政府不只不破坏民间的祭祀结社,反而积极介入出一把力,于是一个关帝,政府民间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历史人物关羽演变为神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挥宗教作用的经典示范。一般不识字的百姓或许看不懂《三国志》,但是尊崇汉蜀的小说《三国演义》却能透过戏曲等各种民俗文艺,把一套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物角色与是非判断灌注到帝国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荣辱观”,他只需要认可早在民间流传的人物典型和正统的历史观。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惹起了中国知识界和网民的激烈争论。这部电视剧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为他率军攻克郑成功后人治下的台湾,“维护了民族的统一,神圣领土的完整”。这样的主调当然会引来非议。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数地区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称作“汉奸”。因为他曾两度背叛南明王室,先随郑成功抗击清军,最后又倒向满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后据点台湾。其次,郑成功是两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连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么该置郑成功于何地呢?第三,郑成功现在也被台独抬作建国先祖,施琅则是他们贬损的“小人”。中央台这套剧集针锋相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此剧最早的倡导者陈明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讳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
关于施琅的历史定位,可以牵扯到中国历史“正统”观的理解,和民族主义形成的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在这里说清楚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件事来侧击中国社会价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传统史学作用的沦丧,和独立知识分子的缺席。
我们先要了解,满清对于向自己投诚的明室旧臣并不客气,干隆41年甚至编纂了《贰臣传》甲乙两篇,列出了157个“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