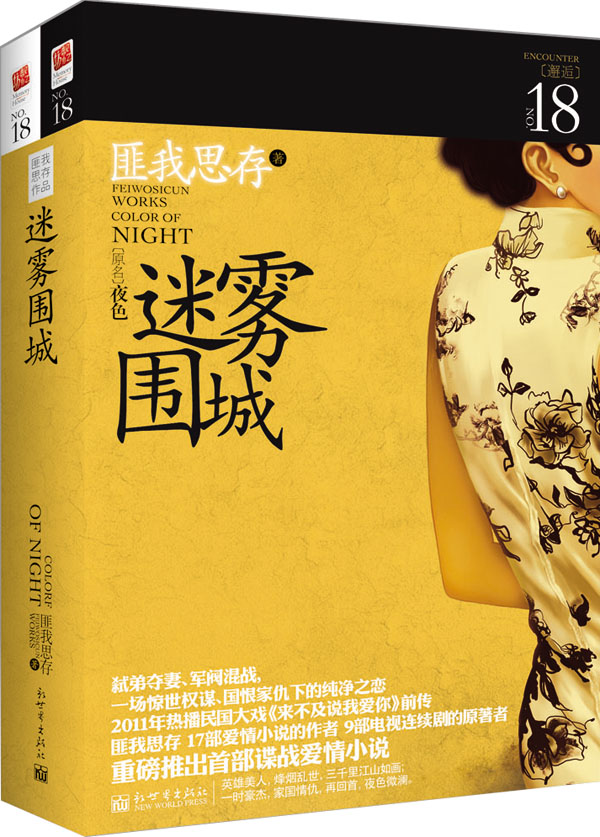围城-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直到车开,偷眼望见那寡妇也有了位子,才算心定。
车下午到宁都。辛楣们忙着领行李,大家一点,还有丙件没运来,同声说:“晦气!这一等不知道又是几天。”心里都担忧着钱。上车站对面的旅馆一问,只剩两间双铺房了。辛楣道:“这哪里行?孙小姐一个人一间房,单铺的就够了,我们四个人,要有两间房。”孙小姐不踌躇说:“我没有关系,在先生方先生房里添张竹铺得了,不省事省钱么?”看了房间,搁了东西,算了今天一路上的账,大家说晚饭只能将就吃些东西了,正要叫伙计忽然一间房里连嚷:“伙计!伙计!”带咳带呛,正是那寡妇的声音,跟着大吵起来。仔细一听,那寡妇叫了旅馆里的饭,吃不到几筷菜就心,这时候才街道菜是用桐油炒的;阿福这粗货,没理会味道,一口气吞了两碗饭,连饭连菜吐个干净,“隔夜吃的饭都吐出来了!”寡妇如是说,仿佛那顿在南城吃的饭该带到桂林去的。李梅亭拍手说:“真是天罚他,瞧这浑蛋还要撒野不撒野。这旅馆里的饭不必请教了,他们俩已经替咱们做了试验品。”五人出旅馆的时候,寡妇房门大开,阿福在床上哼哼唧唧,她手扶桌子向痰盂心,伙计一手拿杯开水,一手拍她背。李先生道:“咦,她也吐了!”辛楣道:“呕吐跟打呵欠一样,有传染性的。尤其晕船的时候,看不得人家呕。”孙小姐弯着含笑的眼睛说:“李先生,你有安定胃神经的药,送一片给她,她准——”李梅亭在街上装腔跳嚷道:“孙小姐,你真坏!你也来开我的玩笑。我告诉你的赵叔叔。”
晚上为谁睡竹榻的问题,辛楣等三人又谦证了一阵。孙小姐给辛楣和鸿渐强逼着睡床,好像这不是女人应享的权利,而是她应尽的义务。辛楣人太高大,竹榻容不下。结果鸿渐睡了竹榻,刚夹在两床之间,躺了下去,局促得只想翻来覆去,又拘谨得动都不敢动。不多时,他听辛楣呼吸和匀,料已睡熟,想便宜了这家伙,自己倒在这两张不挂帐子的床中间,做了个屏风,替他隔离孙小姐。他又嫌桌上的灯太亮,妨了好一会,熬不住了,轻轻地下床,想喝口冷茶,吹来灯再睡。沿床里到桌子前,不由自主望望孙小姐,只见睡眠把她的脸洗濯得明净滋润,一堆散发不知怎样会覆在她脸上,使她脸添了放任的媚姿,鼻尖上的发梢跟着鼻息起伏,看得代她脸痒,恨不能伸手替她掠好。灯光里她睫毛仿佛微动,鸿渐一跳,想也许自己错,又似乎她忽然呼吸短促,再一看,她睡着不动的脸像在泛红。慌忙吹来了灯,溜回竹榻,倒惶恐了半天。
明天一早起,李先生在账房的柜台上看见昨天的报,第一道消息就是长沙烧成白地,吓得声音都遗失了,一分钟后才找回来,说得出话。大家焦急得没工夫觉得饿,倒省了一顿早点。鸿渐毫没主意,但仿佛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跟着人走,总有办法。李梅亭唉声叹气道:“倒霉!这一次出门,真是倒足了霉!上海好几处留我的留我,请我的请我,我鬼迷昏了头,却不过高松年的情面,吃了许多苦,还要半途而废,走回头路!这笔账向谁去算?”辛楣道:“要走回头路也没有钱。我的意思是,到了吉安领了学校汇款再看情形,现大不用计划得太早。”大家吐口气,放了心。顾尔谦忽然明地说:“假如学校款子没有汇,那就糟透了。”四人不耐烦地同声说他过虑,可是意识里都给他这话唤起了响应,彼此举的理由,倒不是驳斥顾尔谦,而是安慰自己。顾尔谦忙想收回那句话,仿佛给人拉住的蛇尾巴要缩进洞,道:“我也知道这事不可能,我说一声罢了。”鸿渐道:“我想这问题容易解决。我们先去一个人。吉安有钱,就打电报叫大家去;吉安没有钱,也省得五个人全去扑个空,白费了许多车钱。”
辛楣道:“着呀!咱们分工,等行李的等行李,领钱的领钱,行动灵活点,别大家拚在一起老等。这钱是汇给我的,我带了行李先上吉安,鸿渐陪我走,多个帮手。”
孙小姐温柔而坚决道:“我也跟赵先生走,我行李也来了。”
李梅亭尖利地给辛楣一个X光的透视道:“好,只剩我跟顾先生。可是我们的钱都充了公了,你们分多少钱给我们?”
顾尔谦向李梅亭抱歉地笑道:“我行李全到了,我想跟他们去,在这儿住下去没有意义。”
李梅亭脸上升火道:“你们全去了,撇下我一个人,好!我无所谓。什么‘同舟共济’!事到临头,还不是各人替自己打算?说老实话,你们到吉安领了钱,干脆一个子儿不给我得了,难不倒我李梅亭。我箱子里的药要在内地卖千反块钱,很容易的事。你们瞧我讨饭也讨到了上海。”
辛楣诧异说:“咦!李先生,你怎么误会到这个地步!”
顾尔谦抚慰地说:“梅亭先生,我决不先走,陪你等行李。”
辛楣道:“究竟怎么办?我一个人先去,好不好?李先生,你总不疑心我会吞灭公款——要不要我留下行李作押!”说完加以一笑,减低语意的严重,可是这笑生硬倔强宛如干浆糊粘上去的。
李梅亭摇手连连道:“笑话!笑话!我也决不是以‘不人之心’推测人的——”鸿渐自言自语道:“还说不是”——“我觉得方先生的提议不切实际——方先生,抱歉抱歉,我说话一向直率的。譬如赵先生,你一个人到吉安领了钱,还是向前进呢?向后转呢?你一个人作不了主,还要大家就地打听消息共同决定的——”鸿渐接嘴道:“所以我们四个人先去呀。服从大多数的决定,我们不是大多数么?”李梅亭说不出话,赵顾两人忙劝开了,说:“大家患难之交,一致行动。”
午饭后,鸿渐回到房里,埋怨辛楣太软,处处让着李梅亭:“你这委曲求全的气量真不痛快!做领袖有时也得下辣手。”孙小姐笑道:“我那时候瞧方先生跟李先生两人睁了眼,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气呼呼的,真好玩儿!像互相要吞掉彼此的。”鸿渐笑道:“糟糕!丑态全落在你眼里了。我并不想吞他,李梅亭这种东西,吞下去要害肚子的——并且我气呼呼了没有?好像我没有呀。”孙小姐道:“李先生是嘴里的热气,你是鼻子里的冷气。”辛楣在孙小姐背后鸿渐翻白眼儿伸舌头。
向吉安去的路上,他们都恨汽车又笨又慢,把他们跃跃欲前的心也拖累了不能自由,同时又怕到了吉安一场空,愿意这车走下去,走下去,永远在开动,永远不到达,替希望留着一线生机。住定旅馆以后,一算只剩十来块钱,笑说:“不要紧,一会儿就富了。”向旅馆账房打听,知道银行怕空袭,下午四点钟后才开门,这时候正办公。五个人上银行,一路留心有没有好馆子,因为好久没痛快吃了。银行里办事人说,钱来了好几天了,给他们一张表格去填。辛楣向办事讨过一支毛笔来填写,李顾两位左右夹着他,怕他不会写字似的。这支笔写秃了头,需要蘸的是生发油,不是墨水,辛楣一写一堆墨,李顾看得满心不以为然。那办事人说:“这笔不好写,你带回去填得了。反正你得找铺保盖图章——可是,我告诉你,旅馆不能当铺保的。”这把五人吓坏了,跟办事员讲了许多好话,说人地生疏,铺保无从找起,可否通融一下。办事员表示同情和惋惜,可是公事公办,得照章程做,劝他们先去找。大家出了银行,大骂这章程不通,骂完了,又互相安慰说:“无论如何,钱是来了。”明天早上,辛楣和李梅亭吃几颗疲乏的花生米,灌半壶冷淡的茶,同出门找本地教育机关去了。下午两点多钟,两人回来,头垂头气丧,精疲力尽,说中小学校全疏散下乡,什么人都没找到,“吃了饭再说罢,你们也饿晕了。”几口饭吃下肚,五人精神顿振,忽想起那银行办事员倒很客气,听他口气,好像真找不到铺保,钱也许就给了,晚上去跟他软商量罢。到五点钟,孙小姐留在旅馆,四人又到银行。昨天那办事员早忘记他们是谁了,问明白之后,依然要铺保,教他们到教局去想办法,他听说教育局没有搬走。大家回旅馆后,省钱,不吃东西就睡了。
鸿渐饿得睡不熟,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公事皮包,几乎腹背相贴,才领略出法国人所谓“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还不够亲切;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长得像失眠的夜,都比不上因没有面包吃而失的夜那样漫漫难度。东方未明,辛楣也醒,咂嘴舐舌道:“气死我了,梦里都没有东西吃,别说桓的时候了。”他做梦在“都会饭店”吃中饭,点了汉堡牛排和柠檬甜点,老等不来,就饿醒了。
鸿渐道:“请你不要说了,说得我更饿了。你这小气家伙,梦里吃东西有我没有?”辛楣笑道:“我来不及通知你,反正我没有吃到!现在把李梅亭烤熟了给你吃,你也不会嫌了罢。”鸿渐道:“李梅亭没有肉呀,我看你又白又胖,烤得火工到了,蘸甜面酱、椒盐——”辛楣笑里带呻吟:“饿的时不能笑,一笑肚子愈掣痛。好家伙!这饿像有牙齿似的从里面咬出来,啊呀呀——”鸿渐道:“愈躺愈受罪,我起来了。上街达一下,活动活动,可以忘掉饿。早晨街上清静,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辛楣道:“要不得!新鲜空气是开胃健脾的,你真是自讨苦吃。我省了气力还要上教育局呢。我劝你——”说着又笑得嚷痛——“你别上毛,熬住了,留点东西维持肚子。”鸿渐出门前,辛楣问他要一大杯水了充实肚子,仰天躺在床上,动也不动,一转侧身体里就有波涛汹涌的声音。鸿渐拿了些公账里的作钱,准备买带壳花生回来代替早餐,辛楣警告他不许打偏手偷吃。街上的市面,仿佛缩在被里的人面,还没露出来,卖花生的杂货铺也关着门。鸿渐走前几步,闻到一阵烤山薯的香味,鼻子渴极喝水似的吸着,饥饿立刻把肠胃加紧地抽。烤山薯这东西,本来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偷着不如偷不着,”香味比滋味好;你闻的时候,觉得非吃不可,真到嘴,也不过尔尔。鸿渐看见一个烤山薯的摊子,想这比花生米好多了,早餐就买它罢。忽然注意有人正作成这个摊子的生意,衣服体态活像李梅亭;他细一瞧,不是他是谁,买了山薯脸对着墙壁在吃呢。鸿渐不好意思撞破他,忙向小弄里躲了。等他去后,鸿渐才买了些回去,进旅馆时,遮遮掩掩的深怕落在掌柜或伙计的势利眼里,给他们看破了寒窘,催算账,赶搬常辛楣见是烤山薯,大赞鸿渐的采办本领,鸿渐把适才的事告诉辛楣,辛楣道:“我知他没把钱全交出来。他慌慌张张地偷吃,别梗死了。烤山薯吃得快,就梗喉咙,而且滚热的,真亏他!”孙小姐李先生顾先生来了,都说:“咦!怎么找到这东西?妙得很!”
顾先生跟着上教育局,说添个人,声势壮些。鸿渐也去,辛楣嫌他十几天不梳头剃胡子,脸像剌猥头发像准备母鸡在里面孵蛋,不许他去。近中午,孙小姐道:“他们还不回来,不知道有希望没有?”鸿渐道:“这时候不回来,我想也许事情妥了。假如干脆拒绝了,他们早会回来,教育局路又不远。”辛楣到旅馆,喝了半壶水,喘口气,大骂那教育局长是糊涂鸡子儿,李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