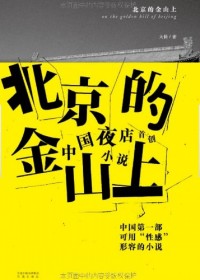北京,这个冬天风不大-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一天一大早,四郎突然间很神秘对着我发笑,说昨天晚上他们什么什么,支支吾吾,欲言又止。我刹那明白,从那天起,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处女和一个处男。望望周围,那些年轻的容颜还是那么灿烂,丁香花的香气弥漫了教室。只是忽然之间,我觉得这个世界一下黯淡了许多。看看班花,她安静地坐着,长发披肩,那张美丽的脸稚气未脱,我不由发出一声少年老成的慨然长叹。
多年以后当我生命中第一次进入一个叫小诗的女孩身体时,我忽然间想到了班花。在骤然疼痛的刹那,她在想什么,抑或什么也没有想?
四郎后来频频告诉我他们做了多少多少次,我都有点腻了。但班花的学习成绩却是在直线下降。她本来是班里的尖子生,被家长和班主任都寄予厚望。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在四郎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从此拐了个弯。花朵过早地凋谢了,谁会在那刻流一滴清澈的眼泪?
此刻四郎不知道又在哪个女人那里鬼混,而班花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听说生活很不幸福。毕业后的第二年,她就嫁人了,我隐隐约约听说似乎是跟堕胎有关。我们上学的那个城市不大,这件事的真实性不容怀疑。所以也就很容易理解四郎一毕业就背井离乡了。班花美丽的长发成了我年少时的一个梦,远去了,一切都远去了。
抚摩着杜若光滑的侗体,我不知道明天又将怎样。亲爱的,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将离开你,你会原谅我吗?杜若,杜若……我呼唤着她的名字,手轻轻地在她的身上划动,缓缓地攀上了她的双峰。杜若又开始轻轻地呻吟起来。
如果杜若知道我每次和她上床时,还想着大学女友薇子,还有一个长发女孩小诗的话,她一定不会让我再碰她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无法忘记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月色明亮,夜色下的黄河泛着微微的波浪。我用几张报纸铺在沙滩上,让小诗躺在上面。小诗的身体绵软无力。我呼吸急促,颤抖着手摸遍了她的全身。她的身下潮湿,胸脯起伏,全身发烫。我摸索了半天才进入她身体,用力一顶,小诗骤然发出一声惨叫,那种疼痛让我一下恐慌。那一刻我的脑海中忽然闪过班花,闪过年少时一个悠远的梦,以及一些疼痛,浮浮沉沉,遥遥远远……
后来和我发生过关系的几个女孩,没有一个人像小诗那样惨叫过。所以那一夜在我的影响中极为深刻。那是我的第一次,用我的力量捅破那层膜,我变成了一个男人。但那个女孩却不是我的女友薇子,而是另一个诗社会员小诗。我们仅仅认识了不到一个月,她就成为了我和薇子爱情的牺牲品。
年少时,爱情是一场阴差阳错的游戏,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珍惜对方。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我牵着女友薇子的手漫步在校园的许多角落,在那里写下我们曾经清澈如水的爱情以及誓言。月亮躲到云后的时候,我们慌张的将两片颤抖的唇凑到一起,留下一些含混不清的昵喃,随后消散在风中。那个时候薇子的长发飘飘,白衣如雪,牵引着我的视线走过校园的林阴道,我们的青春如花一样灿烂。
我只能一再
请你相信我
那曾经爱过你的人就是我
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苍凉的远方
我和你的爱情在四季传唱
那时候,我们对爱情都笃信不疑。就在学校解放碑的台阶上,我们四目相对,心手相映。我天真地对薇子许下诺言,五年后,我将娶你做我的新娘……
青春依旧,而誓言如风一样消逝,谁能记得?谁能从岁月的河里捞起一把青涩的记忆,细细捋过?
多年以后,当我已经在社会的洪流中头破血流,偶尔回首,前尘往事如水一样浮上心头。
那个时候我每每想起薇子,想起小诗,想起那些渐行渐远的青春往事,不由的顿生一种忧伤。薇子和小诗的面容在我的脑海中一样的模糊,一样的遥远和不可琢磨,我不知道她们的生活过的究竟如何,是否幸福。但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忽然间又会变的异常的透明,忍不住在心底里想为她们遥遥的祝福。
小诗是个好女孩,单纯而可爱。人虽不漂亮,个也不高,但有一头很漂亮的长发,身上总是会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凑到她身边闻她的味道。小诗开玩笑说,王愚是条狗,我笑着继续嗅嗅鼻子,迷醉在那种少女的体香中,借以忘了疼痛。她爱做梦,常常给我描述各种各样的梦境,听得我很不以为然,心里暗笑不已。那时候的她还很喜欢写一些很伤感的诗和散文,并且聪明绝顶,我之所以注意到是因为有一次在诗社闲聊,她居然一字不差地给我背诵了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让我惊讶不已,不由得对她另眼相加。而我就那样不经意地伤害了她……
对不起,小诗,我心里默默地说。
正当我和杜若使劲地折腾着,手机不合适宜地响起,我拿起一看,是四郎打来的。
这家伙一点也没想到此刻我正在杜若的身上。用他的大嗓门嚷着:“兄弟,快点来happy啊,我给你介绍个美女,身材……”
我没等他说完就挂电话了。杜若果然听到了,她的表情一下变的坚硬。我还想讨好她,鼓捣了半天,却不见她有一点反应,只好翻身下来。杜若给我一个背影,不理我了。
我点着一支烟,外面下雨了,滴答滴答,一滴一滴,都像掉在心上。天很黑,烟头明明灭灭。
第一部分北京,这个冬天风不大(第8节)
8
如果一个乞丐手里突然有20万,他会做什么?
我打电话问刚去深圳找工作的朋友老谋。研究生刚毕业的他在那里饱受打击,雄心已经被打击殆尽。他显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抛给他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想也没想就说出了答案,先去吃顿大餐。那吃完大餐呢?
第三天,老谋就已经到北京,听完我创业的打算,他马上就决定过来了。他比我想像得还要狼狈。找到我的时候,身上居然只剩几个钢蹦。存折上,也不到1000块钱了,真难想像如果不是我要他来北京,他如何在深圳继续生存下去。但现在,他已经是我的同志了。
我能走多远,取决于和我一起走的人,那位前辈忠告我。
大学四年,再加我毕业这几年,我们是始终如一的朋友。如果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还有为数不多可以信赖的朋友的话,老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身上都还依然残存着文人的那点傲骨。所不同的是,他一直在校园里,用四郎后来初次见他的评价说,有点书呆子气;而我,多的是久入社会的一种成熟和圆润罢了。
当年在学校诗歌学会的时候,老谋是社长,我是主编。他因做事富于逻辑,善于谋算,而被所有的小辈戏称为老谋,他欣然接受,真名反而很少有人叫了。我们用青春的激情将那个几乎濒临关门的诗社搞的红红火火。图书馆门前的梧桐树下,几盏蜡烛,两把吉他,音乐和诗歌共舞,月亮与灯光一色。梧桐诗会一度倾倒无数的校园学子。老谋倾情朗诵他的代表作《黄河之春》,引得无数小女孩对他含情脉脉。在1999年的那个夏天,我们即将毕业。作为我们大学时代的告别演出,由我们策划并自导自演的音乐诗歌剧《时光里的逝者》,在学校的汇演中,引起轰动。列席的一些当地文坛泰斗和校领导对我们褒奖有加,这也成为很多年后关于校园生活最得意的回忆。
我一直幻想,在我们都步入社会之后,还能像当初在校园里一样,为了一个梦想而同心协力,矢志不渝。老谋深以为然。
猪头老总对我的工作越来越不满。他当然不可能想到我利用上班时间,已经为自己开公司做了大量的准备,他要我准备的和那家公司的合作情况,我都是应付了事。好多次我犹豫着想跟他彻底摊牌辞职。创业的激情燃烧着我,我几乎已经没有心思放在公司的工作上了。
可是,你能对一个器重了你一年时间,对你深信不疑的人说不吗?四郎一直说我成不了大事,他说我心肠比较软,缺乏做大事的那种狠,一将功成万骨枯,四郎总是给我灌输这样的思想。我大笑着不听。
老谋来了之后,帮我分担了一下开公司的准备工作,我稍微将王朝假日旅行社的工作抓了一下,加了两天班提交了一个工作计划,老总基本满意。但是接下来跟那家软件公司的谈判,陷入了始料不及的艰难。那家公司的野心比我们想像的要大,他们坚持说在电子商务方面,他们比我们有经验,有技术,要求控股。这显然是笑话。离开了行业背景的电子商务,只会是无源之水,连生存都成问题了,又何来优势。如果王朝假日旅行社不给他们提供欧洲旅游资源,他们还做个屁的欧洲旅游电子商务。
一连几天,在谈判桌上我说的口干舌燥,却毫无进展。我甚至冒出个想法,把我以前认识的很多IT高手召到王朝假日旅行社来,给我们股份,自己开发一套系统好了。但忍住了没说。这个想法说出来,老总会开始不信任我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有的人都会这么想。
老谋的到来也给我带来了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这更让我烦躁。
再跟薇子决裂之后,我还跟另外一个女孩梅有过短暂的相处,但那不是恋情,只是一种惺惺相惜的知遇感觉,可以说,这个女孩是我最好的红颜知己。梅大学毕业之后去澳大利亚留学。老谋说他听人传言梅在墨尔本的高速路上出了车祸,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已经被学校送回国,现在全身打了石膏,几乎一动都不能动,在床上躺了大半年了。
听了我立即给梅打了电话,当梅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时,半天没反应过来,我听到了她无声的抽泣。我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她,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静静地陪着她沉默:“我……”我说:“梅,梅……你还好吧?”
往事大段大段地涌来,纷乱而又清晰,疼痛而又迷茫……
一切恍然如隔世,记忆在这个时刻突然苏醒。我看到很多年前的一个电话厅旁,我第一次看见梅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看到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里,梅一小口小口地吃着那碗面条;我看到老谋在林阴道上拦住了梅,说我想认识她;我看到自己微醉着在她们的宿舍楼下前言不搭后语地给她唱着一首忧伤的歌谣……
跟梅的认识,与我的大学女友薇子分手有关。
1999年初,冬天的北方寒风异常凌厉,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校园里的男男女女一如既往。世纪末的大学生谈论着十字连星的预言、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以及其他诸如考研、工作、性等司空见惯的话题。而毕业班的老大哥老大姐们都是一脸的悲天悯人状。我们的大学生涯即将结束于这个世纪。世纪交替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