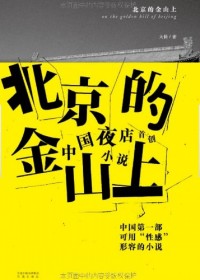北京,这个冬天风不大-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石膏,全身几乎坚硬,看到我进来梅似乎想动一下,但胳膊和腿只是象征性的稍微动了一下,就再也无力挪动一点点了。我的心里一痛,几乎不忍目睹。
梅艰难的用头部示意:“这是老段,专门来看我的。”旁边那个男人那张一看就被岁月打磨得很沧桑的脸上挂满笑容,站起来伸出他的大手说:“我叫段伟业,听梅说过你很多次。”我一时还搞不清楚老段是何许人,冲他点头笑笑。
快到吃饭时间了,阿姨叫我和老段帮忙,把梅扶起来靠在床上。阿姨说现在已经好一点,在别人的帮助下可以坐起来,最严重的时候连坐都坐不住了。阿姨不好意思地说我姑娘的手端不住碗,还得我自己喂她,你们都是她的好朋友,就自己吃吧,我不招呼你们了。
看着阿姨把肉撕得很碎一点点地喂梅,而梅艰难地张开嘴巴,慢慢地嚼动。梅很想自己吃,可是她的手指头把筷子夹住,几乎一点力都使不上。我不忍看下去。阿姨做的饭菜很香,我却无法下咽,心里在使劲地翻腾。我一下明白梅为什么会给我那个绝望无比的电话,说她如果能动一点点,她就会选择死亡。
死亡,这个词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
我对死亡的最初认识源于一个仅仅抱过我几次的爷爷,那时候我也就10岁左右的样子,那个我父亲的爸爸也就是我所谓的爷爷,据说因为我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叔叔的不孝顺,在一个夜里喝下了30片果刀片,然后在经历了数十次滔滔不绝的宣泄后,年事已高的爷爷终于用一种他所认为的理想方式结束了自己。我被父亲从学校里揪回来参加了葬礼,我看到爷爷在照片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下面的一大群人痛苦失声,长须拂然,眼睛中有种冷冷的光。
那时候我终于知道生命原来也可以就这么消失。很多年后我挖空心思的想写点文章来纪念一下并没有多少记忆的爷爷时,常常想起来的一句话是:爷爷那天走了,天下着雨。是的,那天下着雨,我穿着薄薄的雨衣跪在地上,一边在想,原来死亡就这么回事啊,挺没劲的。
留着一副长须的爷爷临走前,就这样让我完成了对死亡最启蒙的认识,那时候,我很幼稚,不,是很幼小。我于是知道人可以在不想活的时候结束自己,就像我已经死去的爷爷一样,还不知道原来有时候你有结束的勇气,却没有结束的力量。这是幸耶不幸?再后来我开始越来越多的认识了死亡。初中的时候,一个和我同名但字不同的同学在三天之内就因为肿瘤去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之前的几天我们还在一起打篮球;上高中的时候,一个据说常常猥亵低年纪女生的小色鬼去一个湖里游泳,跳下去后就再没上来;大二那年,英语系的一个帅哥因为失恋,在黄河边拉着变心的女友完成了一部黄河绝恋,双方家长在黄河边哭声震天……
生命犹如一根脆弱而坚强的芦苇,在岁月的风里左右摇摆,不知道谁会在下一个时刻,突然从你的眼前消亡?
此刻我看着梅,不仅打了一个冷战,情不自禁地想,幸好梅无法动弹一点点,否则……
梅一动也不动,静静地躺在床上,如花的生命在十月的阳光下黯然开放。阿姨说她求神拜佛,祈愿梅好起来。我想起了《圣经》上的一句话,“神说,有光,便有了光。”
我给阿姨说她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还要带梅去澳洲看鸵鸟呢,到时候那里也有个亲戚。
第三部分北京,这个冬天风不大(第22节)
22
老段第二天就匆匆离开了,他的突然到访让所有的人都感动。毕业后这几年见惯了太多的人情冷漠,老段的笑脸让人感觉很温暖。
下午的阳光很灿烂,是个很适合去晒晒太阳的懒散天气。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梅的轮椅抬到楼下,我真的如当年预言的那样,推着她在楼底下的小花园散步。生活竟是如此的残酷而充满戏剧色彩,我禁不住暗自叹息。
花园里几个老头老太太显然认识梅,不时有人过来问候一下,而梅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们介绍我是她大学里最好的朋友,那些老头老太太们的眼神意味深长。梅显然没有意识到什么,她沉浸在和我久别重逢的喜悦中,谈兴正浓。
我和她聊到老段的时候,才知道老段更多的情况。梅说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老段在南方搞房地产,一度身价上10个亿。就在他志得意满,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不料他最心爱的儿子因为车祸而失去生命,老段伤心不已,突然间顿悟再多的钱也无法换回他儿子的生命,于是成立了一家民间慈善机构,夫妻俩从此致力于扶危济困,做了无数好人好事,2000年被其所在城市评选为该城的十大杰出青年之首,但老段放弃了这个荣誉,说不图这个。
老段的故事听得我啧啧称奇。非常之人,当有非常之事吧,我这样想。跟老段的高风亮节比起来,一下感觉自己真是庸俗得很,这么多年了只想着给自己捞点好处,几乎没向雷峰同志学习过,充其量也就不乱丢垃圾,损害花花草草草而已。偶尔心情好给别人指指路什么的,还不一定说得对,心情不好就直接说不知道。
再想想,想想生活潮涨潮落,总会有一些感动让我们泪流满面……哦,当初没钱的时候坐公交还给老人让过座,给一个患白血病的小孩捐过一百块钱,给流浪歌手的破帽子里放过10块钱……还有吗?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到底做过什么好人好事了,暗自惭愧不已,脸有点红,还好梅看不见。
十月的天气慵懒而舒适,适合幻想。我推着梅,一边随意地聊着天。
梅说她想起了墨尔本的学校,那些表面愚笨但却极为实用和纯朴的建筑。每到城市黄昏的时候,梅总喜欢沿着雅拉河边的露天咖啡屋走向码头,耳边是从河边奏过来的萨克斯音乐。那时候阳光投射在水面,建筑物的倒映在光线中纷乱而且招摇。梅说,那是她每天最放松的时候。
教堂里的钟声会在某个时刻响起,敲碎梅所有的孤单,然后梅会惊醒,开始在那个城市一站与一站之间流浪。时空变幻,一些人物模糊了,一些风景消逝了,还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陪着梅第二天的旅程。
比如老墨,梅曾经的男朋友,总是喜欢开着一辆半旧的本田,载着梅停到雅拉河边。树叶在风中发出哗哗声,远处教堂的钟声悠远而沉静,甚至有独木舟在河面上野渡无人。梅在那个时候会想起黄河,梅说,她无论走多远,心里面总有一条河在流淌……听着梅梦幻般的呓语。我默默无语,不经意间低头,发现梅已经是泪流满面。
梅还是无可避免地想起了老墨。停下来吧,故事结束了,我无声地说。我看到梅的绝望开始在心灵深处蔓延,渐渐汹涌。
“王愚,你说,是不是我一辈子就要坐在轮椅上了?”
我抬起头,有一群鸟旁若无人地在小区的草地上觅食,几个小孩正讨论着一个属于他们的问题,天空没有云朵,阳光照在身上说不出的暖和,我看到多年前梅穿一条绿色的裙子,一身青春气息,笑容灿烂地向我走来,越走越近……
今天是杜若的生日,想到她可能会一个人孤零零地度过她24岁的生日,我有点难过,甚至希望有她的同事或者朋友去陪她。可是在我认识她的两年时间里,她那里很少去过她的其他朋友,她一直说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小窝,只属于我们两个人,倒是我经常带四郎等狐朋狗友到那里啸聚,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的,害的杜若每次收拾的时候都痛苦不堪,我嬉笑着哄哄她下次依然照旧。我想来想去,在我所认识的她的朋友中,想不出来谁能给杜若过一个快乐的生日,忍不住给她发了条短消息说生日快乐,半天了她一直没回。
梅问我给谁发短消息呢,我说给一个朋友,今天她生日。她说是女朋友吧,我说不是啊,“我还是一条好汉呢”。撒完谎,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我不能告诉梅我有女朋友的事,让她多一点幻想,也许就多一点信心吧。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
梅哭了个天翻地覆,在我手足无措,几乎要打电话请阿姨帮忙时,她自己终于止住了。雨过天晴,我轻轻地替她擦去眼泪,心疼而又可怜她。我感觉得到梅内心深处的悲凉,梅说她在别人面前都强装笑颜,怕已经为她操碎了心的父母难过,可是她的心里的痛苦积压得太久了,叫我不要笑话她。
我说怎么会呢,你想哭就哭吧,我再去买点面纸,梅破涕为笑。继续推着她转了大半天后,该回去了,梅说要是我能这样天天推着她该多好。我心说,走着不是更好。
小区门口有个报厅,我去买了份晚报,这是从毕业以来新养成的习惯,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要看看那个城市的晚报,了解一下那里在某一天发生了哪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从不看晚报的老谋说我开始“走向庸俗”,我骂他知道个屁,那叫“关心生活”。
推着梅回去的时候,她发现新大陆地说报纸上登某小城有个小孩某某家里没钱上学,父母年迈,一年家里收入才上百块钱,报纸上呼吁社会救助呢。梅很同情地说:“好可怜啊。”我心里想你比她可怜一百倍,边说报纸上这种事太多了,劝她不必当真。
忽然猛一下想起来了,薇子毕业后就去了那个小城,心里一下有种说不出的忧伤。
我终于还是没有收到杜若的短信,这几天让我心里一直很失落。我不知道当杜若收到我的蛋糕和鲜花的时候,会不会像以往那样幸福的一塌糊涂,又或者一个人很寂寞地度过对她来说很重要的本命年的生日?我忽然有点后悔了,那天无论如何也该给她打个电话的。短信就跟网络一样不可全信,有时候未必能百分之一百的保证将所有的信息都传达给对方。如果她真没收到我的短信,那我真的无法原谅自己了。可是,如果她收到了却不回呢,这又意味着什么?
在远离北京的这几天,我开始觉得自己无法割舍对杜若的感情,无论下多大的决心。
传说中有两条鱼,生活在大海里,某一日它们被风浪冲到一个水沟里,为了生存下去它们相互把自己嘴里的泡沫喂到对方嘴里。这个出自《庄子》故事,便是那个成语“相濡以沐”的来历。从上大学开始,我就信奉自己所追寻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爱情。天可以裂,海可以枯,而我和我的爱人将用自己吐出的泡沫,去滋润和延续彼此的生命。
而现实情况是,有一天潮水上涌,那两条鱼再次被浪花卷进大海,它们摇摇头,摆摆尾,从此相忘于江湖。潮水过后,连它们生活过的那条水沟也荡然无存,那两条鱼已经忘了曾经互相吐着泡泡滋润对方的生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薇子离开我后,我痛不欲生,一度以为自己此生不会再爱上其他人。杜若的出现我一直将其当作一个男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艳遇,“人不风流枉少年”,要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