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画师-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画布和从视觉移植到画布是不一样的,你懂吗?以模仿或阐释生活来复制生活的面貌是一回事:享乐、美、恐怖、痛苦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那只不过是眼光独到、技巧和才能的问题。然而,遵从视网膜的命运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是用冷漠的线条来描绘出恐怖啊。”她仍然站在窗边,光溜溜的身子裹在法格斯的衬衫下,看着笼罩城市的蘑菇云,时而稍微举起照相机像是要拍照,却又马上放下相机。“你该画的是一个行凶的景象,让人领悟出画里刽子手的诞生并不该被视为好事。但是我们等着瞧,看哪个家伙看得到那个行凶景象,并把它画下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战争画师 第十五章(2)
法格斯喝了一口女服务生刚端来的啤酒,借酒浇灭了回忆。然后他朝东方看去,那边的海堤遮蔽了大海。一阵遥远的引擎声从防波堤的另一边慢慢靠近,随即看到一根红白相间的烟囱沿着防波堤往海港入口的信号灯处移动。一会儿后,观光游艇穿越海湾人口,开往露天咖啡座附近的码头靠岸。一个船员快速又精确地操作后,随即跳上地面把绳索固定在系船柱上,并架好舷梯,大约有二十来个游客陆续下船。战争画师好奇地注意观察,在观光客散去的同时,他试着辨认出通过扩音器说话的女人。最后只剩下少数几个人,其中有个年轻的女人特别显眼,金发、高挑、健美、和颜悦色,正往游客询问中心的办公室方向走去。她身穿一件让黝黑肤色显得更亮眼的白色亚麻套装,脚踩一双皮质凉鞋,背着一个斜背大包包,看起来有点疲惫。法格斯看见她打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他则继续坐在那儿,看着观光客沿着码头走远,他们正以海港和出海口后方的那片开阔的大海为背景,在渔夫的渔网以及船只旁,拍下离开前的几张照片或录下几个镜头。
观光客。民众。回忆又再次涌进脑海。“剩下的我们来搞定!”奥薇朵提过的柯达胶片广告是这么说的。那个联想让法格斯莞尔不禁,有好一阵子他不断地尝试以摄影达成目标。如果摄影是最终的意图,应该会是个混合或令人不满的公式;不过那是针对他脑海里渐渐成形的计划所做的一种预备,一种事前热身动作和训练方法,一种让眼力更加敏锐的方式,使他以不同的观点去看待摄影和绘画。自从波罗沃拿歇尔捷公路壕沟事件将法格斯的生命推往另一个方向,他通过连续两年在波斯尼亚、卢安达和狮子山等地的紧凑工作,将那个事件的副作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随后便放下战地摄影记者工作。经过一段长时间累积的过程之后,这个决定终于初具雏形:波特曼港的撕裂土地,科威特上空的浓黑云层,远处燃烧的杜布罗夫尼克和奥薇朵染上红光的躯体,接着在萨拉热窝假日饭店没有玻璃的房间里,好几个寒冷寂寥的夜晚,面对着爆炸和烽火所映照出的城市几何图案全景,这一切都以它不可避免的众多汇集直线,引导着法格斯走向那个审判厅。那场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某个冬季早晨,在审判厅里有个名叫波里斯拉夫·赫拉克(Borislav Herak)的塞尔维亚人,他出生于波斯尼亚,也曾是波伊卡(Boica)种族净化分队的成员,之前还在肉铺里学过杀猪,他以冷酷的口吻详述自己除了大规模屠杀行动之外的三十二起个人谋杀事件,其中包括了学生或家庭主妇在内的十六个女性受害者。他从变成塞尔维亚军队慰安场所的汕吉(Sanjak)监狱旅馆里把她们拖出来先奸后杀,像他的战友们对待另外上百个女人那样。在法庭和记者面前,赫拉克以恰当的手势与表情讲述谋杀一个二十岁年轻女子的过程。“我命令她脱掉衣服,她却大吼大叫,当我再次殴打她,她才脱掉衣服。我先强暴她,再丢给我的伙伴们轮奸,然后我们用车子把她带到如奇山,我在她头上开了一枪,把她丢到灌木丛里。”法格斯在相机取景器里框取赫拉克的脸孔,那是个不起眼的平凡脸孔,一种在非战争期间会被当做可怜男人的脸孔。他慢慢地放下相机,没按下快门,因为他相信世上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可以表现或解释出那种东西,甚至连当时电视摄像机所录下的影像或声音也办不到。地质并没有道德可言,奥薇朵谈到别的事情时曾说过,尽管谈的或许是同一件事:绝无可能拍下宇宙慵懒的呵欠。就这样,法格斯以那种方式走到三十年战地摄影生涯的尽头。那三十年的惯性运作依旧维持了一段时间,把他带往其他的战争场景,但是那时他已经对镜头呈现的东西失去所剩无几的信心,失去昔日驱使他把指头放在快门和对焦与光圈旋环的希望。然而,奥薇朵从来无法得知她和那一切的关系有多密切。随后法格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跑遍美术馆,拍摄战争图画,照片中还包括了观画的民众;那是一系列奇怪的作品,他自己慢慢地发觉其中的意图。他取得博物馆的拍摄许可证,带着没有闪光灯和脚架的徕卡相机、35mm的镜头和适合以自然光和低速拍摄的彩色底片,执行详尽的研究与纪录工作,昔日的战地摄影师从包括欧洲和美洲在内的十九家博物馆的一长串清单里,挑选出六十二幅战争绘画,他在每一幅画前站上好几天,拍摄图画以及在画前驻足的人、零散或团体的参观者、学生和艺术讲解员,也拍下展览厅空荡无人的时刻,或是参观民众多到几乎看不到作品的时刻。他就这样进行了四年之久,从不断取舍照片,到收编二十三张照片作为最后一系列作品。从《马德里一八○八年五月二日》(El 2 de mayo de 1808 en Madrid)里男人持刀刺杀埃及雇佣兵时的疯狂眼神——那双眼睛在普拉多美术馆歌厅里万头攒动的人群之间几乎看不到——到布勒哲尔昏暗的《疯女梅格》(Mad Meg),照片里一边是手持长剑的抢匪;另一边是安特卫普市梅耶博物馆几乎没有人的展览厅里一个正在观画的学生。他最后一本问世的摄影集《临死者》,则是这一切工作成果之大成,呈现出从人类到恐怖这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那本摄影集里的世界,唯一合乎逻辑的笑容,是古代大师们在画布和画板上刻画的骷髅头的笑容。而当二十三张照片都准备好了,他清楚自己也准备好了。那时,他永远放下照相机,补习年轻时没学到的绘画技巧,并开始找寻合适的作画地点。
战争画师 第十五章(3)
观光游艇上的女人走出办公室,朝露天咖啡座走来,正要前往停车场。法格斯注意到她停下来和港口的警卫说话,也向服务生打招呼。她的笑容甜美,看起来很健谈,金色的长发挽成一条马尾,虽然稍显丰腴,还是颇具魅力。当她从战争画师的桌前经过时,他注视着她的眼睛。蓝色眼睛,带着笑意。
“早。”他说。
女人凝视着他,一开始是诧异,然后是好奇。她大约三十岁吧,法格斯估算着。她回了句早,要继续往前走,却又犹疑地停了下来。
“我们认识吗?”她问。
“我认得您。”法格斯已经站起来,“至少我认得您的声音。每天十二点整都会听到您的声音。”
她专注地看着他,被搞糊涂了。她几乎和他一样高。法格斯指了指游艇和酋长海湾方向的海岸。几秒过后,她微笑的嘴角拉长了。
“当然啰!”她说,“您就是塔楼里的画师。”
“‘一位知名画家,他以一幅大壁画装饰塔楼内部墙面……’我想跟您说声感谢,尤其是‘知名’和‘装饰’这两个词。总之,您的声音非常好听。”
女人笑了出来。法格斯察觉到从她身上沁出的轻微汗味,一种属于大海和阳光的汗水。他想,流汗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毕竟她从早上十点就得开始忙着招呼游客。
“希望没有造成您的困扰。”她说,“如果有的话,真的是很抱歉……不过,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当地的名人好拿来跟游客炫耀……
“别担心。那条路很长,又是上坡路,很不好走,几乎不会有人上山到那儿去。”
法格斯邀请她一起入座。她坐了下来,向服务生点了一杯可口可乐,随后点燃一根香烟,开始向法格斯谈起工作上的一些细节。她来自半岛内地的某个城市,在旅游旺季时负责处理背阴港的办公室业务,冬季则接一些领事馆、大使馆、法院和移民局的翻译工作。名叫卡门·耶尔斯肯,离过婚,有个五岁的女儿。
“您是德国裔吗?”
“荷兰裔。但我从小就住在西班牙。”
他们聊了十五或二十分钟。那是一段没什么主题的礼貌性谈话,除了长久以来他每天早上听到的声音是属于那个女人的这个事实以外,其他的对法格斯都没太大意义。因此,他让她侃侃而谈,自己则保持相对的沉默,只穿插问了一些得体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还是无法避免那段谈话最后落在他和塔楼内的作品上。卡门·耶尔斯肯解释:“镇里的人都在说那是件原创作品,一幅您画了将近一年并且覆盖整个内部墙壁的巨大壁画。相当有意思,很可惜那幅画不开放参观,不过我了解您希望大家能让您安静工作。”她再次好奇地观察他,“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哪天可以亲眼看到那幅画。”
法格斯犹豫了两秒钟。对自己说,这有什么不妥呢?对方那么和蔼可亲,她的同胞林布兰[6]会毫不犹豫地把她画成一位肤质温润、胸前适度裸露的资产阶级妇女。绑马尾辫让她额头和太阳穴旁的头发显得紧绷、平坦,和肤色形成优美的对比。战争画师几乎忘了身旁有女人是什么感觉。马克维奇的影像快速地闪过他的脑子里。“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个克罗地亚人曾这么说。“您该下山到镇上去了。”那是马克维奇给他的一段反省时间,一种两人最后对话前的休战期。战争画师凝视着自己面前那双蓝色眼睛。习惯观察的他,在那双眼睛里感受到一丝兴致勃勃的光芒。他将右手放在桌上,并确认她的视线也随着他的手部动作而移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战争画师 第十五章(4)
“从明天起我有事情要忙,但是今天下午或许有可能……如果您愿意上山到我那儿,就可以看到塔楼壁画。不过车子只到得了半路,剩余的路途必须靠步行。”
卡门·耶尔斯肯迟疑了四秒钟才回话。“好的,我很乐意上山。五点过后方便吗?游客中心那个时间关门。”
“五点是个理想的时间。”法格斯回答。
女人站起来,他也跟着站起来,握了她伸过来的手。一个热切又率直的握手力度。他注意到那双蓝色眼睛里持续闪耀着兴致高昂的光芒。
“好,五点。”她复述道。
她渐渐走远的同时,法格斯仔细地观察她,金发,白色套装在丰臀和晒得黝黑的腿上摆动着。然后他又坐下来点了一杯啤酒,猜疑地打量着周围,唯恐看到马克维奇正躲在附近笑得合不拢嘴。
他继续望着大海以及邪恶角附近的海岸线,同时,卡门·耶尔斯肯也在他的思绪里缓慢地消失。太阳开始偏斜,强烈的光线赋予物体一种别具美感的精确亮度,有如透明颜料,不是让色彩变浓,而是把色调淡化得格外清透。他陷入回忆里,一边自言自语,美,是可用来描绘景观的诸多词汇之一;但也只是其中之一。过去,他也曾两度在奥薇朵身旁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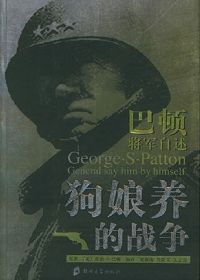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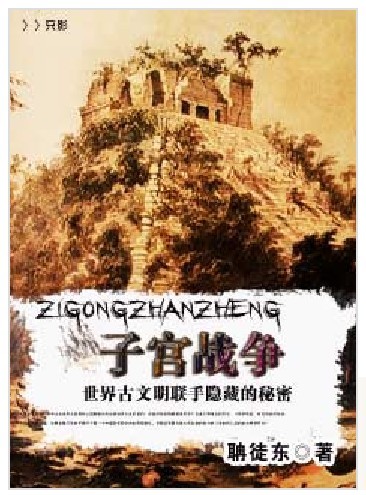


![(综漫同人)[夏目友人帐+兄弟战争]三日暖洋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3/31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