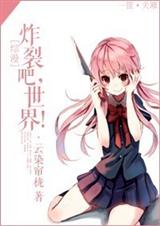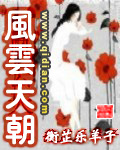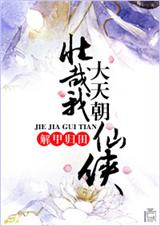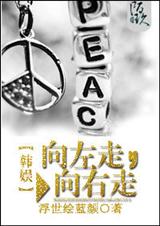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缴绲母础N屡傻慕艹龃硖匪猛罄匆餐ι矶觯造饷黄剑⑾蛩戮矗破洹熬庋笪瘛保翱晌瞎庖印薄 �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3)
那么郭嵩焘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正如海外著名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所说,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他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甚至延伸到五四。他是晚清衰世一骑绝尘的先知智者,正因为他的很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当时的人们不但跟不上他的步伐,甚至望不到他的身影。于是他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自始至终他都成为时人攻击的靶标,成为难容于世的异类。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是悲剧,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悲哀。
§“最了解西学的人”
郭嵩焘是在屈辱谩骂中开始他的外交生涯的。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窜至腾冲地区时,因受当地群众阻挠开枪打死多名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大怒,屡以下旗绝交、增派军舰来华进行威胁恫吓,乘机大肆要挟清政府,企图把此事件说成是清廷幕后指使,进行肆无忌惮的讹诈。
早已对*的官场心灰意冷的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慌乱之中不但答应英国“抚恤”、“赔款”、“惩凶”等苛刻要求,甚至不得不放下“天朝尊严”,按英方要求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挑来选去,清廷认为非郭嵩焘无人能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精通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感性的了解。后来一直倾心西学,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家事务,特别是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为洋务运动大声鼓呼,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士论大哗。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中华文明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无权与中国平起平坐,必须定期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屈尊派使“驻外”之说。所以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外派使节,即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的形象从此崩溃。面对清廷此举,大清子民们捶胸顿足,无不认为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担忧,感到此行凶多吉少,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悲哀惋惜,认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一时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幅著名的对联骂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当时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守旧氛围极浓,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郭氏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湘省乡试学子甚至聚集闹事,扬言要砸郭宅,让郭嵩焘全家受惊不小。 。 想看书来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4)
外有英人的催逼威胁,内有国人的毁谤痛诋,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身心俱疲,意绪全无,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朝廷批准。郭嵩焘毕竟是一位公忠体国的开明官员,在李鸿章等少数人的鼓励支持下,他逐渐转变了思想,自陈心迹“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认为“出师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毅然克服万千困难,踏上与英交涉使命的征途,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作“赔罪之旅”——而面对群议汹汹,为了表示“平衡”之意,清廷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
刚刚上任,他就惹出了不小的麻烦。
临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郭嵩焘非常赞同此举,他早就想将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同胞们尽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受命后他热情大增,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从出国时起,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中,他不仅用心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到了伦敦之后,他就把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他哪里料到,这份日记在总署刊行之后,犹如一颗炸弹投在死水潭里,立马在京师士大夫中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哗然,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痛斥他极意夸饰,美化外国,“用夷变夏”,声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连出版此书者的动机也加以怀疑:“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不仅思想守旧的士大夫如此,连一向开明的文坛领袖王辏г艘踩滩蛔√隼矗舐罟造獠豢删纫邓按阎醒蠖荆蘅刹烧摺薄8幸恍┤酥苯踊骋晒造狻坝卸挠谟⒐泄际轮倍浪峋鲆蟪⒔造獬分暗骰兀裨蛞哦竞M猓雎胰诵模蠊豢吧柘搿9造馍钕莨铝⑽拊场S捎谝皇闭也坏胶鲜嗜搜。逋⑽茨芙倩兀铝罱妒刮骷统獭坊侔妫淞鞔�
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郭嵩焘,这位被李鸿章屡屡称作“有些呆气”的人物,怀着一颗无人能解的赤子之心,不畏讥谗,我行我素,高歌前行,踏上一个人的独醒之路、漫漫长征。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他率先以其独特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他逐步发现,英国的强大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其政体——即它的根本制度——同样勃勃有生机。初至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政府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经常访问炮厂、船厂,并亲自升炮以及试演鱼雷大炮,体会到西洋军队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一系列的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中深思熟虑地写道:“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他从根本上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5)
郭嵩焘再次表现出他的异端思想与不合时宜。他的言行不但与“天朝上国”的规矩尺度大相径庭,而且与他先前的洋务派战友们也分道扬镳。他勇敢突破体制的樊篱,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更跨越到思想意识层面上,成为风格独特的思想先行者。他深感国内的洋务派领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如瞎子摸象,盲人把烛,各得一偏,与实际相去甚远。比如洋务派领袖们忙于造船制器,他却主张正本清源;朝野清流一致主战,他却认为在敌国环集的危局面前,“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只可随机应付,切忌不顾后果的浪战;洋务派领袖们认为当务之急先要强国,他却认为先要富民;朝野清流一致认为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却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制国之本,意在求利,我们不妨因势利导。他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看法与各路“神仙”如此格格不入,大相抵牾,得不到朝野各派系的鼎力相助,以至于孤立无援,便毫不奇怪了。
郭嵩焘犹如一个洞幽烛微,平心静气的医生,不避风险地为病入膏肓的老大中国诊治病因,对症下药。他虽然对西方文化还不能用辨证批判的眼光去全面加以审视,但他能够突破传统夷夏观念,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高于专制主义的优越性,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主张向西方学习,以平等互利的态度去处理对外关系,并力图以理性的方式去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近代外交意识的萌芽,也不愧为先知先觉者的独到之见。难怪乎学贯中西的一代巨人梁启超也心悦诚服地称赞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
§他成了大清朝的“敌人”
美国西部牛仔们有一句用以时刻自警的名言:“枪声总有余响。”
郭嵩焘显然不如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功勋卓异,声名远播。时代的主流难以容他,他也不肯随俗沉浮。作为洋务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的悲剧在于没有像上面三位那样在既定的秩序规则内周旋打拼。郭嵩焘走得太远了,他向清政府大力推荐的那些西方政治理念和先进管理措施,在闭塞狭隘的天朝官僚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闻所未闻。他三番五次挑战天朝秩序的行为,极大地震动了朝野人士的心理底线;而他对落伍的现有秩序的鄙视,也很快招来保守派人士的仇视谩骂。在官场的倾轧和污蔑中,他一生充满长夜独行的苦闷与激愤,尝尽不为人知的屈辱和悲凉。
正当京城上下对他舆情汹汹、十分不利的时刻,他的副手刘锡鸿抓住时机反戈相击,推波助澜,罗织罪状,欲一举置郭嵩焘于死地。刘在出使英国前就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一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