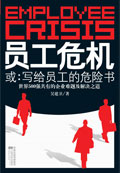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将它放弃。(作出这一决定有什么内在的机制,女人在其中参与到什么程度,通常的材料中都语焉不详。)在20世纪30年代,典押的做法至少是实行的,尤其在低等娼妓业中最为普遍,而有些材料说一半或一半多一点的妓女属于这一类情况。此类交易就像是典当衣服或家里其他值钱之物一样,在城里的穷人当中,这样的交易也很普遍。爱德华·亨德森这位公共租界的公共卫生署官员在1871年对典押交易作了最翔实的描述。他解释说,被典当的女子的父母或主人会以她一半的身价将她抵押给一家妓院。譬如说,她的身价是200元,他们就能借到100元。然后,他们将她每月所挣的钱(比方说,她每月能挣20元)与妓院院主对分(拿到10元),并用所得份额的一部分来还4%的抵押贷款利息(4元)。老鸨提供食宿;父母或主人则有权得到她获取的任何礼品。这样的安排对照料一个贫穷家庭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能给他们提供一大笔钱,接着还有虽不算多却相对稳定的进账,而且还省去他们一个人的饭钱。亨德森补充说,把女人抵押出去的人家(在他所提到的那个案例中,是女人的丈夫)很可能继而把她又卖给妓院,以获得更大一笔钱。 到了20世纪,典押过程更加化简;女人可作为借贷的担保物。借贷期间,她没有任何自由,对她的收入也没有控制权,她的收入由妓院的老鸨掌握。这种作为抵押品的妓女称作“包账”,以同那种从老鸨处得一个短期借贷的妓女(“带挡”)相区别,后者是以她所挣得的钱抵债。典押期限通常为二到三年,虽然有一法庭审讯的报道曾提到过一个八年期的典押案例。典押的钱数则从1920年时的40元一节度(约四个月)到1929年时的400元管好几年。1937—193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被典当的妓女比被卖掉的妓女价钱要高,这或许是因为妓院主无须对她负有没完没了的责任;他或她只要对她最能赚钱的三四年加以控制,而后即可将她打发。妓院老鸨如果想连本带利赚得更多一些,她或许会愿意一上来就多付一些。另一方面,典押女儿的人家往往也想多抵押一点,因而也会使劲抬价;而出卖女儿的人家往往都是到了万不得已的绝望境地,已经无法讨价还价。 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要求变革的呼声的高涨(参见第十和第十一章),甚至连指南手册上也开始用谴责性的语言来概括那些对妓院生活的细致描写,198尤其是在涉及被拐卖和典押的妓女问题时。在对卖淫业日益否定的大气候下,被典当的妓女也被看成是与被拐卖的一样的受害者。新闻报道总是说起妇女被其父母、兄长或丈夫典押到妓院,她们设法逃脱,后又被法院遣送到希望之门,使她们不再受她们家庭的控制。有时候,从事典押交易的家人也会被判刑入狱。 但是,被典押而从事性服务的妇女在许多重要方面仍与那些被变卖的姐妹们不同。由于这种交易本身还保留了与家人的接触,这些被典当的妇女仍可以在典当期满后回到她们的父母或丈夫身边(尽管有指南书的作者忧虑地指出,到这种时候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染上了性病,“她这一生也就完结了”)。有的父母了解到他们的女儿处境恶劣,也有让她们解除合同的。例如,1917年,有一个15岁的姑娘,她的父母把她典押到一家高等妓院中学唱功和表演技艺(显然是当雏妓);他们后来控告一老鸨,因为她让一嫖客使这个女孩破了身。这一类诉讼并不局限于高层妓女。1920年有这样一个案例,一16岁女子被她母亲典押到一家野鸡妓院,说好是只从事招待客人事宜,而老鸨则试图逼迫她与客人发生性关系,于是母亲想把她要回。(她因典当女儿而被判罚款50元,老鸨则因逼迫该女做妓女也被罚款50元。)但有报道说,这种因女儿失身而大怒的做法其实也可能是为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在1924年的一份小报报道中,一穷极潦倒的男子与他的情人将他们的女儿典当给一老鸨,得款500元。契约上写明,女孩到可以开苞年龄时,所获钱款将与其父母对分。该女失身后,老鸨却没有分钱,于是父母将女儿领回,让训练该女的老鸨在经济上大受损失。(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不是女孩的父母,反倒是老鸨跑到上海当地的协会里求助;结果是该女的父母将典押得款还给了老鸨。) 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家人讨回被典押女儿的故事成为妇女杂志上最常见的话题。有一篇报道讲到一个母亲不顾老鸨及其男帮手的威逼毒打,终于在法庭上讨回公道,由她为老鸨当佣人,让她的女儿到妓院外去打工,而不再当妓女。这个故事被当作母爱的典范,当作是对让这种合同得到延续的一种控诉,与那些有关拐卖的故事一样,它推崇的是家庭亲情最终战胜了那些欺诈盘剥的外来者。 对被典当的妓女而言,199她们知道自己是为父母或家人而当了妓女,是为了还债或为了付父母的丧葬费,因而她们把自己当妓女看成是尽一份孝心。有间接的证据说明,这些女人也参与了将自己典押出去的决定。例如1929年的一诉讼案中,一男子将其妻典押进他所工作的服装店旁的一家妓院,该男子的父亲告他卖妻,但他妻子和老鸨都出庭作证说她只是被典当而非被卖。那女人并无利用这一机会从老鸨处脱身的意思。而由于她丈夫的确就在隔壁干活,因而她也不能算是与家庭断了联系。 妓女仍与家庭保持联系,这种情况不仅是低等妓女的一个特点——该层次中许多人是结了婚的,或要担负抚养其娘家人的责任;而且,在20世纪的前二十多年出版的关于高等妓女的详细报道中,这种情况也有所提及。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看到的,一些高等妓女事略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讲上等人家出身的女子如何因家道中落而沦落风尘,并将自己所受到的良好家教和待人接物的本领带到了妓馆中。落泊的高等妓女这一主题,对于日益消亡并对往昔充满怀念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日益增长且对上述士大夫阶层怀有这样那样好奇的大众读者,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然而,经常提到的有关这些女人的家庭背景,(在某些情况下)仍不断出现在她们生活中的父母,以及有些父母省吃俭用、带着做高等妓女的女儿回乡嫁给体面人家的决心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高等妓女与身处下层的那些随时卖身的妓女一样,并不因为她们从事了娼妓业就“与家庭断绝了关系”。
第七章 人口买卖(六)
政治秩序的社会性别化 新闻报道、妓女改造文字、警署档案以及福利组织文件中关于上海妓女的故事,往往都说她们与家庭(娘家或婆家)断绝了关系,说妓女及其家庭都想方设法要救她们出火坑,并设法重新建立联系。但妓女们实际上则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家庭关系之中,甚至一些极普通的家庭,也常常会把她们的女儿或妻子送进妓院,但同时又并不放弃对她们本人及她们的收入所拥有的权利。一些受骗者被拐卖的故事应该说只是多种情况中的一种,但它们被凸显出来、甚至被说成是最主要的情况,这就需要作一点解释。 需要说明的第一点或许是关于对妓女劳动的控制问题。家庭和妓院业主都通过控制妓女的劳动,200包括她们的性服务,而坐收物质上的好处。当妓女的家里人想重新要回这些女人的时候,拐卖的指控就会变得异常突出,因为承认是他们自己卖掉了妻女会对他们大为不利。相反,按照民国的法律,妇女如果坚持说自己是被卖进娼门的良家女子,她则有权获得法律的保护而脱离妓院。如若离开妓院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一种物质或精神状况的改善,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就一定会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受害者,这样才能与家人团聚。因此,尽管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拐卖在人口买卖案件中仅仅是少数,大多数涉及妇女买卖和典当的案件都是事者家庭所同意的,然而,被拐骗和变卖仍是妓女们在为争取自由而提起法律诉讼时的一个常见的故事。 20世纪40年代警方收到的公民投诉信件中,关于人口贩卖或绑票事件的指控非常突出。这些信件都特别提到居民区中存在着一种无照经营的妓院,1946年一案例中曾有这样一段评说:“……共有妓女十余人,该妓女均是从乡下骗来,有许多不愿做妓女拉客,均遭妓院主毒辣殴打,是日夜间听见啼哭之声。”有时,控告信指控某罪犯是绑票者:“其股中最可恶者名杨二,曾派伊胞妹至乡下,拐骗年少女孩三口至上海迫令卖淫。若不顺从即遭毒打。”战后,市政府曾致力于扫除无照卖淫,因而警方照章对这些投诉进行调查,但他们从来不对贩卖人口的指控予以关注。其实,真正令妓院附近住户恼怒的并不是买卖人口问题,而是妓院中的喧闹声和引起的街头争吵,而警方所关注的也多是无照卖淫,而不是人口买卖。只由于人口买卖属于非法,因而任何人若想给邻近的一家妓院定罪,即可指控人口贩卖,而这就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人口贩卖在上海娼妓业中是如何如何的普遍。 造成对人口贩卖问题加以强调、而对其他因素则比较忽视的,当然还不仅仅是法律体系方面的原因。改造妓女的话语也特别涉及到人口贩卖问题。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时,在公共租界区就娼妓业是加强管制(实行有照营业)还是径直取缔的问题曾发生争论。主张管制者认为娼妓业是一种“社会罪恶”,但它的出现又不可避免。他们或以人性使然或以中国的经济状况恶劣来支撑他们的论点,认为老百姓为了糊口而不得不把女儿送出去干活或把她们卖掉。传教士们的观点则相反,他们竭力主张取缔,其理由则是基于自我的自主选择。201他们争辩说,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允许违背妇女的意愿将她们贩卖,无论这种贩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后者的论点多少是基于妇女沦为妓女都是被迫的假设,对此传教士们振振有辞。一位居住在中国内地的人氏以“Honor”(名誉)为笔名在上海一家报纸上撰文论及长江流域的妇女贩卖问题,“这条河流为中国那些拉皮条的提供了一种便利,他们可以一船一船地把妇女运送进张着饥饿大口的沿河各个口岸。”在各个口岸,被拐骗来的女子在秘密拍卖点上被卖出。Honor认为,“各口岸妓院中的大多数妓女都属这类被绑架来的女子”,她们当妓女并不是因为自己选择或经济上的原因,而都是被迫的。一旦当了妓女,她们就无法回家了,“她现在已成了发泄兽欲的工具,成了可怕的灾病之源——这时谁还会再要她”,而只有在这时,经济方面的需要才成为问题。Honor接着又断言,当妓女并不是女人出于“秉性的选择”,而是因为男人创造了对这些女人的需要: 说这些女人中的大多数都已经铁石心肠,说怜悯她们根本没用,说她们即使能离开这样的生活,她们也不肯离开,那显然是无稽之谈。但一旦在里面待惯了,她们又毫无疑问不再会离开。那张将她们裹挟于其中的经济大网,更不用说她们后天所习得的心态和变态的心理,就好像是钢筋铁链似的。但是,她们并不是自觉自愿地这么做的。(黑体部分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