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才之路-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二舅扛着一把大钯头,说要挖土,我也跟去了。那块地好大好大的,这可能就是外公遗留下来的财产吧,二舅说要把它挖转来插红薯。
二舅把钯头提得比屋檐还高,用力一钯头挖下去,再把右手一抬,整块土就翻过来了,足有桌面那么大。我心想,二舅力大如牛,真有本事。
土地的四周围着不高的土围子,土围子的周边都长着密不透风的灌木丛和荆棘条。荆棘上挂着星星点点的野草莓,我一边采野草莓吃,一边捉蝴蝶玩。不到一个上午,那块地就挖完了。
有一天外婆做六十八岁生日,母亲送了厚重的寿礼。所有的女儿都来了,不知父亲在什么院子里打牌,大舅母要母亲去找他回来,一起陪外婆过生日。
母亲带我一起去找父亲,先到风石堰徐吾公家去打听父亲打牌的地方,徐吾公老婆说:“昨天夜里还在深湾院子”。
深湾离风石堰不足三里路,我们一会儿就到了,见父亲正在坐庄,桌子上堆了许多钱。
他的牌友招呼我们去阶基上坐坐,等一会儿就好了。阶基上坐着好几个老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母亲和我刚坐下,就看见一个日本人从下面田垅里的石板路上走来了。我有点怕,想躲到屋里去,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日本人。
一个老乡却向日本人发邀请:“太君,我的孩子高烧不退,麻烦你过来瞧瞧好吗?”
那日本人一听,加快了脚步,二、三分钟就上了台阶。他个子单高单高的,戴着副近视眼镜,一看就是个读书人。手里提着个军用药箱,面部带着一点笑,让人感到一点也不害怕的样子,我也不躲了,屋子里照样打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那个老大爷说:“太君,你的药大大的好,上次你给我老婆看病,她吃了你的药第二天就好了。今天是我孙子发高烧,尽说胡话,又要请你给他瞧瞧。”
日本太君提着药箱进到里屋去,拿出听诊器听听那个小孩的胸部,又测测他的体温,就对那个大爷说:“你的小孩,病重重的,危险的有。我的药大大的好,你的没有关系了------再晚一点,就会死了死了的!”
他给这个小孩打了两针,又拿了几片药,要他今、明两天吃。
说完就走了。
后来听父亲回来说,那小孩患的是肺炎,打了针当天下午就退烧了,第二天就下来玩了。
有一天,父亲要带我去读书,说毛坪来了一个教蒙馆的先生,还是个老秀才。书教得很好,每个月只收一斗米学费,还可以分两次交,说要我好好读书,将来好做大事。
父亲提着五升米和拿着一个送给老师的“红包”在前面走,我紧随其后。心里有点儿紧张,也有点儿新奇,只小一会儿就到了读书的地方。
父亲要我先向孔子的画像磕头,然后向老师磕头。我磕了头,抬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这个先生是驼子,他的右背脊梁骨凸得高高的,歪着脖子,头老向一边扭着看人。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灰布长衫,手里拿着一根古铜色的“士林棍”。他见我向他磕头很高兴,欢迎我到他这里来读书,要我听孔夫子的话,好好读书识字。我发现他说这两句话是很认真的。
他发给我只有几页纸的书,上面是他自己用毛笔写的字,整整齐齐,很工整,很好看。
父亲离开后,他开始给我点第一课书,只点四句话: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他慢吞吞地,扯着长音读一句,我跟着读一句。一连教了三遍,就要我读一遍给他听。然后就安排我自己到一张大桌子边去自己读,说:“读熟了,就去找他背。”
我也扯着嗓子读了四、五遍,早就背得了,但我有点害怕,不敢到他身边去背。
正犹豫间,另一个学生抢先去背了,背得有点疙疙瘩瘩,但也通过了。
于是我胆子大了,拿着书也去背了,老师说我背得很好,用朱笔在后面划了个很大的“√”号。然后就教我拿笔写字,他教了几遍,就要我当着他的面写一“横”一“竖”……说我接受能力不错。然后就送给我他写好了十二个字的“贴”,要我到桌子边去模仿着写字,每个字都要写五遍,写好了就交给他打“圈圈”。
这天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下午又点了四句书,基本上是重复上午的程序。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练习写字,突然一声巨响,惊得地动山摇。我写字的毛笔惊得掉到了地上,学生吓得往桌子底下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随即外面传来喊声:“塘里的炸弹炸了,牛俫己炸飞了!”
我随大人们跑到离外婆家不远的大码头边,发现码头有半边炸塌了。好多人在炸塌的码头上,在水塘边,在禾坪里寻找着什么,说是寻找牛俫己的尸块。
码头上面站着三个日本军人,二个人端着长枪,好长好长的枪,眼睛注视着人群。另一个日本人挂着腰刀,还倒提着一枝短长枪,在那里唧哩哇啦地向一个老者发问。听那老者说:“牛俫己在下面那口大塘里洗澡,在水里摸到了这颗大炸弹,他用尽全身力气扛到了码头上。
“那个炸弹像个五、六岁的胖小孩,胀着个大肚子,头上有坨好大的配件,是铜做的。他挥舞着锄头敲打着炸弹头,想把它卸下来卖钱。“那个日本人可能也懂一点中文,我见他专心地听着,间或还点一下头或者‘嗯’一声,老者叫他“太君”。
“我劝他别敲了,敲炸了不得了。他不听,说这炸弹是哑弹,锈了,里面的炸药让水浸湿了,炸不响了。
“我见他不听,就走了。我朝下面的禾坪里走,走了不到100米,轰的一声就炸了,我回头一看,牛俫己炸飞了,不见了。就像弹棉花似的,炸弹把他弹成了一小点一小点,像天女散花似的,方圆几百米到处散去了。
“牛俫己没有父母,只有一个哥哥。恰巧今天不在家,要不然,哥哥如果来帮忙,就两兄弟都炸死了。”
说完,老者哭丧着脸,有点悲痛的样子。
好心的村民们都流着泪,在到处搜寻着他的碎尸,想把它一点一点捡起来,用坛子装着埋到土里去,“入土为安嘛”。
突然有个老婆婆在一条水沟旁边发现了一块大的尸骸,好像是人的大腿和臀部。老婆婆怎么搬,也搬不上来。那个日本太君很快过去了,他命令旁边那个看热闹的青年去搬。青年人战战兢兢地过去了,他一见到那块尸骸就颤抖得更厉害了。于是他趁那日本人没注意,一个猛子就往水沟外面跳。
水沟外面是一个陡坡,陡坡下面是个小院了。说时迟那时快,日本人反脸一看,抡起枪就打。子弹从他的头发尖上飞过去,他往小院子里一钻就不见了。日本人也不追赶,但嘴里却大声骂着:“叭格牙路!死了死了的!”
好多年后,我从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上得知,1945年德国投降,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中国的东北又有苏联红军压境,中国的老百姓也奋起抗日,到处围剿日本兵。日本鬼子为了保存实力,实行怀柔政策,以缓解与中国人民的矛盾。
第三天,我正要提着小书篮去上学,父亲对我说:“今天不去上学了,我们回赵坪铺去。我在赵坪铺买了房子,以后就在自己家乡读书好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五、 父亲去世
五、 父亲去世
我回到赵坪铺的第一件事,就去榨油坊寻找我藏在草堆中的木码子。
正如父亲说的那样,榨油坊真的被日本鬼子烧掉了,烧得惨不忍睹:稻草盖的屋顶没有了,碾槽的木支架烧掉了。榨床的木腿和那么多的木橛都化成了灰烬,做油饼用的铁圈圈一个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巨大的榨床烧脱了一层“皮”,“肌肉”也被烧成了焦黑的豆腐块,还焦头烂额地躺在地上。西面的墙壁倒了,地面上散落着好几堆日本人拉的大便,稀稀的,像用牛屎洗禾坪一样,有磨盘那么大,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有的烧焦了的桁条还在空中悬着,摇摇欲坠的样子还没有掉下来。还没有倒下去的砖墙,裂开了好几道大口子 ,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母亲怕出意外,赶快把我叫了回去。
父亲买的房屋就在榨油坊的前面,紧临百马大道,离圩厂塘的溢洪口子不到5米。全用土砖砌成,盖着青瓦,有左右两间,左边有一间15平方米的睡房,睡房的前面并排着有两间厕所,紧临百马大道。右边是间八米长,4米宽的厅屋兼厨房,父亲早已请人在厅屋的后半部打好了灶。厅屋的前半部是木板铺的楼,但被煤烟熏得黑黑的。
看到这两间土砖房,使我想起在逃难前谢铁匠在这里打铁的情景:谢铁匠家有三口人,老婆的脑袋像把大夜壶,眼睛、鼻子、嘴巴挤在一堆。有一只眼睛瞎了,老是斜着眼看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们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小名叫泼俫己,成天光着身子,七、八岁了还不会吃饭,在床上拉屎拉尿。有一次他妈妈把饭送到床上让他自己抓着吃,他却散得满床都是饭,跟他拉的屎混在一起,他就连屎带饭抓起来一起吃。谢铁匠高高瘦瘦的,很结实,抡铁锤的手臂胀鼓鼓的,很是有劲,一锤砸下去火花四溅,让人躲都来不及。母亲怕火星子溅瞎了我的眼睛,常常警告我不要去玩!
听父亲说,在逃难的途中,谢铁匠被日本鬼子抓了夫,后来死了,他的独生儿子也跑丢了,如今只剩下他老婆,我家花二万元纸币买的这房屋,就是她卖给我们的。现在只交了一万元,另一万元给她出了欠条,明年八月还。
赵坪铺逃难出去的人,回来的还没有一半,祖母一家就没有回来。每逢圩日,赶圩的人稀稀拉拉的,赌场也还没恢复,一点也不热闹。
有一天,父亲要去一个朋友家买粮食,我也跟着去了。
父亲买米回来不几天就病了,头痛、发热,躺在床上浑身无力,茶饭不思。母亲赶快从田野中采来了草药熬姜汤给父亲喝。但父亲的病不但不见好,反而还在加重:畏寒、发烧得更厉害了,大热天一床大棉被蒙头盖上还怕冷。
母亲急了,赶紧请医生诊治。那时候赵坪铺的四家药铺只有刘余堂一家开业,他看了看父亲的舌苔,把了一会儿脉,问了父亲一些感觉,就说父亲患的是伤寒病。给父亲开了处方,一连吃了七副中药,但一点也不见效。高烧持续不退,还说胡话,胸部和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玫瑰色皮疹,人已瘦得皮包骨头。
母亲急得逢人就打听哪里有好医生。
旧中国本来就缺医少药,加之时逢乱世,日本鬼子还没有走,好多的中医师都逃难在外,还没有归家,更别说名老中医了。
有一天母亲打听到离赵坪铺12里的观音塘有个叫龙方高的老中医,从医50多年了,方圆几十里很有名。
母亲一听,就马不停蹄地赶到观音塘。见了龙方高又是哭诉又是磕头,才终于把个六、七十岁的老中医师请动了。
回到赵坪铺,母亲的脚板满是血泡,可她一点也不觉得痛。老中医给父亲开了处方,对母亲说:“先吃五副,看能不能退下烧来。如果不能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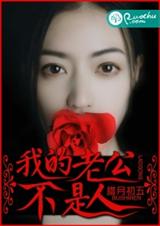
![[韩娱]我的外星女友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0/6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