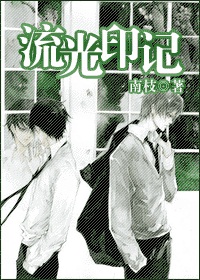流光亦彩-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结果,这么些年,我真就没看见过回头钱。张力实在不放心冉航的偿还能力,又把那五毛钱要了回去。
冉航对我说:“我代表毛主席鄙视他。”
放学后,我们路过游戏厅。冉航说进去看看,缓解一下心情,回家以后才能全身心地投入抄作业。
游戏听里人头攒动烟味弥漫。有个大约有七八岁的娃娃正坐在游戏机前浴血奋战,圆圆的脑袋随身子左右摇摆,像个不倒翁。游戏机杆子摇得飞转,按钮拍得啪啪响,嘴里还在给游戏机里的人物配音:“啊,打你,操操操操……咔咔……杀呀……呼风唤雨……啊……呲……呼呼呼呼……砍他……”娃娃玩儿得大汗淋漓,壮烈了就再投币,奋勇向前。
冉航说,为什么币这么宝贵的东西总是被无知的人占有,不能唯才是用。我说,等你挣钱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冉航的手在空气中挥舞,说,我现在就十分迫切地想玩儿把超级97,你说,我跟那小孩儿要币,他能能给。冉航目光灼灼。我说,我小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现在咱们大了,在小孩儿身上我看到了我过去的影子。冉航说,我也是,不过我不是抢,是要。
冉航把语言付诸了行动,可惜未成功,娃娃表现的不亢不卑,只给了他两个字:不给。冉航没有气馁,坐在了娃娃身边,为其指点迷津,告诉娃娃怎么过关,希望以此拉近距离让娃娃明白,他是善良的。娃娃很警惕,犹如旧社会的土豪劣绅守着自己的金山银山一般,配上冉航在一旁无产阶级形象颇有意境。当屏幕上终于出现“GEME OVER”之后,娃娃拿着剩下的币子去押苹果机,冉航尾随其后。
我扒拉冉航一下说,回家啊,没啥意思也。冉航说,我现在要有一个币就押橘子和西瓜。冉航建议娃娃听取他的意见,毕竟自己有着丰富的赌坛经验。娃娃没有听取冉航的意见,要证明自己是有主见的。当灯光在西瓜图案上闪烁的时候,冉航说,看,听我的是不是就中了。一次言中,冉航再一次指点。娃娃似乎是要让冉航明白,刚才只不过是巧合,瞎猫碰了回死耗子,也就再一次对冉航的建议置若罔闻。结果瞎猫再一次撞了死耗子。
娃娃若有所思,冉航痛心疾首。
回家路上。我问冉航,是不是心有不甘。冉航说,我肝肠寸断了都,张力要不把那五毛钱要回去,咱俩一人一个币,剩一个是不是还能押一把,那么多币啊,够玩儿好几天了。张力那*,别指望我能还他钱了,气死我了都。
冉航对张力的恨表现得毅然决然,天空中最后一抹曛黄见证了这一切,人类的报复心就是这么直接,我忽然觉得冷风彻骨斜日黯然。
第二天一到学校,冉航拿个五毛钱硬币还给了张力,这让我觉得匪夷所思。我问冉航,你是信佛了还是读了论语,中庸,中学生行为规范?他说,五毛钱太便宜张力了,我这是有计划的。
两星期内冉航先后在张力手中借过三次钱,都是当天借隔日马上奉还。他对张力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如此反复,冉航确实在张力脑海中建立起了好借好还的形象。长期的假象,张力对于冉航借钱的态度由大惊失色到欣然借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在冉航身上应验了。一切的准备,铺垫,循循善诱,都是为了在一个平凡的午后从张力手中借得人民币六元整。冉航用这笔不义之财买了两袋小当家方便面,隔日在学校附近的游戏厅过了一下午挥币如土的日子。压抑了半个月的惆怅,愤怒,终于在这一刻得以平息。
几日后,张力对冉航借钱的事几经暗示旁敲侧击,而冉航对此只字不提。直到张力实在憋不住了,对冉航说,那六块钱你啥时候还我啊?冉航说,这几天手头紧,等我有钱的。
两日后,张力问冉航,有钱没啊,赶紧还我啊。冉航说,我妈对我实行经济*,你再坚持坚持,有钱能不还你么。
坚持了多日之后,冉航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张力心有不甘:“还钱。”
冉航:“没钱。”
张力:“……”
一阵短暂的沉默。
张力以央求的口吻说,哥,你还我得了。
“真没钱”冉航无动于衷。
“好借好还那都谁说的,以后还指不指望再跟我借钱了”张力说。
“我现在是真没钱,那啥还你啊”冉航双手一摊情真意切。
天空中漂浮着几朵白云,并未蔽日。阳光无碍地照在张力脸上,微微有些灼热,泛起淡淡的红。操场上几个学生拿着笤帚、墩布在互相追逐打闹,无视组织纪律。地上瓜果皮屑一片狼藉。
冉航凭借他的脸取得了胜利,那六块钱一直欠到毕业,未果。
张力由此幡然醒悟,觉得这世界充满了黑暗与陷阱。
大亮在胡同里抽烟。我站在一旁。
灰暗的夜色中,大亮的脸随每一次深吸吐气忽隐忽现,烟头如萤火虫屁股一样闪着幽光。恶毒的白昼所产生的热气已经消失殆尽,虽依然没有一丝风,但总算可以把背心儿穿在身上和猿人区分开,大难过后的人们还是比较文明的。
几番吞云吐雾,大亮圆圆的脑袋四周烟雾缭绕。
我说,成仙了。
几日后大亮去了长春一所技工学校就读,我们不得谋面。
七
德惠的公交车大概有六米长,每当学生放学的时候总能慢慢地塞上几车。车里的人都是前胸贴别人的后背,摩肩接踵难以动弹。夹在中间的人根本不需要抓扶手,不用担心停车时的惯性把自己悠倒,一车人相对固定住了。如果是坐在最后一排,需要提前一站向门口移动,左突右击奋勇向前,没力气的就提前两站往车门冲。路边等公交车的人经常在往车里瞅一眼之后就失去了上车的勇气,继续等待下一辆。
有一首歌叫香水有毒,我领教了。有一次就在公交车上,人很多,我旁边站了一位少妇,浓烈的香水味熏了我十多分钟,直到让我有些微微头疼,我受不了了,提前下车走路回家。路边一个食杂店把我逗乐了,名叫“*”食杂店。无知真可怕。
比无知更可怕的就是迷信。我怕鬼,虽然我没亲眼见过鬼,但是对鬼已经有了定义——看不见莫不着。幻想中的鬼看得见摸得到我。这份恐惧始终埋藏在我心里。
哥哥喜欢看恐怖电影,尤其喜欢在晚上人们熟睡之后独自观赏。我有起夜的习惯,半夜起来放水,经常瞧见哥哥、电视机还有VCD在辛勤地值夜班。
某夜,哥哥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机。血泊中,一名被染得斑驳的白衣女子从地上缓缓爬起,把自己的头拧下来,扯着头发像抡铅球似地甩了出去。
我站在院子里,在极度恐慌中释放膀胱。风刮着窗子微微作响,此刻的我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十分敏感,歪过头,将惺忪的双眼瞪若铜铃,眨了眨,聚精会神地盯着窗户,怕有妖魔破窗而出把我捉了去下锅。我精神过度集中在对于未知事物的怵惕,不经意间考验了尿桶旁边的红砖地,水滴是否会石穿。听到水声有异样,我回过头调整枪口,加强压力,我听到了波涛在怒吼,完毕,一拽裤衩夺门而入。
我爬回温暖的被窝借着剩余的一丝倦意急欲睡去,可睡觉不像撒尿,越急越糟。我蜷缩在炕上,出了身冷汗,一闭眼就觉得有只手正朝我迎面抓来,我茫然了。
对鬼魂的恐惧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折磨着我幼小的心灵。夜晚,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直到实在熬不住困倦才能浑然睡去。我憔悴了。
这种情况不记得到底持续了多久才渐渐被我淡忘。
白日,折磨我的鬼魂消失了,但折磨我的人并没有消失,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哥哥当过兵,体壮如牛身手矫健,比我大七岁。我闲着没事儿总喜欢用语言打击他,他则用拳头击打我。我说,小样儿不用你美,等你老了走不动道儿的时候看我咋揍你。哥哥上来七扭八拗把我扣住,说,这叫乾坤霹雳麻花锁。我说,投降了投降了,投降输一半。哥哥真就让我输一半,打红了我半边屁股,在我百般告饶下罢手,奸笑着问我,爽不?我说,也就是你撒手了,要不一会儿进医院的肯定是你,不乐意揍你还不知道咋回事儿呢。我做了个鬼脸,撒腿便跑,没跑出几步又被哥哥捉住。我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学校的走廊里响起下课铃。于善龙拿本英语磁带放在凳子腿下,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磁带脆弱的塑料外壳不堪重负应声而碎,而后他把带子扯了出来在教室里四处乱窜,把屋子弄得好似盘丝洞。遭了几个女生的斥责。临近上课前于善龙又把带子全都收了回来,气喘吁吁地坐在位子上。
我坐在于善龙旁边,我瞅瞅他,乐了,说,我能想起个成语。
于善龙说,啥成语?
我说,自食其果。
于善龙说,靠。
“文曲星借我玩玩儿。”
“还不死心啊,这辈子你都超不了我。”
“重在精神,不就一千二么,让你看看两千是怎么摞出来的。”
“嘁,累尿血你,你要打到两千分我脑瓜子都给你。”于善龙从裤兜里掏出文曲星递到我手上。
俄罗斯方块对于我来说确实有难度,因此于善龙的脑袋也就一直挂在脖子上,稳如泰山。
一节课的时间,我满眼都是各种形状的平面图形,我充分地运用着不太合格的智慧,想方设法将各种形状的方块摞在一起,尽力做到严丝合缝,其专心程度达到了漠视老王的地步。这也要归功于一旁贼一般的于善龙,他可不想文曲星被没收。 。 想看书来
八
教室里有三组座位两条过道。一旦老王往我们这边来了,一只脚刚迈下讲台于善龙就扒拉扒拉我说,老师来了。
老王经常像是在吓唬我们,或许是她多年教师生涯养成的习惯,总在讲台和两条过道之间徘徊,十分可疑,却又很少深入群众,一般刚走到第三排就开始往回返,走走停停欲擒故纵。这苦了上课开小差的,防老王的心从未松懈。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还不明事理,容易被假象迷惑。从我开始在英语课做与其无关的事很多次以后得出个结论,老王从讲台走到我身边的几率几乎为零。如此,我便放松警惕。开始对十几米外渡来渡去的老王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曾经某次我上课时把目光全部投在膝盖上的《老夫子》,笑的花枝乱颤。老王从台上走了下来,步履轻盈,如鬼魅般出现在我身边。我还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被漫画上的故事逗得五官错位,我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只手,一直女人的手,一直四十多岁中年女人饱经沧桑的手——老王的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警戒时期做过千万遍的动作,把书往书桌堂里塞,可惜为时已晚,事已败露,挣扎已经是多余的。老王的手抓着我的漫画,我往回轻轻拽了拽,以万分恳求的眼神望着老王,说,老师,这书是我借的。
“谁让你上课看了。”
“我再也不上课看了。”
“晚了。”
老王手上加了两成力道,我放弃了抵抗,手松了开。
“老师,给我吧,我不上课看了还不行吗,我保证指定不





![[古剑奇谭] [越苏] 流光可待时追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