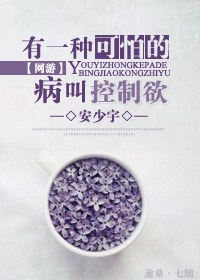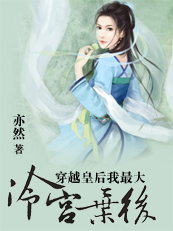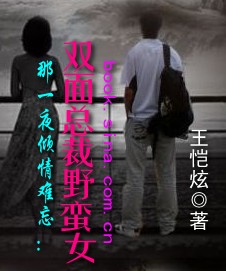我最难忘的病人-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轻轻地拍了一下婴儿的屁股,随着婴儿清脆的啼哭,我紧张的心开始放松。我用两把止血钳夹住脐带,结扎脐带后用棉被包住婴儿。这是一个女婴,生出来就胖嘟嘟的很可爱。等孕妇娩出胎盘,我和护士把孕妇抬上了担架。这时产妇的丈夫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天晚了没有找到领导,证明也没有开,空手而回。有好事者在旁向他诉说着接生的经过。看到母女平安,小伙子非常高兴。
我给妇产科病房打了联系电话安排母女住院。只要不在病房生就不违法,生了下来就可以住院了。
事后我并没有因为孕妇没有准生证帮助接生而受到批评,我已经很满足了。其实原则和实际工作有出入的时候,应该讲究灵活。如果治疗和决策会影响病人的生命,作为医生我会把生命看得更重。我愿意牺牲我的个人利益,去换取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你要问我为什么?因为生命无价!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非典,我们临危不惧
2007年4月1日黄昏,夜静悄悄地,天空下着沥沥小雨,我照例在家里吃着晚餐,7时左右,突然接到单位领导护理部任主任的电话:“市院的‘非典’病人病情危重,急需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我院需派两名ICU护士前往六院参与抢救工作,去护理‘非典’病人。”我很快整理了一些衣物,与EICU的何晓华在院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六院。
天一直下着雨,我们简短地听取了病史讨论后,匆匆放下行李,还没来得及打理,便踏入了“非典”病房。病房的气氛格外紧张,在“非典”病房护士长的指导下,我们急急地穿上一身防化服、三件隔离衣,再戴上四层帽子。口罩就更厚了,先是一个活性炭口罩,紧接着是48层纱布口罩(普通纱布口罩是12层的,我们相当于戴了四个),就这样一下子武装起来了。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厚厚的口罩,我们顿感全身出汗,额头渗出了汗珠,呼吸有些困难。但时间紧迫,我们也没顾得上这些,很快地再穿上鞋套、长统雨靴,外再穿鞋套,戴上眼罩和三副手套,走到“非典”病人身边。
一进病房,便可见其中两位“非典”病人呼吸窘迫非常明显,无创通气已不能维持患者的呼吸,SpO2进行性下降,插管迫在眉睫,我们还没顾得上望一眼病房周围的环境,便很快投入到抢救中。当时,病房里除了麻醉师、ICU主任、呼吸师以外,就是我们4位护士了,环境非常差,条件十分艰苦。飞沫传播是“非典”传播的主要途径,插管期间医护人员的感染率谁都清楚,危险性谁都明了。可是,我们必须尽快地为病人插管,也就没想这么多了。此时,全身的衣服已湿透了,汗水把眼罩也湿糊了。
插管开始了,气道一打开,我们又是与病人零距离接触,这过程最危险,我们最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地完成插管,尽量减少病毒播散。病人躁动,不配合,隔离服又使得任何操作都比平时困难好几倍。汗一直在流,可我们还是尽可能利索地配合着插管。虽然是第一次合作,我们双方甚至都没打过招呼,但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十分投入,插管成功了。
同样,另一个病人也很快置入了气管插管,开始机械通气。曾有报道说,有许多医护人员都是在插管过程中被感染的,但我们不畏惧,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会没事的。插管结束了,病人的呼吸困难缓解了,SpO2上升了,看到这些,欣慰感油然而生,但此时戴着厚厚口罩的我们,多说上几句话,就已是气喘吁吁了。“闷、渴、热”的痛苦一直折磨着我们,但我们必须战胜它。抢救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紧接着在医护人员的配合下,成功置入了桡动脉置管和深静脉置管。
戴着三四副橡胶手套的我们给病人打针、穿刺,完全凭感觉,因为我们的手已被汗水浸湿,麻木了。根据病情需要,我们又给病人置入了胃管、导尿管,这么多的有创操作,都在这短短的几小时之内,在这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完成了。这真的是我碰到过的最艰苦、最难忘的一次抢救。抽血化验、挂盐水、用药、吸痰,我们一直忙着,马不停蹄。病人安静下来了,呼吸平稳了,心血管监护相对稳定了,此时的我们感到脚上穿着的长统靴是那么沉重。夜是寂静的,我们猛然抬头一看,天已亮了,时钟已指向7点整,从4月24日晚10点进入病房,一直到次日凌晨7点离开病房,我们连续工作了9个小时,滴水未进。
离开病房,外面的空气真好,疲惫不堪的我们很费力地取下一层又一层的口罩,脱下一件又一件的衣服,感觉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相互望望对方,陡然发现:面色晦暗的我们每人脸上都有一道又一道的口罩印痕,工作时间太久,缺氧十分严重,口唇已有点苍白了,腕上也留有深深的手套痕迹,低血糖使得我们头晕眼花、四肢疲软乏力。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相互搀扶着来到昨晚刚放下行李,还没准备好床铺的房间,准备先饱餐一顿,再好好地休息一下。体力消耗真的是太大了,但我相信,明天,我们会依旧精神饱满地走向“非典”病房,走到“非典”病人身边。
“患者”给我上了一课
不少人说,医生的职业充满风险,此话不假。我当上医生不久,一位“患者”就给我上了一课。
这天,某大型企业安排上千名职工来我院体检。院内各科室忙得不可开交,到处都挤满焦急等待的体检者。我当班的放射科外,人群排成了长蛇阵,大家依次递上体检单,鱼贯进入透视室,按顺序脱去外衣,挨个走上X线机,轮番接受透视检查。
体检者中,有一位敦实的小伙子,看上去很精神。在脱去外套后,仅留一件背心,“噌”的一下便站到了透视机上。荧光屏上出现了跳动不止的心脏和忽明忽暗的肺脏。蓦地,一个极其醒目的图像映入我的眼帘:患者的左侧胸腔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椭圆形阴影。这是啥病呢?我的脑海里充满一串问号。难道是气胸吗?我想了想,又看了一下荧光屏,感觉阴影与教科书上描绘的气胸几乎一模一样。体检?气胸?我虽有些不解,但还是作出了气胸的诊断,并嘱咐他尽快到急诊室治疗。小伙子一脸的惶惑。
就在小伙子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我不由得一愣。这小伙子既不气急又不胸痛,身体壮如牛,完全不像一个气胸患者。我对自己的诊断产生怀疑了。可问题出在哪儿呢?
我留住了小伙子,让他再检查一下。重新开机后,在荧光屏上他的左胸仍然是一个大椭圆性阴影。不过这次我发现这个阴影不随呼吸移动,而且阴影外侧没有透亮的气体。我嘱咐他慢慢地转动身体。就在他旋转约半个身位时,一个令我目瞪口呆的图像出现了:他左胸那个阴影竟转到了背部的衣服上!我立即冲出控制室,让他把身上仅有的背心脱下来,只见上面有一个醒目的“10”字。因为字是用油漆喷上去的,不透X线,从而形成被压缩的肺组织的假象。由于他的背心是反穿在身上的,以致我起初没有发觉。脱去背心后再透视,左胸的“阴影”消失了。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假如他按照气胸治疗,后果真不堪设想。
这位小伙子胸部的阴影虽然消失了,但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它时刻告诫我:要谨慎!为医者,责任重于泰山。须知医者一次不起眼的失误,就可能造成误诊误治,可能让患者付出沉重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担架受阻记
在急救中心工作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天天的收获却是充实的!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夜班,凌晨4点半,急诊走廊一片寂静。每每在这时,内科病人已经廖廖无几,外科的病人也少了。几乎忙碌了一晚上的值班护士和医生,可以休息一下(值主班的护士通常要接诊分诊,因此护士站的椅子拼起来,就是“休息床”),整理一下疲惫的思路,甜甜地做一个梦,好振作精神随时应对下一场“战役”。我回想着刚才看过的一个个病人,这已经成为每天睡前的必修课。这时,电话铃“高叫”起来,在这宁静的夜晚里,听起来分外的刺耳。我急忙收回思绪,竖起耳朵……
“高大夫,出诊!”得,被子还没捂热呢,起来吧!
“住几楼?”下了车,我朝着家属问道。
这位来接应的是一瘦高个子的男孩子,回答说:“6楼。”
“病人现在情况怎样?”提着大约20公斤重的氧气和心电图箱上楼,我有点喘息地问。
“凌晨2点上完卫生间后,发现在打呼噜,然后就叫不醒了……”
到5楼时,我又接着问:“以前有什么病?”“高血压。”那男孩回答。
患者住的是老式楼房,楼道的公用部位被充分地“利用”,箱子、坛子、自行车把楼道挤得拥挤不堪。我心里顿时一阵郁闷,这楼道,担架怎么抬?
进了屋,见一位跟男孩子差不多身材的老人躺在床上,我走上去翻开眼皮,发现他双瞳孔等大,压眶刺激没反应,深度昏迷。“血压180/120mmHg,心电图,你看一下!”同来的茹说。在我查体时,茹已经熟练地完成了血压测量和心电图。
“估计是脑出血,甘露醇250ml静滴,留置导尿。”下完医嘱,我就去找家属交代病情,“患者目前很危险,回医院的路上随时可能出现呼吸心脏停止,随时可能有意外……”
那位男孩很木然地点点头。“抓紧时间准备担架,我们需要马上回医院进行进一步急救。”茹这时已经在指导家属铺担架了。我们总是很默契!
当我们把病人抬出门,先前的忧虑变成了现实:楼道被乱七八糟的东西拥塞着,下到楼梯拐弯处,我们只好把病人抬高上肩,以绕过那些障碍……茹每次都要尽量地把输液瓶举得高些,狭窄处还得从担架下面钻过去……每下一层,都要付出巨大的体力;每下一层,都要让他们把病人放下,观察血压和脉搏;每下一层,担架工都得歇口气,恢复一些体力;每下一层,都要花将近10分钟;每下一层,冒火的心就像被煎熬了一个世纪。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了,液体会不会滴完?针脱出来又如何是好?病人出现呕吐、抽搐,或者出现心脏骤停,在狭窄昏暗的楼道里如何抢救?每下一层,我们的心就在绝望和希望中挣扎!
到了2层,楼道灯坏了,就在这时,病人仿佛醒了,他不停地呻吟,似乎想翻身,我用几乎颤抖的声音安抚病人:“您别动,坚持一会儿!”我们在昏暗的手电光下又挨到1楼……终于出来了,6层楼整整挪了45分钟,所幸的是,到了车上,病人还能自己翻个身。
“直接回CT室。”我大声告诉司机。警笛在晨风中奏响胜利的乐章!
三天后,上白班,茹告诉我:“那个病人做了手术,现在醒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深深叹了口气!
时至今日,每当去朋友家,上下楼梯,都不由得要目测一下,看担架是否可以过得去……
按压下的奇迹(1)
1997年的那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早晨,我刚接班不久,同在急诊室工作的一个护士大姐过来找我说:她的儿子这几天感冒了,很重,今天坚持上班了,但同事们发现他的状态不好,派车来接她和医生过去看看。
那时的120系统还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