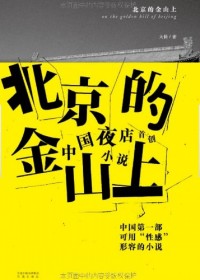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理黑道问题。弟弟和妹妹两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并尽可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对他们二人来说,压力绝对不算小,因为一年平均搬五次,其中一半是要换学校的。日本的公立小学、中学是严格按照行政区划来招生的。你到了不同的行政区域,就要上不同的学校。我上的是私立学校,就不受这一规定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来负责处理一切与黑道有关的问题,一方面是出于作为长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冲淡我对弟弟和妹妹抱有的愧疚感。当我跟他们俩通报小会的结果,妹妹勉强接受了,只是很担心我,而弟弟开始根本不接受,说他要和我一起来对付黑道。
我弟弟叫“喜芳(Kiyoshi)”,1985年11月1日出生。他在我们三兄妹中是公认的“另类”,不仅别人这么看,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个子矮,只有米,跟妹妹差不多高,他说话不多,性格内向,不善于和外界沟通,而喜欢一个人做事。但我知道,他是意志特别坚强的人,体育方面的表现,很多时候都比我优秀。他曾经从事过棒球和田径,都是国家级的水平。说实话,后来我放弃运动员生涯,转到学业上面,也跟弟弟的存在有关。兄弟分工嘛,我主攻学业,弟弟主攻体育,我就是这样给自己找“借口”的。至今,放弃运动员生涯是我人生中唯一的遗憾,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不会再选择放弃。
这里给大家讲一件关于弟弟的故事。我上初三、弟弟上初二那年的春天,在一个星期日,我们同时参加一场1500米的比赛,父亲在操场里观战。结果我取得第一名,弟弟第二名,他成绩也不错,4分10秒。但弟弟对成绩不满意,他心里最不能接受输给哥哥,比赛结束后,他一直坐在椅子上,脸上充满失落感。我和爸爸逼着他回家,运动场离家有20公里左右,我们骑脚踏车,爸爸骑摩托车。到了停车场,开锁之后,弟弟突然把自行车抬起来放在自己肩膀上,我问:“你怎么了?”弟弟回答说:“我就这样回家,惩罚一下自己,这样以后绝对不输给你了。”
爸爸大笑,他很喜欢弟弟这样倔强的性格,就没有阻止他,我很不放心,时间已经傍晚5点多了,他要多久才能回到家呢?但同时也知道,我是劝不动弟弟的,于是干脆放弃劝说,跟爸爸先回去了。
弟弟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才回到家的,记得那天正好报纸停刊。见到他的时候,我和爸爸很自然地跟他说:“怎么样,累了吧?”弟弟却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这么一点路,谁累啊……”吃完早饭,他跟平时一样对母亲说:“我吃完了,谢谢妈妈,我去上学了。”
这就是我的弟弟。
相比之下,我的毅力绝对不如他。
爸爸很喜欢弟弟,在加藤家里,他们俩是一帮,我和母亲是一帮,妹妹好像总是保持中立的位置,很有意思吧?妹妹毕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所以很受父亲喜爱,但同时,她跟母亲的关系也不赖,看来,还是妹妹最聪明,最成熟。
除了具有顽强的毅力之外,弟弟还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优点——善良。他在任何场合都能非常友好地对待任何人,总是首先为他人考虑,自己的事情总是放到最后去做。母亲生病的时候,立刻出去买药,向医生描述母亲病状,鞠躬请求医生的是弟弟;父亲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主动骑车去买几瓶啤酒和几包烟送给爸爸,陪他聊天的是弟弟;我有困难的时候,很自然地伸出手,叫我一起去跑步,跑完请我喝饮料的是弟弟;妹妹被同学欺负的时候,跟她班主任商量,请求尽量保护妹妹使她免受欺负(因为当时经常搬家,换学校,妹妹容易受到一些孩子的排斥和欺负),拉着妹妹的手回家的,也是弟弟。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3)
弟弟后来跟我上了同一所高中——山梨学院大学附属高中,也参加了校运动队。我高二,他高一那年的夏天,我们正准备夏天赴高原集训的时候,发现家里的钱不够了,两个人都去集训,两个星期怎么也需要30万日元(约合两万元人民币),严峻的形势决定了只能一个人去参加。我试图跟弟弟商量时,弟弟突然站起来跟我说:“哥哥,你去吧,我不喜欢那种集体的训练,不如一个人安静地跑步。那种训练方式更适合你,别想太多,你去吧。”弟弟的话不容商量,我无法拒绝,最后,我去参加集训,弟弟没参加,而是一个人在山里训练,他是怎么练的,后来也没告诉过我。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后第一场校队内部比赛,记得是跑3000米。从高一到高三一共30个学生一起比赛,我得了第三名,还行,得第一名的竟然是高中一年级,唯一未参加集训的加藤喜芳——我的弟弟。这就是弟弟,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人能打得过他的。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毅力、耐力以及在关键时刻的爆发力,是我曾经接触过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里面最杰出的。
同时,他很内向,不爱说话,但他又是三兄妹里面最有礼貌,最低调和最谦逊的人。我这个人不行,爱突出自我,爱与众不同,总希望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强,太不懂得谦虚和收敛。像弟弟那样真正的帅气(对,弟弟很帅,每年的情人节,我拿到的巧克力也不少,但从来都不如弟弟收到的多),我是做不到的。我知道,弟弟一直很羡慕我,觉得哥哥各方面很突出,很有色彩,事实是,我一直羡慕着弟弟,欣赏他做人的方式,做人的态度,甚至有点钦佩。只是弟弟可能并不知道而已。
关于我的弟弟喜芳和妹妹萌美,大概介绍完了。在这里我想告诉朋友们,我这个长子是在他们的支撑下长大的。他们给予我的信任对于我也是一种压力,面对他们的信任和期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也只好坚持到底,尽可能做得像个长子的样子。否则说不过去,也站不住脚,也很没有面子。如今弟弟已经开始工作了,作为出色的营养管理师,他负责医院、体校等多个机构的营养管理。妹妹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到骄傲,是的,他们永远是我的骄傲。
话题再回到应对逼债者这件事上来。
过了几天,讨债的黑道来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问:“你爸在不在?”
我说:“不在,他忙着工作,他也不住在这里。”
忽然间,有条腿冲着我的肚子踢过来了:“你这小子他妈的骗我,快说真话!”
我说:“真的不在啊,我骗你干吗?”
“你跟你爸说一下,再不还债,就会有大麻烦了,明白吗小子?!”
那天晚上,爸爸真的是不在家的。他除了白天协调很不顺利的新业务之外,早上要送报纸,晚上还要到道路工程现场做类似调度的工作,过了十二点才回家。母亲也差不多,每天早上7点半出发,晚上10点多才回家。我们家当时就是这样辛苦地勉强维持生计的。我后来跟父母汇报说黑道的人来了,他们担心我有没有受伤害,我说:“没什么,他们不会对小孩子怎么着的。”但母亲建议还是离开这里,过了几天,我们就又搬离了那个家,搬到了十多公里外,房租是每月六万日元,稍微便宜了点,条件当然也差了点,房子比以前小,三间小房间加厨房、卫生间,没有大厅了。黑道是天才的讨债高手,新住地被他们发现只是时间问题。但我为了维护家庭成员的安全和正常生活,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住在哪里的,一旦被发现就麻烦了。我在思考,最有效避开他们的办法是什么。我尝试了许多办法,最常用的一招是,故意给黑道打电话约时间,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见面,但却要装作离家很近似的,并向他们解释“爸爸正在外地赚钱,很快就可以还债了,请再等一等”什么的。我大概每两周主动见他们一次,给出各种借口让他们耐心等待。每次见面都彬彬有礼的,鞠躬,甚至跪下来,请求他们再等一等。有时候还从送报赚的钱里拿出两三万日元交给他们,作为利息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缓和他们的情绪。但那些坏蛋,每次一定一起上来打我,打我的脸、背、肚子,还有对长跑运动员来说最宝贵的双腿……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4)
我从来不还手,还了手,就完了,我没资格还手。当时,我的身体到处都是伤疤,记得泡澡的时候特别痛,但只好忍着,至今为止有些伤疤还留着,也有永远消除不掉的,比如心理上的伤疤。我脖子上有块疤是被他们弄的,具体怎么弄的,我就不细说了,太残酷了,我不想把我那几个同胞人性中的丑陋和残忍暴露在中国读者朋友面前。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样面对黑道们有可能是不明智的,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只能那样做,以保护弟弟和妹妹,让父母集中精力打工,以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存。
我跟黑道们“谈判”了将近三年,一直到高中三年级的秋天。黑道们不再追我们了,一方面是我负责翻译工作的企业的老板很同情我,帮我想办法,联系在日本很有威信的地方势力,给那帮人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一直相信新公司能够时来运转,一定能还清债务的父亲终于对现实妥协了——正式宣布破产,那样可以不还债,只是接下来的事业和生活都要受到各种限制。
逃债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感到有些不对劲儿,甚至有些不适应看不见黑道的日子。当然,可以抱着平常心过好每一天了,这让我们全家人从前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只是难以忘记父母每次看到我脸上伤疤时的表情,那种心疼,那种愧疚。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没事,真的没事,你们好好打工,这一难关,一定能过去。”在那段时间,我的努力,我的坚持,我的执著,实话实说,都是为了复仇。我当时非常恨这个社会,觉得太不公平,太不人道,也多次思考过为什么只有我们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过得这么苦。一边挨打,一边痛恨,一边倒下,一边沉思……向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复仇,在那几年时间里一直是让我挺下来的最大动力。现在,虽然一切都慢慢好起来,但要完全清理掉心底的阴影,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有时,我跟母亲还会回望那些逃债的日子。记得姥姥经常劝告母亲跟父亲离婚,可以理解,自己的女儿过着那么辛苦的日子,任何母亲都会心中不忍的。但我的母亲坚持下来了,因为有三个孩子,她觉得离婚对孩子不好。我很佩服母亲的坚韧,也非常感激母亲为了我们所付出的牺牲。我曾半开玩笑地跟她说,“其实,我还是很珍惜那段日子的,那么小就有了那么苦的经历,以后无论再遇到什么都不会感到苦的,你说这是不是伟大的精神财富?而且,跟那些黑道的谈判过程真让我坚强了很多,应该积极看待那段日子。”母亲照例回应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了。”
结束本章之前,再来说说我父亲的事业为何未成功。如前所述,我爸爸的新事业就是从矿山挖沙子、运沙子、卖沙子。事情说起来非常简单,挖掘的技术都具备,客户也落实好了,但在运输环节上出了问题。运沙子是个大工程,载重汽车轰鸣,当地人害怕生活受到影响,更大的难题是,当地居民并不同意父亲他们搞那样的开采,于是就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