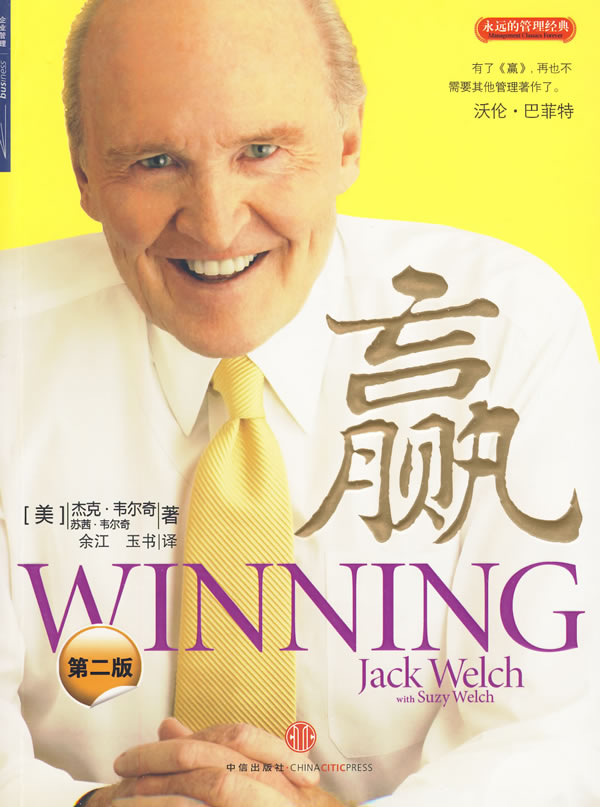马赛克-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其实就是这样。并非你使出十万分努力就能得到回报。种种执着所能求的,也不过听个响。就该知足。
☆、镣铐
谢荣生审了我一夜。
我为了显示自己积极的态度,话多了些。
我说自己怎样盯上任晴,任晴如何带我回家,任晴有一个怎样的女朋友,我又是怎么死缠烂打拆散她们。我说我和任晴干柴烈火,她给我“失忆”,我才发现她就把毒品藏在家里。
我断断续续地蹦字,后来疼得紧了,他开恩给了我一颗止痛片,我才囫囵说起来。颠三倒四地,很多细节他听得不分明,就来回问我。
等到有人送早餐进来,他才恍然发现我说得没一句重点,把岳明和南楠撇得干净。
谢荣生再问,我就说这些天查南楠的场子,大大小小跑了个遍。
又过了几个小时,我讲得来了兴致,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人看起来怎样长相凶悍先动起手来。末了,发现不过是个小偷小摸。
谢荣生恼怒起来。反锁了房门,拽着我领子,将我甩在地上。
椅子随着我摔倒在地,正压住右脚脚踝,剧烈地疼,我眼泪都要下来。手铐拖着翻到的椅子上,手腕扯出血。
“够能扯的啊,看来你精神不错,那就站起来活动活动好了。”
我依着他的说法,用手肘支着地,跪坐着,想要站起来。脚踝骨折一样疼,使不出力气。手臂被手铐拽着连在椅子后腿上端,卡着,腿卡着椅面,木椅又高又重,一时站不起来。
谢荣生就那么坐回去喝着茶冷眼看我,
“等一会儿你的检测报告就送过来了。要还是这个场面,我没法开门,他们就交到缉毒科去了。到时候别怪我不护着你。”
虽然觉得他贪功应该不舍得这么快把我交到别人手里。到时候他要审我手续复杂不说,更没那么容易滥用私刑。但如果惹恼他,让他觉得绝无希望从我这里挖出什么,那就未必再留我。谢荣生说得对,凭我现在上瘾的程度和身体状况,不必说缉毒科环境如何,断了“失忆”不出五天,吾命休矣。
我一次次尝试,扭曲姿势,将木椅先扶起来,才拉着椅子半坐住。本来坐在椅子上手铐的长度还有宽松。想要站着,就不得不将椅背拉得翘起。椅背顶在我脊梁上,手臂被向后拽起。就算这样也只能曲腿站立。
他看我这样费力,轻哼一声,
“你进来到现在将近九个小时,自己不着急,我更不急。”
响起敲门声,他开了锁,拿过报告,
“还有六十多个钟头,不过我想要不了那么久你就该说了。你也不必激我,刑讯逼供那一套我比你懂。不需要怎么花心思对付你,再过几个小时,戒断反应就够你喝一壶。呵,查了这么久还没见过‘失忆’毒瘾犯了的样子。刚好你做个宣传片,给大家好好看看。”
他叫了两个亲信继续审我,转身出去。
冷汗一层层下来。
重新打了灯光,逼得我拖着椅子站在亮里,不断重复回答过的问题。手铐嵌在肉里,黏腻的血一点一滴落下,手痛得将要麻木。空调调得更低,半曲着膝站着,膝盖从痛到麻木。大腿肌肉抽筋了似的痛,抖个不停。
止痛片失效后,疼痛就密密地传来。
我渐渐失去思考的力气,基本的问题就回答,其他一律不知道,实在逼急了,就背之前上交的报告。饶是这样,好几次痛得说不出话。
神智越来越模糊。站不住倒下去,又被扶起来。到后来索性也不再管我,由我坐着。
他们晚上交班的时候,戒断反应逐渐强烈起来。一天一夜喋喋不休,我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他们把我换到审讯室。铁制仿紫檀木的椅子钉在地上,扶手间锁住挡板,又用手铐将手脚固定,保证我没有办法移动。我没想过坐这么高端大气的高椅。
又痛又痒的感觉从骨子里冒出来,好像锉子在身上的每一处骨节来回划割。身体又被椅子卡得死死的,只有镣铐滑动发出暴躁的声响,嵌入骨肉传来摩擦的钝痛。我弓着身子颤抖,他们就耐着性子审问,等我缓慢地吐出几个字。
再往后我已经完全失控,用头撞隔板,站不起身又一次次乱动乱碰。整个房间都是镣铐与铁椅撞击的巨响。血和着汗不断淌下来。
他们就只是看着我,减少我晕厥的时间。
在我稍微清醒的时候,谢荣生进来。逼着我看尸检的照片。青白的皮肤现出紫红色的尸斑。腹部的创伤处皮肉外翻,被水泡过而显得肿胀。最后一张是任晴的头像。在青色的光下,眉目还露出痛苦的表情。
“被刺穿两次,基本可以认为在同一位置。下手是有目的性的,切口平滑,动作非常快。内脏被刺穿,尸体散发出内脏气息。又在流水冲刷下,迅速失血。那种感觉应该是非常冷,很痛苦。”
“……”
我紧闭双眼,弓下身干呕着,稍微平缓的痛苦再度加剧。手紧紧攥在扶手上,指甲狠狠抠着。
“怎么,你也会觉得愧疚?”
谢荣生给了我一耳光,
“任晴为什么死,你敢说不知道?有种就对着她的照片,你还说得出之前的话?”
“……我录的口供,都是实话实说。之前怎样,之后还是怎样。”
我睁开眼,抬起头看他。他戳中我的痛处,纵然我勉强坚持,对着任晴的头像谎言依旧,却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身体。
从没有觉得时间这样长,只是维系生命就如此艰难。血管随着心脏跳动不断突起。呼吸越来越困难,每一下都费尽力气。耳边塞满了质问的言语,大脑将要爆炸一样。
这样痛苦的滋味,超过临界。
忽然想起一年多之前,审判南楠,我在法庭上翻供。退庭后我直接拦住南楠的律师,坐上他们的车子,在重案组一众注目下扬长而去。
那一晚的经历,我一直不敢回忆。
我跟着他们迅速回到旅馆。主辨律师叫助手记录,要我将整个案件作为机密的卷宗背诵出来,供他们整理找寻突破口。
我接触审讯的部分记忆深刻。背诵地极快,用录音笔录下,然后分给几个助手输入电脑。这样连续不断地拼命回忆,加上时间急迫的紧张,头脑像要被榨干一样。
但没有办法休息。一停下来就想到公诉那边同样因为我的临阵倒戈连夜准备。
助手们轮替着吃饭。小刀把我的一份拿过来,我动了筷子,吃下去,又吐出来。前一晚熬夜喝白酒,又一天没有吃东西,胃痛得要命。但如此密集的记忆挖掘让我只觉得恶心。
持续下去,越来越混乱起来,常常前言不搭后语。律师拿着整理出来磕磕绊绊的文稿,又再三跟我强调细节最重要,让我务必精准。我只能不断地喝浓茶,抽烟。叫小刀拿桶装了冰水,在间歇时把头泡进去。这样极力维持清明。
到后半夜,脑子里已经一团浆糊。剩下占一半的卷宗交到我手里也不过翻了几遍。把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是卧底前特别训练的内容。当时我是凭本能背下,但隔了这些天,看过这么多资料,加上先前的背诵,远远超过训练时的极限。我越是努力回想,越觉得头痛欲裂。只是闭上眼睛,就好像随时可以睡去一样。
主辨律师听我大致报了一遍剩下卷宗的内容,指定有几个南家亲戚和担负要职亲信的审讯记录一定要一字不差背出来。
烟抽太多,嗓子哑到几乎说不出话。我就要了电脑打字。打着打着,烟灰就抖在键盘上,直到烫了手才发觉。或者索性叼着,烟烧短了,熏得眼睛疼。
第一遍凭记忆写下的凌乱不堪,我又大致梳理。回过神来,窗外已经大亮。房间里的人一个个看起来狂热而憔悴。
到了早上我开始发烧。因为律师需要时间整理剩余的资料,不再需要我背卷宗。小睡半个小时,又在噩梦里惊醒。
律师塞给我几千字的证词。我拿着看了几遍,白纸黑字,竟然看不懂意思。头痛加上胃痛,分不清哪里更剧烈。即使吃了小刀买的止痛药也没有一丝一毫缓解的迹象。我泡进放满冷水的浴缸里,仍然没有办法集中注意。
不得不打了兴奋剂。
临开庭我给主辨律师说证词,被驳得哑口无言。我看得出所有人都很紧张,小刀攥着拳头盯着我。我们围绕着防守准备得在充分,也比不上我这个南楠贴身保镖的证词有力。越是这样的时候,过往的一幕幕,卷宗里的陈述,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闪过。我就那么忽然晕过去。
但再醒来时,精神稍微恢复了几分。我强迫自己记忆,回想所有被指出的问题。
最后站在法庭上时,我们合作完美无缺。唯一美中不足是南楠在我发言的最后,起身破口大骂。
庭上宣布审判时,小刀激动地要喊起来。然而我并不能分享他们的喜悦。只有公诉一方,所有人向我投来责难和鄙夷的目光。
我跟他们共事那样久,一同查这个案子,日日点灯熬油,难道他们是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我可以不在乎什么是道德和正义,但为了南楠不断背弃自己的生活。每一次背叛,心碎一次。粉身碎骨,我还要怎样继续?
南楠踏出法庭时回过身来对我道:“郑乐,我不会放过你的。”
但她不知道我几乎是一夜白头,那一刻已经被抽干了力气。
闪光灯迭声叫嚣。我只能对着耀眼的虚空,微笑。
那样的往事没有人再提。南楠自然都不会知道。
因为太过痛苦,我自己也避免回忆。
但这个时候。在审讯室里。“失忆”的瘾上来,我却重新忆起。
当我眼前再度出现南楠踏出法庭的画面,光线一点点充溢眼前,吞噬掉整个视野。渐渐得,耳边再没有一丝声音,浑身抽痛也淡去。身体变得很远很远,再没有烦恼可言。
我逐渐失去意识。
作者有话要说: 看了济南异地审理那个案子的庭审记录。觉得之前法院那段写得太粗糙了。被逼到跟亲人朋友对峙,怎么说也太惨了。政治斗争叫老婆孩子划清界线什么的,差不多总是这样。
成王败寇的世界,没有道理可讲
☆、驾鹤
小马办好手续,站在警局大厅里等着。从郑乐进去到现在两天半,足有六十个小时。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提前释放的手续并不好跑,加上警局这一次难得地强硬态度,拖到现在。
等检察院提审后没有批准逮捕,人才被放出来。
郑乐被两个小警察推着,纵然手脚用衣服遮着,也露出血痕。脚踝肿得和鞋口一样粗。脸色苍白得吓人,皮肤像风干了,没有弹性。嘴唇干燥脱皮露出灰白的颜色,下唇咬破了几处,还渗着血。
“呃……”
郑乐摆脱了小马伸来的手,将交到警局的随身物品一样一样收回身上,自己一步三摇地走出去。小马赶紧跟着,抢先推开门,开了车过来。
“谢队,就这么放了?她好像知道的不少。”重案组小汪看着郑乐单薄的背影,小声道。
“哼……”谢荣生翻看了这几天的记录。郑乐嘴里吐出来的,零星不全,到后面虽然泰半和南楠相关,但都是当年旧事,全是卷宗里记好的。本打算在她身体和心理都接近崩溃的时候套出些有用的东西,结果这个人防备太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