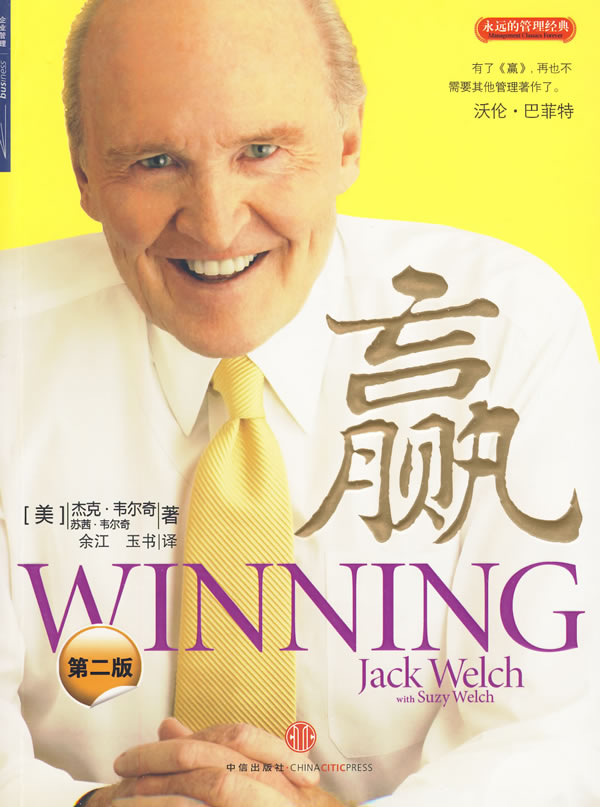马赛克-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 m。。……… 【wwl】整理
================
书名:马赛克(黑道)
作者:黯雪时晴
==================
☆、救人
作者有话要说: 整篇估计就是一直很虐。
是不是为虐而虐呢?我就不知道了。至少不是满清十大酷刑。
这个世界的哲学是,你随时随地都会死。但悲剧是,那一刻始终未降临。
Marla’s philosophy of life was that she might die at any moment。 The tragedy; she said; was that she didn’t。
——《搏击俱乐部》
狂奔,狂奔。下水道泛起浅绿色带着热度的不明气体,被踩得畸形的易拉罐撞击在覆着苔藓潮湿墙面上发出的咣当声在窄巷里一遍遍回响直至湮灭。空气阴冷稀薄。不远处水滴敲击岩石有节律地发出啪嗒声,声音逐渐放大,频率也渐次增快,像云子倾斜坠地,轻轻巧巧,却是接连不断地紧随而来。
不敢回头,不知逃避何物。景物渐次退后,巷子却似无尽,封锁在潮湿腐旧的色调里。转过道弯,却是一面墙。磨砂的马赛克瓷砖拼接,和周围景物并不协调。敲击砖面,竟然发出清脆的回响。砖面似乎松动,一片片忽然剥离跌落,露出纸糊一样透光的薄层。戳破一个洞,强光像箭一样激射而出。
从这样的梦境里醒来,浑身汗湿。手机屏幕渗出惨白的光,映在床头的台灯上。粗线条的古铜色支架围城花瓶一样的形状,彩色玻璃镶嵌其中,拼成碎裂的图案。南楠喜欢马赛克的装饰,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暗含规律。
抓起手机,两个未接来电。恐怕出了什么事。
因为南楠在睡,手机关掉振动调成静音。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仅仅是手机微弱的亮都可以把自己惊起。黑夜很长,却也习惯了静静聆听呼吸声,只凭这一丝存在的痕迹,维系到天明。
南楠枕着我的左臂睡得正沉。我侧过头,手机光打在枕头上。阿崇打来的。这小子又惹什么官司。正迟疑着,新来电插入。
在静夜里,这样的环境实在太过嘈杂。好像隔着什么,远远地听不清谁在说什么。隐约能分辨出重低音的节奏声。
“阿乐……”伴着大喘息。
“唔。”我含混地轻声应道。
那边忽然挂断了。再打过去,变成不在服务区。恐怕是直接卸掉了电池。
问题似乎严重。我抽出手臂,跳下床。
“阿乐?”南楠的声音带着睡意,夜特有的抚媚。
“嗯,嗯。”我拍拍她隔空探来的手臂,把薄被重新掖好,十月光景,夜晚已很有些凉。“没事哦,很快就回来。”
捡起地毯上的衣裤,掩上卧室门。赤脚在厅里大理石面地板上金鸡独立,一丝凉意窜上来。提起裤腰,触到后腰的硬物,心定下来。
南楠新添的双门轿跑,一直说要晚上兜风,结果每次都是我一人半夜救急出去。南楠也曾在夜深里撒娇着抱怨我事多,白天变脸似的常常带我见人,又说有事找我就好,还不忘夸我办事利索身手好。
南楠有意扶植我的势力。在道上混凭的是仗义和实力,非生即死,就算是女人。我不确定能给她什么安全感,南楠却并不介意。越知道这条路是凶险小径,越要拼尽全力为未来扫清障碍。
拨出第八个电话,终于接通。其间我打给常和阿崇一起的小松,小松说阿崇整天神神叨叨不知道忙些什么,喝花酒都不去。
最麻烦的就是这种单独行动,势单力薄不说,还要瞒过熟识的人。敲出一支烟点了。
拨号声沉静地在耳边回响。实话说我确实心急,电话里的俄罗斯风迪曲似乎在一个星期前听过。奉兴会程徒堂主经营的场子。那块地盘好,场地大,演出又卖力,夜夜火爆。是程徒手里最吸金的宝贝。如果别的店用了那里的曲子也不稀奇。查SIM卡的位置自然直接,但我隐约觉得阿崇接了外快,不能向帮里的兄弟开口。更无其他线索。
那边忽然接通了。换了安静的环境,对方是老鸟不肯开口,只能听到呼吸声。
“喂?有人吗?”OK,那就由我先。
那边沉吟半晌,“你是哪个?”戒备的男声。
我们的通讯录不存全名,我忽然觉得对方拖延的反应,根本不知道阿崇是哪个山头。然而这种调查只需要很少的时间。
“阿崇的……朋友。”
“嗬。”像嗤笑,语调里似乎松懈了几分,“这小子倒有艳福。”
想到哪里去了?
笑声异常熟悉,脑海里出现一个梳着小辫子,背上有老鹰纹身的健壮男子。程徒的亲信。果然是那家场子。
“阿崇呢?叫他听。”南楠常说我电话里的声音娇滴滴的别提多撩人,可惜见光死。
“你男人在我们的场子里卖K粉。这可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找人来带他吧。”倒是和颜悦色,轻视了的语调。
在别人的场子里贩毒,抓一次打一次。说小了是贪财又不拜地头大哥,说大了就是陷害人家。更何况阿崇所在的堂口紧挨着奉兴会,两边可算不上善交,弄不好就是倾覆天平的大事。
初入六合会时,我就和阿崇一道在丁叔管辖的梁婆街做事。六合会和奉兴会交界的地带,纵然双方宣告休战多年,底下人还是少不了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火拼。丁叔向来管教得严厉。在丁叔堂口的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丁叔对待下属出手极其大方,就有许多人宁肯死也要挤进来。
阿崇在丁叔手下三年了,刀尖上活下来的人,除了身手还得有一副好脑子。我真不大相信他可以这样铤而走险。
“……”
听我不说话,那边道:“叫他大哥来就好了,半个小时,或者你就考虑换个男人吧。”然后竟然是爽朗的笑声。虽然幸灾乐祸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但声音倒并不难听,还算当得起风流名声。
“等等!在哪里?”
“南码头12号仓库。”
电话戛然而止。
打开车窗,风倒灌进来,烟味散了散。我调转车头,从靴子内侧抽出另一张SIM卡。
虽是深夜,南码头灯火通明。这是奉兴会程徒的地盘。
隔着十余米便有一黑衣人影在路灯下。铺张的排岗方式,无言地透露出逼人的气势。
我微微皱眉,车子停在一旁,刚下车便有两个黑色短打身材匀称的年轻男人逼过来。
“你是?”
“郑乐。我来带人。”
两个男人面面相觑,显然没听说过我这号人。我露出左手,小指被斩断半截。对方倏然变色。
六合会早年有不成文的规矩,入帮派要断指示忠。这是一辈子不可恢复的痕迹,意思浅显。现在六合会积极漂白,会里大多数人不必守这样的规矩。但我是从最底层的梁婆街爬上来,六合会的死士,即便今日守得也是旧年的规矩。
库房里堆着包装箱,绕过大小不一染着潮痕的纸箱,老鹰正站在当中。“原来是南大小姐身边的人,失敬失敬。”
我并不理会,目光扫向一旁。阿崇被捆着倒在地上,浑身是血,一双手别在身下,紧紧攥着。难怪没有察觉阿崇的断指,整个人灰头土脸得瘫成一团,装成怕事的样子,任谁都懒得细瞧。似乎察觉到了我来,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嘶声。绑都绑了,下手还这么狠,这男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怎么都不能划归为风流倜傥的大哥啊,道上的女人都怎么了。
“他出来单干,我是他朋友。还请教怎样才能放人?”
我一本正经道。
分辨出我的声音,老鹰微微一怔。的确,我看起来实在不像能发出那样温柔声音的女人。笔直的长发在脑后束成一捆,刘海遮挡着侧脸。黑色夹克,黑色牛仔裤,黑色短靴。“像从地狱爬出来的,”南楠就这么埋汰我的装扮。
“单干?这样就和六合会撇得干净?既然这么逞能,那就照规矩办——留下点东西。”
最后几个字说出口好像说着前一天的天气,脸上还带着笑意。双臂交叠露出肱二头肌上蜈蚣般夸张的刀疤,这是比刺青更好的炫耀。
所谓留下点东西,那非得断手断脚。太暴力,我在心里画个叉叉。
我冷笑,
“我手里大约有你感兴趣的东西,何必要那些没用的?”
面对手心里的猎物,他大可以好整以暇。
我扫视周围的打手。
老鹰做了个手势。没有人发出一声异议,安静迅速地退下去。这一点我倒是有几分佩服。
“关于燕金姐。哦,你该叫大嫂的。”
老鹰瞳孔收缩,露出鹰隼一样的凶光。
于是我正中要害。
“我有一点照片,自己留着也没什么用,本打算过几日送给你们堂主做寿礼,现在觉得还是送给你比较合适。阿崇也学了教训,不如就让我带回去。”
程徒正当壮年,论体格不该比老鹰差多少,怎么就满足不了一个小女人?
老鹰沉思半晌,
“若有消息流出去……”
“大可放心,若有一张流出去,随时来找我。”
老鹰的眉头微微一皱。
我便不再理会,径自解开阿崇身上绳索,听他闷哼一声,脸已经疼的扭曲。大约断了肋骨。
“能走吗?”
他连忙点头。
我刚将他扶起,老鹰忽然开口:
“慢着,东西呢?”
“这样要紧的东西当然不会随身携带。”我脸上大概挂着笑,老鹰脸色更差。“你若对底片有兴趣,过几日寄到你家?”
“不用。毁掉就行。南大小姐身边的人我还是信得过的。”
好一句阴阳怪气的反话。我答应着,将阿崇手臂搭在肩上,扶他勉强行走。就这般大摇大摆地出去,倒没人阻拦。
☆、暗涌
将阿崇拖上副驾,关好车门,我真心后悔开了这么辆华而不实的车,塞人十分地不方便,沾了血又难以跟南楠交代。忽然身后传来刹车声。三菱单厢。老鹰的手下变戏法一样拖着拳头粗的木棍或是长刀迅速将我的轿跑和那辆三菱团团围住。三菱侧门滑开,跳出的精壮汉子个个手里带着战俘刀。哑光,刃口小齿交错,带血槽。拼命的架势。
就只眨眼的功夫,刀穿透拦我的人,拔出的一瞬鲜血雾一样喷涌而出。下山猛虎的势头,两边就要厮杀起来。
“住手!”我暴喝一声,眼见已是一阵血雨。我抽出后腰的匕首,直朝战俘刀挡去,手臂一麻,战俘刀沿着匕首滑下。我向后跳出一步,堪堪避过。不妨身后一凉。闪身躲避,才勉强卸去力道。
带队的正是小松,像是为我的格挡吃了一惊。把我护在身后与砍伤我的老鹰手下对峙。
“怎么回事?”老鹰走出来。这么一个停顿的功夫,老鹰的手下窜出不少,我们就成了海里的一叶小舟。
一阵寒意从背部透进来,接着是火辣辣的疼。
老鹰显然看见了倒在血泊里的手下,眉头拧起。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郑乐,我给你面子,人都让你带走了,这是什么意思?”
我正待开口。忽然有人站出来,当先那个死士。
“实在是误会了,兄弟不懂事,给您赔罪。”小松反手将战俘刀插入那死士的腹部,抽刀的一瞬,那人咬紧牙关一声不响地窝倒下去。战俘刀刃□错的小口刺入人体会造成无法愈合的巨大伤口。这一下直穿过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