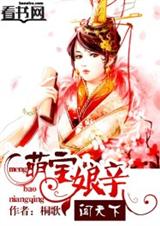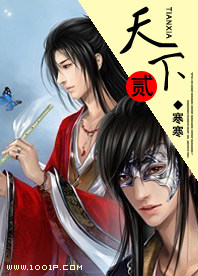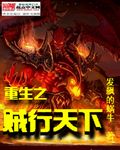医行天下-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分钟。第二天早晨再点穴几分钟,病人已经能说话、吃饭,第三天早晨再点穴几分钟,病人就下地走路了,到这时总共累计的点穴治疗时间还不到一小时。病人一星期后完全康复出院,我第二年去病人家回访,发现她不仅没有任何后遗症,而且继续在老年腰鼓队活蹦乱跳地打腰鼓。中医点穴治病,原来可以如此简单有效!
老李自幼习武,在湘西的河流上跟各类奇人怪杰学了不少江湖绝技,其中有武术、医术,也有巫术,他甚至向监狱里放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偷偷学习。他点穴治病的绝技就是从武术的点穴中渐渐演化发展而来的,他已经用点穴治好了很多中风导致的偏瘫和心脑血管疾病。他的病人大多被抬着进来走着出去,而且几乎全是在医院治疗无效而退出的“垃圾病人”。
回到北京,我就开始对李仕平进行宣传推广。我不仅将国内的病人,而且将美国、台湾和香港的病人陆续带到湘西,令李仕平倍受鼓舞。后来我将几十个由外国针灸师组成的国际中医代表团带到湘西考察,包括澳洲的“冲浪道人”沃利。为进一步推广点穴法,李仕平执意让我跟他学医,因为我云游未完,没敢贸然答允。后来他又几度来电催促,让我赶紧开始学点穴。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跨入了中医江湖。
5、春节学医
今年的春节与往年不同,我不仅云游异乡,而且开始了学医生涯。这是一种新游戏:一边学医,一边读书,一边练气功。气对医者极为重要,所以我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对着冉冉升起的太阳练气功。点穴须用手指,站桩练手指的气感,可一直要练到手指能感到呼吸的脉搏。练气是东方式的实证方式,而且必须在活人身上实证。
师带徒学医是直接在临床实践中学习,中国的传统技艺几乎全是用此法传承,琴、棋、书、画、戏、武等等,无一例外。我学习的第一天就直接在师傅身上点穴,他也在我身上点,以便我体会。由于种种原因,学习进度极慢,每天真正学习点穴的时间大约只有几分钟,但我早晚跟着他在病房中临床观察半小时。这样我每天学医的时间合计也不超过一小时,其余的时间都自由支配,我比在家有更多的时间。
大年三十前一天,我跟师傅一起划船去看望一位在酉水上漂泊的孤寡老人,给他送了年货和钱。老人因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长期头晕眼花,一位徒弟用点穴为他治好了病,不仅免费治疗,还在过年前给他送来年货。老人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他独自一人从常德闯荡到此二十多年,至今仍说一口常德话,那条破船就是他的家。老人站立船头的孤影,倒映寒水的孤舟,加上我这个孤独漂泊的心,真是一种恍惚凄美的意境。老人和我,还有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风景,似乎就是对“闯荡江湖”四个字的生动写照。
一个月以后,我学完了点头部穴位。至于身上的穴位,师傅让我跟着他儿子们学。我和几位小伙子每天嘻嘻哈哈地互相点穴,尽管身上的穴位比头上多,我还是很快学会了,就差临床实践。李仕平教的穴位中有一部分是名不见经传的奇穴。中医有言:奇穴治奇病。我越发体验到中医之奇,奥妙所在,不仅靠学,更要靠悟!江南的山水和气候让我重新体验了儿时对大自然的感觉,湿漉漉的,充满地气,绿色中透着一股灵气,那是一种久违的亲切和感动。
大年初三,我从一辆破旧的面的中迎来了好友程迈越。他对一个从前和他一样搞投资的家伙在乡下学医过年充满好奇和热情,所以专程从深圳坐火车到湘西来看我。赶巧的是对我半信半疑的弟弟和对我充满信心的武当山道长,因为他们不约而同,正好在我第一次临床治病那天到达湘西。他们亲眼目睹了我独立点穴调理中风病人的全过程。
病人在县医院被当作心脏病治了5天后,病情恶化,从病床上摔下来后半身不遂,嘴眼歪斜,经邻居介绍转来这里。师傅说这病人归你治,正好考考你的学医进展。那天我穿着白大褂,比平时更像医生。经过我两天的点穴调理,中风老人的血压和歪斜的嘴眼就基本恢复正常,五天后即能缓慢行走。弟弟一直认为我四处云游是不务正业,现在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顿时又惊又喜。道长则自信地对他说,我早说了,这就叫天医命!10天后,我点穴治疗的病人就能自如地行走了。大家开玩笑说,这个七十岁的老人就是我点穴治疗偏瘫的处女作。
面对病人家属充满感激的目光和话语,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人生充满无常,但也充满神迹。我们既是人也是神,既是佛又是魔。一切在乎一念!于是我比病人和他的家属更加充满感激!我感激他们,感激上苍,感激一切!
一旦出现瘫痪病人,家庭的和谐就被破坏了。若点穴能治好瘫痪病人,不也在搞和谐社会吗?不打针吃药,用一种祖宗留下的手法解除痛苦,救人一命,不亦乐乎?若在瘫痪前就点穴消灭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岂不更好?点穴的感觉像艺术创作,充满了美和善。而且,与吃药、手术相比,点穴的风险小得多。如果用点穴让那些长年吃降压药的病人摆脱对药物的依赖,多好?西药之于人体,就如同农药之于庄稼一样,有效,但也有害,所以应适可而止。点穴之美,就在于它不用药,而且有疗效,是个真实不虚的自然、环保疗法。
6、拜师朱增祥
从湘西回到北京后,我经常为朋友治疗头痛、失眠和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很快发现:各种莫名的痛症很普及,过去的老年病正在变得年轻化,疼痛部位更多样化,涵盖腰腿、项背、肩膀、手腕、肘、踝等等,白领阶层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此类痛症和不适。究竟有没有一种疗法能简单有效地治疗这些发病率很高的痛症呢?
就在这时,我见到了在香港美林证券工作的朋友郑杏娟。她得知我在云游学医,就送给我一本书《错缩谈》(即将以《筋长一寸,寿延十年》为名在内地出版),说这是有关中医的,封面是一张慈眉善目的老人照,他就是作者朱增祥。书的名字很怪,读进去才知道“错”是骨头错位,“缩”既筋缩之意。该书对人体痛症的病因有了一种全新的解释:长时间不变的姿势不仅导致筋腱萎缩,而且形成骨头错位,这种细小的筋缩和错位用CT扫描等仪器看不见,却造成了各种莫名的病症,而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头晕、胸闷、颈椎痛、腰痛、手腕痛等等。
书还没读完,我已经对朱大夫肃然起敬,等通读了全书,我已在期盼着早日见到作者。因为书中介绍的疗法和疗效都堪称神奇,西医对此全无概念,连中医对此也未曾有详细记载。不仅如此,作者的风格与个性也很合我的口味:手法外治、化繁为简、立竿见影。全书没有过多的理论,基本上是医病分析,颇似现代案例教学法。其中一部分是他自己写的,一部分是他的患者写的。他的疗法治疗电脑综合症有奇效,而此病正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病之一。
纵观全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朱大夫治疗痛症的效果和速度。很多四处求医无效后来到他这里的患者都被他在谈笑间治愈,所化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半小时。而他所用的疗法并非我们熟悉的推拿、按摩和针灸,而是正骨和拉筋。正骨即调正骨头,拉筋就是将人体内萎缩的筋拉开。病人通常会带来一堆各种医院的报告、诊断书,可是他一般不看报告,而是以病人的主述和亲自观察为依据,常常还没等病人反应过来,病已经治好了。
病人在治好病后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不相信,因为这种结果与他们多年所受的教育和看病经验太不相符。但症状的确解除了,所以又不得不信。朱大夫经常叮嘱病人勿需复诊,自己在家拉筋就可康复,这样既预防、自救,又方便、节省,最符合中医的原则。但这与很多医生希望病人多次复诊以便多赚钱的套路完全相反。病人若执意再来,他会说:你的钱没地方花吗?如此医术和医德,实属罕见。
对于这样一位神奇的朱大夫,我自然神往之。我赶到香港,向郑杏娟表达了拜会朱大夫之意。她心领神会,马上热心举办家宴邀请朱大夫和我赴宴。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和朱大夫居然一见如故,谈笑甚欢。他对我云游深山的学医法非常认可,认为此乃正道,只要治病有效,英雄不问出处。我当场向他示范了我的点穴疗法,他也当场向我传授了拉筋、正骨疗法。后来我再次去香港,他连续两天到住处来看我,既热心给我的朋友治病,又给我当场示范、讲解。我一直不明白,我究竟何德何能,受朱大夫如此器重?朱大夫说,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就这样,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朱大夫门下的弟子。
那次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当天,就有朋友抱怨腰背痛。我当时笑着说,这不是天赐良机么?并声称用刚从香港学的绝招马上就可搞定。说完就用朱大夫教的拉筋法和正脊椎法给他治疗。大家还以为我吹牛,我让他躺在椅子上只拉筋几分钟,其痛感立刻减轻。然后我用朱大夫的手法在背后为他调整腰椎和胸椎,只听胸椎的两节“咔喳”响了两声,说明错位的骨头已经复位,他的痛症当即全消,皆大欢喜。
在此后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朱大夫几乎每天给我一个电话,无论我云游到峨眉山、青城山还是西藏、东北,他的电话都源源不断。我想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如此密集地与人通过这么多长途电话。
7、临床学针
我与针灸有缘,但一直未动手尝试。我的第一个针灸老师是煤炭总医院中医针灸科主任张世雄大夫。三年前,一位澳洲学中医的学生跟张大夫临床实习,我当英文翻译,每周三次跟着张大夫,看他望闻问切,然后取穴、扎针、拔罐。由于张大夫是针灸界的著名专家,医术高超,凡是他当班之日都人满为患,令我对针灸的魔力更有直观感受。当翻译有个好处,就是不得不听懂双方的语言并说出来,这样我被逼比实习生还要认真仔细,渐渐对针灸的兴趣越来越大,干脆拜了张大夫为师,经常到他家讨教。
几乎在认识朱大夫的同时,乐后圣给我引荐了另一位民间针灸高人杨真海,他除了有家传的针灸技法,还有用点穴治疗弱视、近视、老花眼等各种眼疾的绝活。老杨是乐后圣在一家医院的走廊里发现的,他就看了一眼老杨仿佛就看清了他。老杨和我至今也不知道乐后圣究竟用怎样的目光发现了我们与中医乃至我们三人之间的奇缘:乐后圣、杨真海和我,居然都是湖北老乡,而且我们三人老家的距离都不过三十公里,都在一个叫刘家场的古镇赶集。三人在老家彼此不识,却因为中医在北京走到一起。
老杨长的清癯,最醒目的是那满脸的胡子。一问,居然和我留胡子的原因一样,都是乐后圣指点的结果,因为“道人要有道像”。老杨虽然是民间高人,但也是科班出身,不过他在大学学的是地质,一辈子都在搞探矿。他父亲是鄂西山区的一名针灸高人,想在临终前将针灸绝活传给后人,但没一个子女原意搞针灸。老杨正好赶上单位解散,于是回到家乡,在老爸去世前扎扎实实地跟着学了一年。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