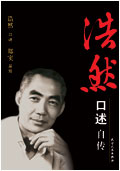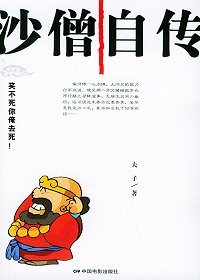贝·布托自传-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成千上万的贺电从世界各地发来,不管是政府首脑还是平民百姓都给我写信,共享欢乐。这对于广大年轻女性来说尤其是个重大时刻,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生育小孩同时不影响工作,即使处在充满挑战的领导岗位。第二天我就开始工作,阅读政府文报,签署政府文件。后来我才了解到,我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边工作边生小孩的政府首脑。既然这样,以后的女总理们也不必把它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要大胆地去冲破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新版序言(3)
巴哈特瓦生于1990年1月。7个月之后的8月6号,总统违背民主解散了我的政府,那时候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聚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无暇顾及巴基斯坦。我的丈夫被逮捕,母亲劝我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与孩子们分离无疑像揪心一样疼痛。那时候比拉瓦尔才两岁,巴哈特瓦还不到一岁。我的妹妹住在伦敦,愿意照看他们。我的公公婆婆也来帮忙,不顾一把年纪搬到了伦敦。在家里我连做恶梦,听到孩子们在哭着要妈妈。我经常给妹妹打电话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她告诉我不要担心,但是梦魇还是挥之不去。
政府被解散后,港口城市卡拉奇一片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恐怖活动猖獗,无辜的平民遭到屠杀,惨死在公交车上,在家门口,甚至在办公室里。我知道孩子们住在伦敦相对更安全,但我仍然夜不能寐,时常被恶梦惊醒。
我和母亲大部分时间住在首都###堡。我丈夫在1990年当选议员,现在只要议会一开会,他就被当局软禁在家。我向丈夫和母亲倾诉,跟孩子们分离对我是多么大的折磨。我觉得是我抛弃了他们,我担心他们的心智成长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1991年,比拉瓦尔开始在伦敦昆斯凯特区上幼儿园。巴哈特瓦这时才一岁。我突然想,把这个小不点安全地藏在巴基斯坦的家中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我径直飞往了伦敦,迫不及待地奔向妹妹的公寓。刚到门口,就听到女儿在哭,正是我在梦里听到的哭声。我急忙把她抱进怀里,又拉过儿子。“我决定把巴哈特瓦带走,”我告诉妹妹。她立刻舒了一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你担心,这孩子一直哭了好几个月了。”
无需言语,两个孩子好像都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的场景,比拉瓦尔穿着白衬衫,蓝条裤,白袜子,小黑鞋,呆呆地站在走廊上,背靠着墙,棕色的眼神充满悲伤,茫然、默默地望着我。没有哪个母亲忍心把两岁的儿子丢下不管,也没有哪个孩子能想到母亲会带走另一个孩子却把他丢下。
把巴哈特瓦抱在怀里,我驱车直奔希斯罗机场。她在我的怀中安静无声。我带着她登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9个多小时的航程,巴哈特瓦一声都没有哭,她把小脸埋在我的肩上,酣然而睡。巴基斯坦有名的音乐艺术家牢吉汗女士当时坐在我的身旁,她看到小不点这么乖觉得很惊奇,对我说:“我在飞机上从来没见过这么安静的小孩。”
公公婆婆决定仍然留在伦敦,帮我妹妹照顾比拉瓦尔。让我稍感宽慰的是比拉瓦尔有家人陪伴,可以在海德公园散步,喂鸭子和小松鼠,这些能暂时转移他的注意力。
1990年人民党政府被解散,我又重新参加竞选活动,还要经受与孩子们分离的煎熬,应付当局对人民党和我家人的迫害。我心力交瘁,瘦了很多。1992年春天,我发现自己怀上了另一个孩子,我们的家庭在扩大,这带给我极大的快乐。然而这时候国家局势动荡,当局在卡拉奇展开了军事行动。少数族裔政党统一民族运动党(MQM)挑起血腥事端,谢里夫政府指控该党蓄谋分裂国家、妄图建立一个所谓“真纳普尔”的独立国家。军方公布了蓄谋的“真纳普尔”国地图,随即开始了军事镇压。大多数国民已经厌倦了社会争斗和流血冲突,统一民族运动党的国中之国图谋不会得逞。
军队的坦克开上街道,推倒MQM设置的层层栅门,解救出被封锁的民众,然而这时候巴基斯坦却陷入了更深的危机。谢里夫总理迷信沙特式的政治体系,想把巴基斯坦变成神权国家,强迫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强化神权统治。我的政党在参议院中坚决抵制这项法案,但抗争的时间所剩无几。因为到1994年,谢里夫将在参议院取得多数,那时候他会把巴基斯坦“###化”。
大所数人民反对把巴基斯坦变成神权国家,人民坚守国父真纳的世俗理念。然而军队中的强大势力支持谢里夫,而且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谢里夫才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
。 想看书来
新版序言(4)
当局在财政政策上玩忽职守,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停电现象在人民党执政期间早已消除,而今重新上演。腐败丑闻充斥报纸头条。印度孟买爆炸案使印巴关系急剧恶化,印度把爆炸袭击归咎于巴基斯坦。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首次遭到袭击,巴基斯坦又差一点被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这样,在野党各派坐到了一起,成立了一个大联盟“巴基斯坦民主联盟”,并且号召在1992年11月18日举行一次抗议###。
那时的我非常瘦,没有人以为我就要生小孩。尽管体重下降——也许正因为体重下降,我感觉健康而精力充沛。我的力量被抗议号召再次激发。全国人民都纷纷响应,各地的大篷车已经就绪,准备向拉瓦尔品第进发,向当局展示人民的力量。运动的目标是恢复民主、停止神权和解决民生。
在抗议运动的头一天,我获悉政府将动用武力阻止###。“这说明政府会使用催泪弹。”我对政治秘书纳西德?汗说。我开始担心腹中的胎儿。纳西德找来了护目镜。有人答应给我们准备防毒面具,跟军队用的那种一样,但第二天他们根本就没露面。我们只好随身带上湿毛巾。夜里,一大群人把我家的房子围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发现,一道铁丝网栅栏立在房子周围。当我和党的其他领导走出前门的时候,棍棒迎面而来。党员们爬过铁丝网来奋力保护我,遭到野蛮殴打。
我们中一少部分人奋力穿过铁丝网,找到一辆车,从###堡立即赶往拉瓦尔品第。途中我们不时地遭遇搜索的警车,因此不得不缓慢行驶,而且要把头埋藏起来,以防被发现。忽然我们的面包车刮上了铁丝网路障,动弹不得。我们发现旁边封住的道路上有几辆车,便向其中的一辆吉普车打招呼,车主很同情我们,把车给了我们。最终,穆斯林联盟(伽西姆派)领导人马利克?伽西姆,空军司令阿斯噶尔?汗,现任外长卡苏里,我的政治秘书纳西德?汗,她的丈夫萨夫达尔?阿巴西参议员,还有我的安全官穆纳瓦尔?苏拉瓦尔迪(2004年遇刺身亡),我们七人一起上了这辆吉普车。
幸好铁丝网路障只架设在###堡一带。我们的吉普车一进入拉瓦尔品第狭窄的街道,人民就欢呼沸腾起来。他们开始聚集到我们车子周围,高喊口号。我们一路来到里亚卡特?巴格公园,这里是###地点。
后来警察告诉我,他们之前接到有人报告说我出现在拉瓦尔品第,刚开始对这些举报嗤之以鼻,置之不理。但是随后几分钟里无数相同的电话打来,他们开始当真了,决定亲自来查看个究竟。事实证明这些报告都是真的。于是,一场疯狂的追捕在拉瓦尔品第的街道上展开。我们这辆孤零零的吉普车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催泪弹。一时间警笛大作,混乱一片,整个场景就像007的电影,或者说更像印度宝莱坞的电影。
群众涌到警车和我们的吉普车之间,阻挡警察追击。警察发射催泪弹,还跳下车来用棍棒驱赶人群。催泪弹爆炸,烟雾翻腾,我们就改变方向或者越过人行道驶上另外一条街道。群众为我们欢呼,口号响彻天空。越来越多的警察赶来增援,每条道路都被警车封锁了。现在警察们径直向汽车挡风玻璃发射催泪弹,目标直指我们。挡风玻璃碎了,最终我们的司机受不了了,他踩住了刹车,跳下车去,不见了踪影。警察包围了车子,把我们全都逮捕了。后来,我们还是被释放了,这次活动给当局者造成重创。
不知道是不是催泪瓦斯的关系,自从这次事件后,我的胆囊就开始疼痛。我服用顺势疗法的药物,但疼痛仍不见消减,而且经常疼得不堪忍受。如果采取手术治疗的话,我将冒失去孩子的风险,我不愿冒这么大的风险。后来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只好飞往伦敦求医。医生们的建议是尽快剖腹产生下胎儿,然后立即进行微创手术切除胆囊。1993年2月3日,我的小女儿阿西法降生在波特兰医院,我搂起可爱的小宝贝。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新版序言(5)
当时我并不知道,随着小阿西法的降生,我们的家庭已经不能再扩大了。不久,人民党于1993年10月24日再度赢得大选。然而在巴基斯坦重复性的政治轮回中,我的第二届政府于1996年再次被非民主地解散,我的丈夫阿西夫随之被捕。令人伤心的是,当他2004年11月出狱时,我的年龄已经不允许再要小孩了。
我们庆祝小阿西法的诞生,那时我却不知道母亲的老年痴呆症已经越来越严重。她的病源于1977年,那天我们在拉合尔看板球赛,齐亚将军的帮凶用棍棒殴打我们。母亲遍体鳞伤,头部受伤尤其严重。从那以后,她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但是现在病情恶化得太快,太突然,令人心碎。
我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美丽、优雅、迷人的母亲淡去,她的生命之烛逐渐暗淡、微弱。这位坚强的女性,曾经为反对军事独裁不屈地抗争,曾经为妇女争取权力英勇地冲锋,而现在却病得几乎不认识人了,也不会说话了。她已经不会说自己饿不饿,牙疼不疼了。看到向来坚强的妈妈现在如此的无助,我心如刀绞。然而我仍然感谢真主,让妈妈还坚强地活着,与我相伴。她的存在给予我无穷的力量,她是连接我们家族血脉、亲情和爱的纽带,使我牢记不屈的信念,还有我们共同经历的风雨坎坷、共同的悲伤与欢乐。
阿西夫的长期监禁是家庭的巨大痛楚。孩子们在童年时期没有爸爸在身边——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他的囚禁也说明男性主义思想仍然主导社会。试想,一个家庭主妇会因为她丈夫的政治事业,在毫无证据和宣判的情况下被作为人质监禁八年吗?当然不会。但这种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就必须面对。出狱不久,阿西夫心脏病严重发作,险些撒手人寰。
置身国外看巴基斯坦,我认识到祖国现在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急。毫无疑问,如果西方国家继续纵容军事统治者压制民主自由,新一代恐怖分子将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中演化出来,盗用###之名,与西方进行暴力对抗。重塑自由民主政府绝不仅仅是巴基斯坦人民的诉求,也是全世界所有力图避免“文明冲突”的有识之士的目标。
当我在伦敦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虽然吸引人,却也折磨人。我不论走到哪里公文包都不离身,往来于世界各地,在大学校园,在商业协会,在妇女组织,在外交智库,对###、民主和妇女权力发表见解。我不停的进出美国和英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