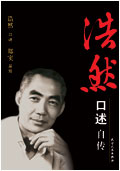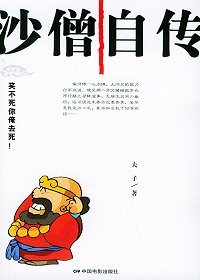贝·布托自传-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牛津有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从社会主义者、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俱乐部到划船、打猎俱乐部,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而最有名气的要数牛津辩论社。它创立于1823年,仿效英国下院的模式,一直被看作是未来政治家的训练营。由于亲眼目睹过政治生活的压力和紧张,我并不想成为政治家,我的目标是投身巴基斯坦外交事业。尽管如此,为了让父亲高兴,我还是参加了牛津辩论社。
一方面为满足父亲的愿望,另一方面我也被辩论的艺术所吸引。亚洲次大陆上还有千百万文盲,雄辩的口才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数百万人被圣雄甘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穆罕默德?阿里?真纳,还有我父亲的演讲所折服。讲故事、诵诗歌和作演讲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在牛津辩论社所得到的历练,会使我日后能在巴基斯坦数百万人民面前大胆讲演。
学了三年的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后,我第四年又选修了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研究生课程。牛津辩论社是我生命中最重要和最快乐的一个焦点。它的花园和大楼位于牛津校园的中心,楼里有地下餐馆,还有两个图书馆和一个台球室,这儿对我来说就像阿尔—穆尔塔扎的房间一样熟悉。在辩论大厅,从女权主义者作家杰曼?格里尔到工会主义者阿瑟?斯卡基尔等各色人物都给我们作过演讲,两位英国前首相斯托克顿勋爵和爱德华?希思也给我们作过演讲。而学生上台演讲都要穿上正式的服装,还要在衣服翻领上插枝康乃馨。我不得不换下牛仔裤,穿上安娜?贝林达的丝绸衣裳。用完烛光晚餐,我们便坐在一起进行激烈的舌战。
命运真的巧得很,我第一次在辩论大厅里演讲,面对格莱德斯通和麦克米伦等英国政治家的半身塑像,演讲的主题是通过宪法手段而非武力撤换一位民选的国家元首。“本院将弹劾尼克松”就是辩论社主席要求我提出的动议。
“一个人以法律和秩序为口号,参加总统竞选;然而在他当选后却为所欲为,肆意破坏法律,引起国家的全面混乱,这是一个悖论。”我展开了论述。“但是,美国的历史充满了悖论。让我给你们讲讲乔治?华盛顿和他父亲的故事。一天,小乔治的父亲发现有人砍倒了他的樱桃树,他大发脾气,要查明是谁干的。小乔治勇敢地站到父亲面前说,‘爸爸,我不能说假话,树是我砍的。’大家看,美国人的第一位总统说不了假话,而他们如今的总统却说不了真话。”
20岁的我,像个初生牛犊,自信大胆。我痛陈了这位美国总统应该被弹劾的理由:他在越南战争中违背了开战权属于国会的原则,他下令秘密轰炸柬埔寨,他为逃税而篡改票据日期,他涉嫌掩盖水门事件真相、抹去秘书的磁带企图销毁罪证。
“不要搞错了,朋友们,”我总结陈词,“这些罪责是非常严重的,尼克松总是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英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也是这样干的,结果掉了脑袋。我们建议对尼克松动动手术,虽说不如砍头那么严厉,但效果绝不会差。据说,有一次尼克松去看精神病医生,医生告诉他说,‘总统先生,你没有患妄想狂症,人们确实在恨你呢!’今天,尼克松不仅遭人恨,而且还失去了所有的信誉。由于失去人民的信任,尼克松便失去了领导国家的道德权威。这不仅仅是尼克松的不幸,更是美国的不幸。”
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3)
法律、信誉和道德,这些在西方是理所当然的民主原则,在巴基斯坦却荡然无存。弹劾尼克松的动议在牛津辩论社以345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然而在巴基斯坦,推翻我父亲的不是选票,而是枪炮。
巴基斯坦对身在牛津的我来说显得十分遥远。正如父亲预言的那样,我在牛津轻松愉快的岁月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朋友们带我到查韦尔河上撑船,到布伦海姆宫的树荫下野餐。周末,我们驾驶着黄色敞篷小汽车(父亲为我从哈佛毕业送我的礼物)去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观看莎士比亚戏剧,或者去伦敦,在新开的巴斯金—罗宾分店大吃一顿美国薄荷奶油冰淇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赛船周”中,各学院的船队在河上你追我赶,我们就去参加学院赛船场旁的花园派对,男士们头戴硬草帽,身穿运动衫,女士们头戴有沿帽,身穿长花裙。考试期间我们则一身朴素,着传统的白衬衫、黑裙子和黑色无袖长袍,连不是牛津的学生见到我们跑过也禁不住喊道:“祝你们好运”。
哈佛的外国留学生寥寥无几,我在拉德克利夫时,班上只有四名外国学生,包括一名英国姑娘,她也被当作“外国人”,我当时还感到很奇怪。而牛津却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巴基斯坦板球运动员伊姆兰?汗在这儿上学,还有个叫巴赫拉姆?德赫卡尼?塔夫蒂,他父亲是个伊朗人。巴赫拉姆常常为我们演奏钢琴,一弹就是几个小时,从吉尔伯特、沙利文和斯科特?乔普林的钢琴曲到富尔的安魂曲,无所不能。后来在1980年5月,伊朗革命后不久,他被杀害了。尽管在牛津的亚洲学生只被当作一般的外国人来看待,不会被归入哪一阶层或哪一等级,但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是这个态度。
1974年2月,我乘飞机回巴基斯坦,和家里人一起到拉合尔参加父亲召开的###峰会。几乎每个穆斯林国家的君主、总统、总理和外长都出席了,来自38个国家。当父亲呼吁与会各国承认孟加拉国后,穆吉布?拉赫曼也乘胡阿里?布迈丁总统私人飞机来参加会议。这次峰会是父亲的伟大胜利,也是巴基斯坦的伟大胜利。父亲向穆吉布伸出了橄榄枝,为和平遣返巴基斯坦战俘铺平了道路。孟加拉领导人曾威胁要对战俘进行战争审判。
当我怀着亚洲人身份的兴奋心情返回英国时,却第一次遭遇了种族歧视。
“你在英国准备住什么地方?”英国移民局的官员一边问我,一边审视着我的护照。
“牛津大学。”我礼貌地回答,“我是牛津的学生。”
“牛津大学?”他眉头一扬,以嘲讽的口气问。我压抑住愤怒,把学生证拿给他看。
“布托,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卡拉奇,巴基斯坦。”他以轻蔑的口气说,“你的治安卡呢?”
“这儿,”我说着递给他我那张最近续签的治安卡,在英国的外国人都必须携带这个证件。
“你打算如何支付你在牛津的费用呢?”他以恩赐的口气问道。我本来想说我只带了铅笔和水杯来嘲弄他,但还是忍住了。“我父母会定期向我的银行账户上汇款。”我说着给他看了银行存折。
但是这个可恶的小官员还不让我走,反复检查我的各种证件,在一个大厚本上查找我的名字,但他显然没有从中认出来。
“一个巴基斯坦人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去牛津上学?”他最后又来了一句,才把所有证件退还给我。
我十分恼火,转过身大踏步走出机场。移民局的官员如果可以这样对待总理的女儿,那么他们会怎样对待英文没有我流利,胆子没我这样大的其他巴基斯坦人呢?
早在我去牛津之前,父亲就让我当心在西方可能遭到的歧视。他做学生时就有过切身经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一名旅馆服务员拒绝给他提供房间,倒不是因为认出他是巴基斯坦人,而是因为他黑黝黝的皮肤让他看上去像个墨西哥人。
当我从牛津往家里写的信以及在家中的言谈越来越西化时,父亲又一次提醒我种族歧视的存在。我猜测他是担心我受西方的诱惑而不再想回巴基斯坦了。“西方人心底里认为,作为一个学生你不会永远呆在他们国家,”他写信给我说,“他们接受你,是因为觉得你不是移民,不是一个要依赖他们的有色人种。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到他们的伟大国家避难的又一个巴基斯坦人或者又一个亚洲人,他们的态度就会完全转变,将开始瞧不起你。他们将认为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你竟然也来同他们竞争,那不公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4)
父亲的这些担忧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我从未想过不回巴基斯坦。我的心在那里,我的传统和文化在那里,我的未来也在那里——祖国的外交事业。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我已经具备了一些外交经验。
1973年父亲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坚持要求美国取消对巴武器禁运。在白宫的正式宴会上,我坐在亨利?基辛格旁边。喝汤时,我总想着《哈佛讽刺文摘》上的一幅插图,画的是叼着雪茄的美国国务卿正躺在一块熊猫皮毯上。当时我立即把那份珍贵的刊物寄给了在巴基斯坦的妹妹和萨米娅。后来宴席上上了鱼,为了不再分神,我和基辛格闲聊起哈佛精英的优越感和其他无争议的话题。第二天晚上在另一场宴会上,基辛格拉住我父亲说:“总理先生,你的女儿比你还要咄咄逼人啊。”我当时不知所措,父亲却爽朗地笑了,他把基辛格的话当作是真心的恭维话。然而,我至今仍不确定……
1974年父亲去法国参加乔治?蓬皮杜总统的葬礼,而核能成了此行的主要议题。一年前父亲就已经同蓬皮杜达成非正式的核援助协议,法国帮助巴基斯坦建立一个核再处理工厂。他不知道蓬皮杜的继任者是否会继续这个谈判。“你认为谁将是下届总统?”父亲和朋友们在马克西姆饭店吃饭时问我。“吉斯卡尔?德斯坦。”我当时在牛津基督学院的指导老师彼得?普尔萨开设了法国政治学,根据这门课我做出了推测。很幸运我猜对了。德斯坦总统力排基辛格和美国的压力,同意信守协议。
然而,三年前在中国时,我对美国总统选举的预测却没有这么准。那一回,父亲送我和弟妹们去中国看一看共产主义国家。在对周恩来的礼节性拜会中,这位中国总理问我谁会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乔治?麦戈文。”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周恩来总理告诉我说,他得到消息是理查德?尼克松会成为总统,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猜测。我是哈佛大学坚定的反战分子,又居住在自由开明的东北部,因此除了麦戈文,我再也想不出其他人选。“你回美国后再给我写信来谈谈看法。”周恩来对我说。我照做了,但仍然坚持麦戈文会当选总统。可见作为学生的我,政治敏锐性还是不够。
尽管如此,我自己的竞选还是很成功的。1976年秋,我返回牛津,开始修一年的研究生课程,同时也开始忙于竞选牛津辩论社主席。虽然我想尽早结束学业投身外交,但父亲坚持认为,作为总理的孩子,工作之前必须练好本领,达到双倍胜任,这样才没有人说闲话。
这时弟弟米尔已经在牛津开始他的第一年学习生活了,我盼着能和他一起多呆些时日。我在牛津这一年的最大收获是担任了牛津辩论社的主席。几年来,我一直是辩论社常务委员会成员,并且担任财务员,但我第一次竞选主席时失败了。这一次我终于成功了!1976年12月,我的胜选把这个“大男孩俱乐部”搅得翻了天:10年前,辩论会的女性还被限制在演讲厅的楼上座位;直到今天,辩论社男女成员的比例仍然是7:1。我的胜选出乎每个人的预料,包括我父亲都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