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第9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金汉街召开一个私人议会。
我希望在任何其它地方看到这种议会!姨奶奶和狄克先生代表政府或反对党——这要根据情形来定,特拉德尔则借助于《恩菲尔演讲术大全》或议会演讲记录来大声驳斥他们。他靠着桌子,手指揿着书页,右臂高举过头挥舞,像皮特先生,福克斯先生,谢里登先生,伯尔克先生,卡斯特里爵士,西德茂子爵或坎宁先生①那样,十分激烈地对我姨奶奶和狄克先生的种种劣迹作有力抨击;我就坐在不远处,膝盖上放着速记本,竭尽全力来跟上他。特拉德尔在自相矛盾和语无伦次方面远远超过实际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政客。一个星期里,他提出了各种主张鼓吹各种政策,在他的桅杆上钉着各种旗号的旗子。姨奶奶看上去很像一个无动于衷的财政大臣,只偶尔在正文需要时插进一两声。“听,”或者“不!”,或者“哦”什么的,这时狄克先生(一个地地道道的乡绅)也往往同时用力发出同一信号。只是由于在这种议会生涯中,狄克先生因为总要受到那样的指责或要对那样可怕的事承担责任,他精神开始紧张起来。我相信,他开始真的害怕他确实蓄意破坏过宪法或危害过国家了。
①上述人均为18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有的还兼剧作家、演说家。
我们这种辩论常进行到时钟指示夜半时分、蜡尽灯灭之时。由于经过这么好的练习,我渐渐能跟上特拉德尔的快慢了,如果我知道哪怕一丁点我记的是什么,我也十分得意了。可是,记完后我再读我的笔记时,我觉得我写下的像是许多茶叶包装盒上的中国方块字,或是药店里那些红红绿绿的瓶子上的金色呢!
只好再重新来,别无选择。这让人很难为情,但我还是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回头重干起,又像蜗牛那样辛辛苦苦、循规蹈矩地重新在那令人厌倦的同一地域爬行;停下来认真地从各个方面来研读那艰涩的每一点划,我用了最坚决的意志使自己能无论在哪儿见到那些难以捉摸的符号都可辨认。我一直按时到事务所,也按时到博士家;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像拉车的马那样苦苦工作。
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博士院时,看到门里站着斯宾罗先生,他样子极严肃还正在自言自语。由于他的脖子生得短,加上他又总把自己衣领浆得硬梆梆的(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原因),他总叫头痛,所以我起初也以为他又在那方面不适了,不免有点吃惊。可他马上就解除了我的这种感觉。
他不用惯有的那种热情回答我的“早上好吗,却用一种很疏远的冷漠神色看我,冷冷地邀我和他一起去一家咖啡馆。那时,这家咖啡馆有一扇门直通博士院,刚好就在圣保罗教堂的小拱道内。我跟在他身后,忐忑不安,浑身发热,好像我的忧虑正在发芽出土。由于路不宽,我让他走在前面一点,这时我看出他昂着头,那神气好不傲慢,令人绝望,我担心他已察觉了我和我的朵拉的事。
就算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我没这么猜,当我跟着他走到楼上一个房间里,看到那里的默德斯通小姐时,我也会明白原因了。默德斯通小姐靠在食器柜的后面,柜架上有几个倒过来放的无脚柠檬杯,还有两个四周稀奇古怪的盒子,它们通体都是棱角或供插刀叉用的凹槽。
默德斯通小姐把她那冰冷的手指伸给我,同时僵硬地坐在那里。斯宾罗先生关上门,叫我坐下,他自己却站在火炉前的那块地毯上。
“默德斯通小姐,”斯宾罗先生说道,“请你把你提包内的东西给科波菲尔先生看看吧,”
我相信,这正是和我小时候那同一个钢口铁牙的提包,关起来时就像咬牙切齿一样。嘴像那提包一样紧闭着的默德斯通小姐把包打开,同时也把嘴略略张开,从包里拿出了我给朵拉最近写的那封充满热烈情话的信。
“我相信,这是你的笔迹吧,科波菲尔先生?”斯宾罗先生说道。
我发热了。我说“是的,先生”时,我觉得我听到的不是自己的声音。
“假如我没猜错,”斯宾罗先生说道,这时默德斯通小姐又从她的包里拿出一扎用极好看的蓝缎带捆着的信,“这也是你写的吧,科波菲尔先生?”
我怀着再畏怯不过的感觉从她手上接过那些信来,看到在顶上面写着“从来就是我最亲爱的属于我的朵拉”,“我最爱的天使”,“我永远最珍爱的”等这类字样时,我的脸刷一下红了,并低下了头。
当我机械地把信交还他时,斯宾罗先生冷冷地说道,“不必了,谢谢你!我不要夺走你的这些信。默德斯通小姐,请往下说吧!”
那个文雅的人沉思着看看地毯,很刻毒地说道:
“我应当承认,在大卫·科波菲尔这件事上,我已对斯宾罗小姐有过一些时候的怀疑了。斯宾罗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注意了他们;那时,我得到的印象是不佳的。人心的邪恶是那样——”
“小姐,”斯宾罗先生插进来说道,“请你只说事实吧。”
默德斯通小姐垂下眼帘摇摇头,好像对这不客气的打岔抗议一样,然后苦着脸儿,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说道:
“既要我只说事实,我就只好干巴巴地陈述了。也许应该讲这程序。我已说过,先生,在大卫·科波菲尔这件事上,我已经对斯宾罗小姐有过一些时候的怀疑了。我时常想找到证实这些怀疑的证据,但没有结果。所以我忍住了,不曾对斯宾罗小姐的父亲提过,”她这时严厉地看着他说道,“我知道,在这类事上,对出自良知的忠实职责之行为,通常是很难予以欣赏的。”
斯宾罗先生似乎完全被默德斯通小姐那男性化的严厉态度吓住了,便求和似地摆摆手,想让她那苛刻的神气缓和一点。
“由于家弟的婚事,我请了一个时期的假;我回到诺伍德,”默德斯通小姐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往下说道,“在斯宾罗小姐看望她的朋友米尔斯小姐回来时,我觉得斯宾罗小姐的态度比以前更有理由让我怀疑,所以我严密地监视斯宾罗小姐。”
我亲爱的天真的小朵拉,一点也没觉察到这毒龙的眼光。
“我一直找不到证据,”默德斯通小姐又说道,“直到昨天夜晚为止。我觉得斯宾罗小姐接到她的朋友米尔斯小姐的信太多了;可是米尔斯小姐是她父亲认为很好的闺友,”她又重重打击了斯宾罗先生一下,“我没有必要干涉。如果不允许我提到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邪恶,至少也可以——应该——允许我提一提误予的信任。”
斯宾罗先生歉疚地小声表示同意。
“昨晚喝过茶以后,”默德斯通小姐继续说道,“我看见那只小狗在客厅里又跳又滚又叫,咬着一个什么东西。我对斯宾罗小姐说道:‘朵拉,狗咬着什么?那是纸呀!’斯宾罗小姐马上把手伸进长袍,惊叫了一声。我拦住她说道:‘朵拉,我亲爱的,让我去办吧。’”
哦,吉普,可恨的小狗,你这可恶的小东西,原来这都是你惹的呀!
“斯宾罗小姐,”默德斯通小姐说道,“想使我心软,就用了亲吻、针线盒、小件珠宝来收买我——我当然置之不理。我朝那只狗走去时,它缩到沙发下了。我费了很大的事,才用火箸把它从那儿赶了出来。它虽然被赶了出来,却依然把信咬住不放;我冒着被它咬的危险奋力去抢那些信,它就把它咬得那么紧,哪怕我把它提起来四脚悬空,它还是不肯放。终于我把信拿到了手。读完后,我就断定斯宾罗小姐手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信;于是终于从她那儿拿到现在大卫·科波菲尔手中的那一札来。”
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一面关上提包,一面闭上她的嘴,显出不屈不挠的样子。
“你已听到默德斯通小姐的话了吧。”斯宾罗先生说道,“请问,科波菲尔先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仿佛看到我那整夜哭泣的美丽的小宝贝——仿佛看到处在无援的可怜的孤独中的她——仿佛看到她那么恳切地哀求那个铁石心肠的女人——仿佛看到她徒劳地亲吻那女人,献上那针线盒、手饰——仿佛看到她完全是因了我而忍受那些难堪和苦恼——这样想象使我那本可以多少振作点的自尊心大大受挫。恐怕有那么一两分钟我浑身发颤,虽说我想尽力掩饰。
“我只能说,”我答道,“一切都是我的过失。朵拉——”
“是斯宾罗小姐,请你这样称呼她。”她父亲很严厉地说。
“——受我的劝诱,”我吞下那比较生硬的称呼往下说道,“才答应把这事隐瞒起来,我很后悔。”
“你太不应该了,先生,”斯宾罗先生说道,一面在火炉前的地毯上走来走去,由于他的领巾和背脊梁硬僵僵的,他只好用他整个身体来代替点头以加重他的话:“你已经偷偷干了一件不合礼法的事,科波菲尔先生。我带一个上流人士到我家,不管他是19岁,29岁,或90岁,我总以信任之心以持。如果他滥用了我的信任,他就做了极不光彩的事,科波菲尔先生。”
“我也那么认为,先生,我向你保证。”我回答道,“不过,我起先一点也没想到。说真心话,斯宾罗先生,我起先一点也没想到。我这样爱斯宾罗小姐——”
“呸!胡说!”斯宾罗先生脸都红了,“请你不要当我面说你爱我的女儿,科波菲尔先生!”
“如果我不这么说,我能为我的行为辩护吗,先生?”我很谦恭地说道。
“如果那么说就能为你的行为辩护吗,先生?”斯宾罗先生突然一下在火炉前的地毯上停下说道,“你考虑过你的年纪和她的年纪吗,科波菲尔先生?你考虑过破坏我女儿和我之间应有的彼此信任会意味着什么吗?你考虑我女儿的身份、我为她的进取拟定的计划、我要留给她的遗嘱吗?你有过什么考虑吗,科波菲尔先生?”
“恐怕考虑得很少,先生,”我够恭敬地回答,感到很伤心,“可是请相信我,我已经考虑过我自己的处境。当我对你解释时,我们已经订婚了——”
“我求你,”斯宾罗先生用力击掌说道——虽然我这时非常沮丧,我也不能不发现他比我认识他以来更像个小丑了——“不要对我说什么订婚,科波菲尔先生!”
在一切其它事上都无动于衷的默德斯通小姐轻蔑地发出短短笑声。
“我向你说明我境况变化时,先生,”我不用那个不合他意思的表现方式,又重新开头说道,“这一隐秘行为——完全是我使得斯宾罗小姐这么做的,我很抱歉——已经开始了。由于我已身处那变化了的境况,我已把神经绷得紧紧的,用我一切力量,去改善这境况。我相信我一定能到时候改善它。你愿意给我时间吗——不管多久?我们两个都还这么年轻呀,先生——”
“你说得不错,”斯宾罗先生皱着眉头说道,“你们两个都很年轻。这全是胡闹。别再胡闹了。把这些信拿去,扔到火里吧。把斯宾罗小姐的信给我,也扔到火里。我们将来的交往只以博士院为限,你知道,我们可以同意不再提过去的事了。就这样吧,科波菲尔先生,你不是一个糊涂人;只有这样办才合理。”
不,我不能同意这办法。我很抱歉,但有一种东西比理性更高。爱情超越于一切尘世的权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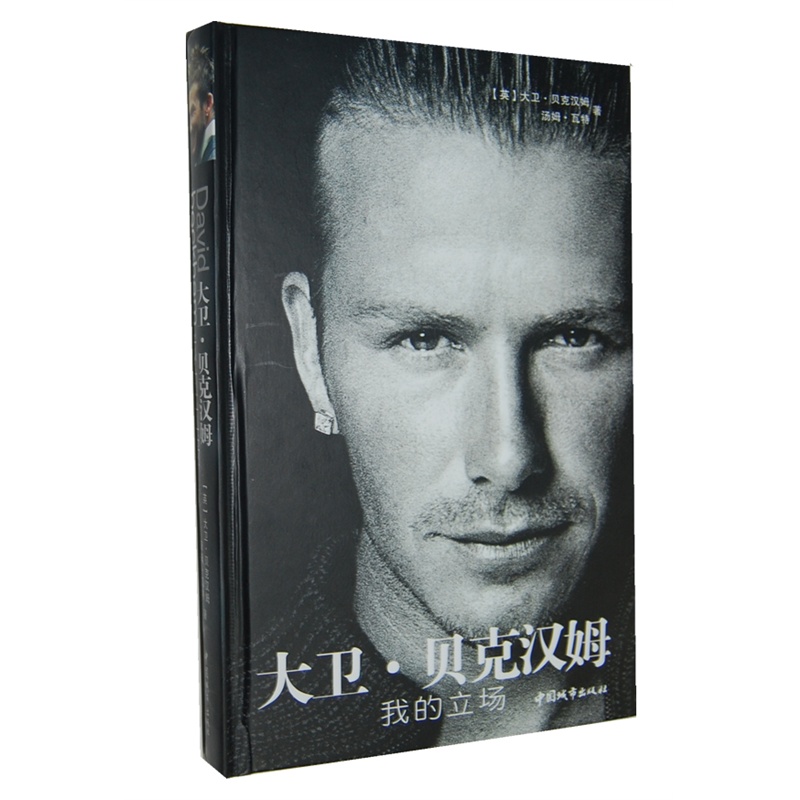
![[西里尔·科恩布拉特_孙维梓] 黑箱子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