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先生,是大卫·科波菲尔,”我说。
“别指教我。你就是布鲁克斯。”那人说,“你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就是你的名字。”
听到这话,我更仔细地端详这人。我记起了他的笑声,我知道他就是奎宁先生,以前——我毋需记起那是什么时候——我曾和默德斯通先生去罗斯托夫特看过他。
“你过得怎么样,在哪受教育,布鲁克斯?”奎宁先生道。
他已经把手放在我肩上,让我转过身来和他们一起走。我不知道回答什么好,犹豫地看了看默德斯通先生。
“现在他呆在家里,”默德斯通先生说,“他没在任何地方受教育。我不知道把他怎么办好。他是个麻烦。”
和旧日一样阴冷险恶的眼光又落在我身上停了一会;然后他皱皱眉,眼光暗下去转向别处。
“嗯!”奎宁先生说着看看我们两人——我觉得是这样——“好天气呀!”
接着谁也没说话,我在想怎么才能把肩膀从他手里挣脱然后走开,这时他说道:
“我想你是个挺机灵的家伙吧?呃,布鲁克斯?”
“嘿!他够机灵了,”默德斯通先生很不耐烦地说,“你最好让他走。他不会为麻烦了你而感谢你的。”
听到这暗示,奎宁先生放了我,我便急忙往家走。转到前面花园的门口时,我朝后看,只见默德斯通先生靠着墓场的柱门,奎宁先生在对他谈话。他俩都在我身后看着我,我觉得他们在说我什么。
那天夜里,奎宁先生宿在我们的住宅里。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我推开椅子,往屋外走去时,默德斯通先生把我叫了回来。他一脸严肃地走到另一张桌前,而他姐姐就坐在她的那张书桌边。奎宁先生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儿看窗外;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大家。
“大卫,”默德斯通先生说,“对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切实行动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世界。”
——“你就是那样的,”他姐姐补充道。
“珍·默德斯通,请让我来说。我说,大卫,对于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切实行动的世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世界。尤其对一个像具有你这种气质的青年来说如此,你这种气质需要下很多功夫矫正;除了强迫这气质去服从劳动世界的规矩,去改造它,去压碎它,再没更好的办法对付它了。”
“因为不允许倔强,”他姐姐说,“它所需要的是压碎。一定要压碎它,也一定能压碎它!”
他看了她一眼,半是反对,半是赞成,又继续说:
“我想你知道,大卫,我并不富。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知道了。你已受了相当多的教育了。教育是很花钱的;就算它不花钱而我也能供你,我仍然持这种看法:留在学校对你毫无好处。摆在你面前的是和世界斗一次,你开始得越早,就越好。”
我想我当时就认为我已经笨手笨脚地开始了;不过不管当时怎么想,我现在就这么认为的。
“你已经多次听人说起‘帐房’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帐房,先生?”我重复道。
“默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的,贩酒业的。”他答道。
我想我当时流露出犹疑,他马上说:
“你已经听人说起过‘帐房’,或那生意,或那酒窖,或那码头,或和它有关的什么。”
“我想我听人说起过那生意,先生,”我说,我记起我对他和他姐姐两人的财产的模糊了解,“不过,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不关紧要,”他答道,“那生意由奎宁先生管着。”
我向站在那儿望窗外的奎宁先生满怀敬意地看了一眼。
“奎宁先生建议说,既然雇别的孩子,那么他觉得没理由不以同样条件雇你。”
“他没有,”奎宁先生转过半边身子低沉地说,“别的前途了,默德斯通。”
默德斯通没留心他说的,做了个不耐烦,甚至是很气愤的手势,继续道:
“那些条件是,你可以挣够你的吃喝和零花。你的住处(我已安排好了)由我付钱,你的洗衣费用也由——”
“必须在我预算之内。”他姐姐说。
“你穿的也由我提供,”默德斯通先生说,“因为你一时还没法自己挣到。所以,你现在要随奎宁先生去伦敦了,大卫,去自己闯世界了。”
“简言之,你得到赡养,”他姐姐说,“千万要尽责。”
虽说我很清楚,这一宣告是为了除掉我,可我记不清当时我对此是喜还是怕。我的印象是,当时我对此是处于一种迷乱状态中,处于喜和怕之间却又并不是喜或是怕。我也没多少时间整理我思绪,因为奎宁先生第二天就要动身。
第二天,就看看我吧——戴着顶很旧的小白帽,为了我母亲在上面缠了根黑纱;穿了件黑色短外套,下着条硬梆梆的黑棉布厚裤子(默德斯通小姐认为在我向世界作战时,这裤子是护腿的最好铠甲)——看看这样装束着的我吧,我所有的财产就装在我前面的一只小箱子里,这样一个孤苦伶丁的孩子(高米芝太太会这么说),坐上载着奎宁先生的邮车去雅茅斯换乘前往伦敦的车!看到了,我们的房子和教堂怎样在远处消失,从我昔日游戏的场地上向上高耸的尖尖的塔顶又怎样再也看不到了,天上空荡荡的了!
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立生活,但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现在我已相当练达世故,几乎丧失了为任何事感到吃惊的能力了;但是我当时那么小就这么被人轻而易举地给抛弃了,就是现在也叫我多少有些吃惊呢。一个才能优异的孩子,一个具有很强的观察力的孩子,机敏、热心又纤弱,身体和精神很容易被伤害,却没有一个人表示出半点为我着想,我至今觉得不可思议。没人为我着想,而我年方十岁便成了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小苦力了。
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发店就设在河边,位于黑弗莱尔的一角。那地方已被现代的改良举措改变了,不过那批发店还是一条窄窄街道尽头的最后一所房子,而那条窄窄街道弯弯曲曲从小山上下来直达河边,街尽头有几级供人们上、下船的台阶。那房子相当破旧,但有自己的码头,涨潮时它与水相连,退潮后则与烂泥栉比,事实上它已被老鼠占据了。它那镶板房间的颜色已被一百多年——我敢这么说——的污垢和烟气改变了,他的地板和楼梯也已腐朽,在地下室里争斗的灰老鼠吱吱尖叫,充斥那里的是腐败和龌龊;这一切在我心中并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具在眼前。就像当年被奎宁先生握着我颤抖的手第一次走过这一切一样历历在目。
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和很多种人有生意来往,不过主要交易还是给一些邮船提供萄葡酒和烈性酒。现在我记不得这些船主要是去什么地方了,不过,我想它们中有一些是前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我还知道这种来往的结果之一就是有了许许多多空酒瓶,于是一些男子和男孩被雇来把那些瓶子对着阳光来检查,剔出有裂纹的再擦洗。空瓶子洗完了,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或配木塞,或封住木塞,或把这一切都就绪的瓶子装箱。所有这些活都是我干的活,也是和我一起被雇的少年们干的活。
我们——连我算在内——有三或四个。我的工作地点设在批发店的一角,奎宁先生想站在帐房凳脚上的横木上就能从写字台上的窗口里看见我。在我如此幸运地开始独立生活的第一个早上,那几个长期在此干活的少年中最年长的那个被派来指点我干活。他名叫米克·沃克尔,系着条破破烂烂的围裙,戴着顶纸帽子。他告诉我说,他父亲是个船夫,系着黑天鹅绒的头巾在伦敦市市长就职举行的赛会上竞走过①。他还告诉我,我们中为头的是另一个男孩,并告诉我这男孩的名字——这名字真是奇特怪异——叫白粉·土豆。可我发现那年轻人的教名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批发店里人们给他取的名,因为他肤色很浅很白,像粉一样。白粉的父亲是个水手,并以任消防员而名气大,从而又被一家大剧院雇来灭火;白粉家的年轻成员——我想是他的小妹妹吧——在那剧院的哑剧里扮演精灵。
①沃克尔(walker):意为步行者。
我沦落到这么一个圈子里,把这些从此与我朝夕为伴的人与我快乐童年时代的那些伙伴——不必说斯梯福兹,特拉德尔,以及其他同学了——相比较,我觉得我要成为博学多识、卓越优秀的人希望在心头已破灭了。当时的彻底绝望,因所处地位的卑贱,深信过去所学、所想、所喜爱、并引起遐想和上进心的一切正一天天、一点点离我而去,那年轻的心所受的痛苦,对这一切的深刻记忆是无法写出来的。当米克·活克尔上午离开后,我的眼泪立刻流进了洗瓶子的水里,我哽咽着,好像胸头有一道裂缝随时行将迸开一样。
帐房的钟指到十二点半,大家都准备去吃午吃了。这时,奎宁先生敲敲帐房的窗子,作手势要我进去。我进了帐房,看到那里有个大块头中年人,穿着褐色外套、黑色紧身裤和黑鞋。他的头很大,亮光光的;上面的头发决不比一个鸡蛋上的多,他把那宽宽的大脸完全转向我。他衣衫寒酸,却戴一条很打眼的硬假领。他的手杖挺帅气,上面还系了对褪色的大穗子,外套上还挂了个单片眼镜——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个饰物,因为他几乎从不用它看什么东西,就算他看也看不见什么。
“这,”奎宁先生指着我说,“就是他。”
“这,”那位陌生人说,他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种屈就下交的语调,还有那种从事上流职业的无法形容的神态,“就是科波菲尔少爷了。我希望你贵体无恙,先生。”
我说我很好,也希望他很好。我当时十分不安,上天知道;但我不愿在那时诉苦,所以我说我很好,并希望他也很好。
“谢天谢地,”那陌生人说,“我很好。我收到默德斯通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我把我那现在未住人的后一部房屋当作——简言之,出租——简言之,”那陌生人笑了笑,迸发出勇气说,“当作卧室——租给我此刻有幸结识的年轻创业人——”那陌生人挥挥手,把下巴搁进那硬衬领里。
“这是米考伯先生,”奎宁先生对我说。
“嗯哼!”陌生人说,“这是我的姓氏。”
“密考伯先生,”奎宁先生说,“和默德斯通先生相识。他给我们拉生意,只要他拉到了客户,我们就付他佣金,他收到了默德斯通先生请他替你安排住处的信,并愿意收你当他的房客。”
“我的地址是,”米考伯先生说,“都会路,温泽巷。我——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度迸发出勇气说,但还是用那种上流人的神态——“我就住在那里。”
我向他鞠了一躬。
“依我之见,”米考伯先生说,“你在这大都市的见闻尚不甚广泛,要穿过这现代巴比伦的迷宫时都会路——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次迸发出勇气说,“你可能会迷失方向——我很高兴今晚来这里,用最近的路线的知识将你武装起来。”
我真心真意地谢了他。因为他竟愿意费神,真是太热诚了。
“几点,”米考伯先生说,“我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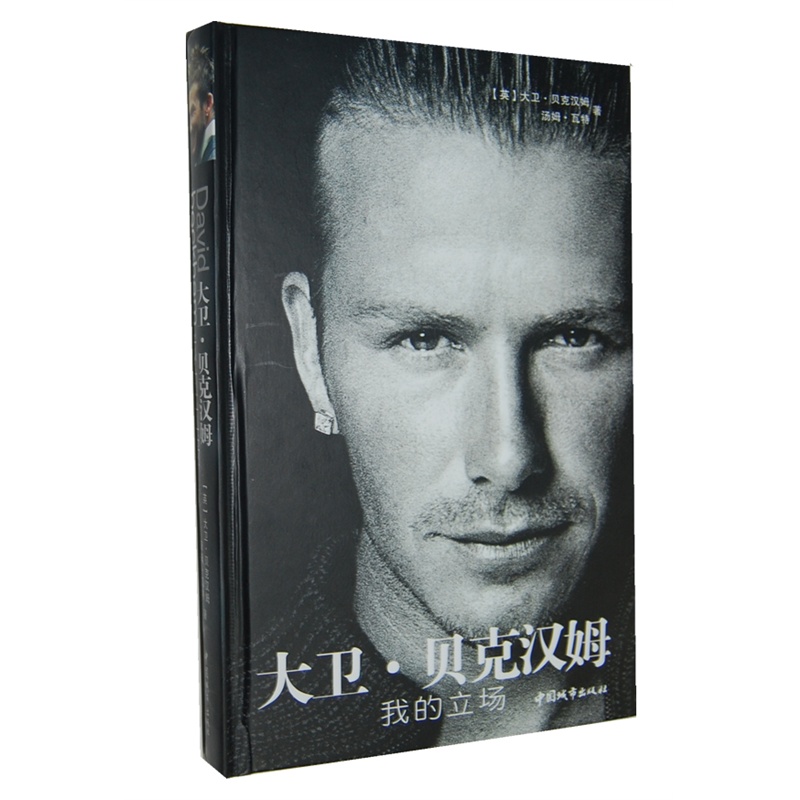
![[西里尔·科恩布拉特_孙维梓] 黑箱子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