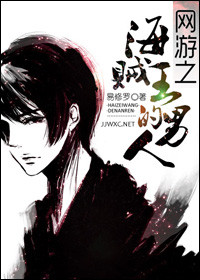走下坡路的男人-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次肺炎像魔咒一样笼罩着我。后来,我常常要犯支气管炎,常常要到40哩外的福特恩镇去住院。看看身边的氧气瓶,还有插到我瘦骨嶙峋的身上的巨大针头,在家里走不成路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我一边咳嗽抽搐,一边翻翻购物广告、看看漫画,看到脑子累得实在不愿再看才作罢。吃什么东西由我随意定,热巧克力、全麦薄饼,配上粘粘的甜面包圈,一个一个不停地吃,直吃到再也塞不进去、肚子难受地上下翻动才停嘴。
病情有点好转的时候,妈妈把我抱到起居室的长沙发里,她和收音机一起给我做伴。电热水壶跟在身后,在屋子一角很快烧开了水,把蒸汽放在空中,让我的肺保持潮湿柔润。那时,病情既不好也不坏,算是病得最舒服的日子。即便一直呆在家里,也没觉得特别无聊,没觉得无法忍受。呼吸的时候,胸膛不觉得特别难受。松松的吸痰袋吊在胸前,说明还不用担心要回学校。我挺享受雾气弥漫的赤道型天气,享受妈妈的溺爱,好像自己是一只罕见的热带鸵鸟。
那时,家里还没电视。一生病,我的兴趣和注意力便都集中在周围的事物上。我想把周围所有东西都研究个透。我比一般孩子早知道,要是你安安静静、不吵不闹,别像其他孩子一样总想让人注意自己,大人便会觉得你跟家具一样,比如就像个靠垫,既不重要、也没头脑。跟妈妈一起,我得以见识成人世界中常见的困苦与流言。
六岁的时候,我还不懂“流产”是什么意思,但却知道伊塔·汤普森已经有过一次。现在,她家的下水道堵住了。透过蒸气弥散的起居室窗户,我能看到老处女库茨纳斯卡在挂洗好的衣服。看到她,我便能证实说她不愿穿*的传言。她弯下腰,在洗衣篮里摸索,我能瞅见她硕大的白屁股,在春天孱弱的阳光下发着光。
我还知道(怎么知道的记不太清了),诺玛·拉格斯和卖酒小店有染。每天早上10点50分,她总会经过我家窗外。早上11点,卖酒小店开门营业,她会站在门口。11点15分,她会摇摇晃晃地回家,一手拿着一品脱冰淇淋,一手拎着一个棕色纸袋,里面藏着掺了烈酒的红酒。她脸上原本有红色的色斑,此时,却带着一层羞愧的红晕。
“可怜的姑娘!”只要看到诺玛从窗前经过,看到她破旧的外套和脚下一双男人的大鞋子,妈妈便总要这么感慨。她们是高中同学,诺玛曾是班里的尖子生,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过言。她那时很用功,也很乖巧,现在也一样。酒不是她的,她只是爱吃冰淇淋,酒是她丈夫的。她丈夫是兽医,从战场上回来,跛得很厉害。
总是仔细观察大人让我挺早熟的,或者说,有时我会很明显的“与众不同”,要么就是“这孩子有点怪怪的”。1959年7月的时候,我搬去和奶奶住,她一眼便看出来了。当然,她开始只说了些表面的事,比如说我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她还有点尖酸地说,我有个坏习惯,总是用眼睛盯着她,还说我是个长了一双大耳朵的“小茶壶”,她从没见过这么爱偷听大人话的孩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看客(2)
我之所以要住到奶奶家,是因为那年三月,妈妈的肺病加剧了。大伙都觉得挺意外。熟人都觉得她的病不会严重到哪儿去,其实并非如此。政府出资的X光体检发现,妈妈有肺结核。妈妈脸色灰白、神情忧郁地收拾好东西,准备住到外地的疗养院。
到学年快结束的将近一个月时间,爸爸一个人照看家,还有我。他身材瘦高,性格忧郁,像根耸拉着叶子的野草。爸爸结婚很晚,却很适应家庭生活。我不太喜欢他。
妈妈生病不在家,爸爸心怀抑郁。他拿根破铅笔给她写很长的信,字迹潦草,难于辨认。后来,我不在家了,他每周都去看妈妈。他心肠太软,多愁善感,谁摘下帽子,谁家的猫死了,他都会眼泪汪汪的。他跟他妈、就是我奶奶布拉德利不太一样,他没她那么果断,也没那么硬的心肠。
他那么多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这个老太太挺坚决,没把携带责任意识与实干精神的细胞遗传给笨拙的子女。她的孩子一个个生意失败、婚姻破裂,一次次经受失败与灾难,即便往好的说,也总是一次次的战略退却。我父亲算是例外,其他孩子的事业与生活都不稳定。
妈妈从他们身上,也没看到什么可资补救的希望。他们太爱喝酒,说话吵闹,养的孩子也没什么教养,像些堕落的魔鬼,毫无礼数。妈妈总有无数的例子教育我,怕我以后也成那样的人。“你吃东西像猪一样,”她会这么说,“跟那个表弟埃尔文一模一样”,或者跟爸爸说,“你没好好管教他,他会变得跟莫里的小儿子一样说话没礼貌。”
布拉德利奶奶身处在不幸与悲惨的家族中心,如磐石一般。各种问题摊在她门口。我堂妹克丽丝达16岁,肚子被人搞大,不知道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也没法指个罪犯逃逸的方向出来,让大伙声讨。她被送到奶奶家,生下了孩子。厄尔尼叔叔在奶奶家的农场戒了酒。埃德叔叔也跑到奶奶家躲了好几个月,为的是躲避几个买了他预制的、可以自行组装的农用飞机的人。
家庭传统让我一定也得被寄养在奶奶家。当爸爸再也承受不了家庭的责任,而我又大声抱怨晚饭总吃煎蛋三明治时,他甩下脏盘子里变硬卷得奇形怪状的煎肉,跨过灰尘团随风滚动的地板,当即开车把我送到150哩外的农场。
一旦爸爸坐在方向盘后面,他便成了冒险人物。他对任何长途行程总要严阵以待,觉得公路如同丝带般狭窄,风险密布。在他眼中,旅途中的危险无处不在。他双手片刻不离方向盘,眼睛始终盯着公路,还让我这样一个长期受肺病折磨的人,给他不断点烟,小心地把烟放到他干燥的嘴唇之间。妈妈要是看到了,非杀了他。
“你会喜欢呆在奶奶家的。”他不断地说,却没什么说服力,“农场里的夏天,你会真正觉得自己像个男孩了。体力活能让你结实,也有好玩的。现在你还不知道,会有你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让我当个孩子,我都愿意。你会喜欢那儿的,那儿有鸡,啥都有。”
他的话也不全是假的,那儿的确有鸡。但爸爸的那个“啥都有”——就像他话中极力想表达的那么包罗万象、那么引人入胜、那么乐趣无限——其实啥都没有。没有我心中的小马驹、小狗什么的。那儿只有鸡。
奶奶一辈子都在农场过活,最后也死在农场,却并不怎么在意农场,起码对多养点家畜没有兴趣。她养鸡是为了取蛋。她还承认,秋天要杀鸡的时候,她总是情绪很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看客(3)
她养的鸡叽叽喳喳、骨瘦如柴,整天在院子前面的泥地里打滚,不是把鸡蛋藏起来,就是像躲豹子一样飞跑,傻不啦叽的脑袋上,长着光亮无神的眼睛,抓到逃命的壁虎以后,便一脚踩住、几下子嘬死。这些鸡里面,只有一只名叫斯坦利的公鸡,我还觉得有点可怜。它浑身脏兮兮的,腿上绑了带子,身后拽着绳子,不能到处跑。斯坦利囚徒一样可怜巴巴的叫声,让人心碎。母鸡在垃圾堆里翻吃的东西,斯坦利会贪婪地盯着,鸡冠绝望地倒向一边。奶奶把它绑起来,不许它跟母鸡*,蛋黄里便不会有血块。我对吃的东西很讲究,所以赞成她的做法,但也会为斯坦利感到有点内疚。
布拉德利家的农庄,也是爸爸嘴里那个什么都有的地方,实在不怎么样。两层的房子,虽然硕大坚固,也该重新粉刷、加固房顶了。厨房顶上的油毡有道裂痕,直通地板。纱门上也有一道口子,缝补过,用打过蜡的线封实了。院子里野草丛生,有大腿高,母鸡会躲在下面乘凉。屋子北面,防风用的云杉得跟蓟草抢水,都快干死了。长青树都不长青了,手随便一碰,干枯的针便会从枝上掉下来。
院子后面是座废弃的谷仓,旁边是小山一样的两座粪堆。我还记得,每场温暖的透雨过后,那儿便爬满了小蘑菇。院子里满是垃圾,旧汽车、烂轮胎、坍塌的棚屋,只有粪堆还算有用。谷仓业已破败,雨水、冰雹、干燥和热风把木板上的油漆剥落下来,屋顶也坍陷了,像一匹疲惫老马的背。对一个小男孩来说,夏天的谷仓危机四伏。空气呆滞,黑乎乎的,燥热湿重。一有脚步声,空食槽里面老鼠便吱吱尖叫,四处乱窜,在房梁上拉屎、把房梁都染白了的麻雀,也惊飞起来,啾啾的叫声像鬼哭一般。
1959年的时候,奶奶69岁,她应该生于“快活的十年,” 可快活的时代却没在她的性格发展上留下印记。她身材健硕,差不多6英尺高,能背起180磅的重物,不用猜她肯定是反对女人束腰的。她弯下腰,手掌能毫不费力地触到地面,还能把一袋80磅重的鸡饲料扛上肩头。她不把当地观念放在眼里,头发染成了红褐色。不戴顶帽子、不把浑身上下甚至牙齿收拾利落,她是不会去镇上玩纸牌的。奶奶喜欢各种不同的纸牌玩法。她觉得不喜欢玩牌的人,肯定是智力发育有问题。
奶奶嘴里总叼根点着的纸烟。她一天能抽60根。为省钱,奶奶把烟卷得很细,像织毛衣的针一样。夹在她肿胀的手指间,这些纤细精致的烟卷好像没有似的。
除此之外,她说话也简洁直率。爸爸的栗色轿车刚从院子开出,我们还在院前台阶上向他挥手道别,她便让我知道了。
“我们先把事情说在前面,”她跟我说,眼睛没离开正驶上公路的车子,“话我从不说两遍。要是你跟这儿的人一样,就会像个他妈的印第安人一样野。我的孙子孙女都不听话。你要长点脑子。我从不聊天扯淡,不听别人吹牛,也不瞎吹。你爸爸不乖的时候,我拿皮带抽他。我也肯定会抽你,明白吗?”
“明白。”我心里一沉。爸爸的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左右摇摆,消失在路的尽头。
“这些可恶的蚊子要把我活活吃了。”她拍着胳膊,“我进屋了。”
我跟在她身后。她穿双破球鞋,鞋带都没了。房里昏暗,半明半亮的光在每个房间都会改变形状。客厅拉着百叶窗,散发出酒窖般的潮气。幽暗的空中,有苍蝇在翻筋斗。还有些苍蝇拿自己子弹模样的身体“啪啪啪”地撞向窗格。 。 想看书来
看客(4)
奶奶走到厨房,把壶放到炉子上,烧水喝茶。她点了一根火柴棒粗细的烟卷,透过蓝色的烟雾,问我饿不饿。
“我身边的人一般都不抽烟。”我跟她说,“我的肺不好。爸爸为这个,从不在家里抽烟。”
“这样啊?”她温和地说。她嘬着烟卷,脸颊深陷。我脑子里有个意象,似乎看到了她以后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你不太会喜欢这里,”她说,“我整天都抽。”
我咳嗽几下,没什么效果,没人在乎。她不像妈妈那样重视我的咳嗽。
“我妈妈的肺也不太好。”我说,“她现在在一家肺结核疗养院。”
“听说了。”奶奶说道,起身去拿响起哨声的水壶。“噢,稍微休息一阵,她很快就能好的。肺结核不像过去那么厉害,有了那么多新药。”她想了想,“不过,你爸守着她这个病殃殃的,还会没完没了。在这种事上,梅波尔是个没用的笨蛋。”
我差点从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