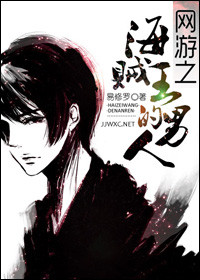走下坡路的男人-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他没有,而是睡着了。
哈克丝太太躲在屋檐下等雨势退去。雨气势汹汹、淋漓不净地下了一个小时,然后才开始减弱成无精打采的毛毛细雨。雨小了之后,她小心翼翼地拣路穿过满是水洼的花园去拿锄头。她用锄头敲碎地下室的一扇窗子,有板有眼地清除干净窗框上的玻璃,然后把屁股坐在上面,喘着气,扭动着身子钻进窗洞。她闭上眼睛,心想自己要是摔坏了就拿老家伙的脑袋来算帐,然后让自己跳了下去。她单腿着地,腿一弯,一头撞在煤气锅炉上。这锅炉震得这幢房子里所有的热气阀门和管道都发出沉闷、嘈杂的响声。她从地上爬起来,没有受伤。但尊严损了,权威伤了,她开始慢慢地穿过杂乱无章的地下室,朝楼梯走去。
老人猛地一惊,醒了。有个声音打断了他的酣梦。那是个很愉悦、很快活的梦。那头跳舞的熊在为他表演,没有谁强迫,是自愿的。那是一出完美、优雅的舞蹈,没有一丝玷污了人类舞蹈的那种浮华的矫饰和刻意的专注。熊一边跳着,一边好像在长大,仿佛是受那清纯的音乐的哺乳。它越长越大,但迪特尔带着一种异常平静的感觉看着这一切,没有丝毫恐惧。
太阳在它肉桂色的软毛上闪耀,把它的毛皮打磨成闪闪发亮的红色。等到音乐停止,那熊大张双臂,摆出一副友好、欢迎的姿势。它的嘴巴张开,好像要开口说话。这正是迪特尔一直期待的,那头熊将要向他坦露真相,将要证明在那层粗毛厚皮下面掩藏着的是惟有他才认得出的真相。
可这时,有什么东西打断了这个梦。
他被弄糊涂了。他这是在哪儿?他伸出手,触摸到一种平滑、坚韧、扯不掉推不开的东西。他吃惊地哼了一声。这不对。他的思绪在来回游走,慢慢地,很容易地从梦境来到了这痛楚、心烦的现实。
他试图站起来。他颤巍巍地起身,身子摇晃不定,感到地板在移动,然后又倒下,头撞在衣柜上,嘴里满是暖暖的、咸咸的东西。他能听见房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接着那声音消失在自己血管里澎湃的声音当中。在他的眼睑、耳朵、脖子和指尖,血脉在微弱地跳动。
他设法挣扎着站起来,想要在从身边流过的激浪般轰鸣的阴影中踩出一条路来,走到门厅去。
这时,在模糊的光线里,他看见了一个形状,在耐心地等待着。是那头熊。
“是熊吗?”他问道,拖着腿朝前走去。
那熊说了些他听不懂的话。它在等待。
迪特尔抬起双臂,为了那期待已久的拥抱,那将把他搂进芬芳、亮丽熊毛当中的拥抱。可奇怪的是,他的一只胳膊抬不起来,而是像块抹布,软软地垂着。老人感到自己的一侧面颊被什么猛击了一下,令人麻木的一击。他的左眼皮像百叶窗那样耷拉了下来。他想说话,但舌头感觉发肿,只能在牙齿上无声地乱碰。他觉得自己在瘫倒,但那头熊伸出双臂,把他拥进自己最最向往的温暖怀抱。
就这样,迪特尔·贝斯基死于中风。他是慢慢地、慢慢地,像一片树叶,倒进哈克丝太太等待着的怀抱里的。
赵伐 译
走下坡路的男人(1)
走下坡路的男人
六点半,妻子下班回来。她的钥匙在锁里嚓啦嚓啦响,我在刮胡子。搬进来以后,小偷已经两次光顾过这栋楼,所以我总紧锁房门,不想有什么意外。我的警惕让她有点恼火,她总希望夫妻两人能以开放的心态共同面对生活,但紧锁的房门恰恰证明,我没能忠于她的想法。我知道她肯定不高兴了,她的鞋跟在没铺地毯的门厅里哒哒作响,清脆嘹亮。我锁上浴室门,把她挡在外面。
这么做是因为浴室里的情形、还有我的模样,只会让她更不高兴。刚抽完的烟头在盥洗台台沿上留下了一点扎眼的烟渍,弹下的烟灰积在洗脸盆里,一杯没喝完的苏格兰威士忌放在马桶水箱上。为迎接那个实在不想去的新年聚会,我花了一下午用威士忌给自己打气。都说酒精是一种优质的社交润滑剂,要真是这样,我已经尽力了。但不知为什么,仍然觉得不管用。
妻子笃笃地敲门了,“埃德,你在里面吗?”
“还能在哪儿?”我答道,赶紧在脸颊上的肥皂沫上一道道刮起来。
“该死,埃德,”她生气地说,“我跟你说过,跟你说过的,请在我回家之前用完洗手间。我要为晚会准备,我跟海伦说过会八点到。”
“我没留神已经这么晚了。”我的辩解很苍白。我能想象她在门外摆出的姿势。她做社会工作,每天都要和我这种不负责任的人打交道。现在,她胳膊交叉抱在胸前,脑袋微微偏向一边,头发像盔甲般闪闪发亮,嘴巴撅得像个拉链钱包。她双腿叉开,稳稳戳在那儿,像是在说她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
“埃德,你要在里面呆多久?”
我听得懂这种语气。话中有话,总是质疑的口吻,总在暗示说我悲惨的性格缺陷是能够依靠努力来弥补的。那么,干嘛还不努力呢?
“五分钟!”我欢快地叫道。
维多莉亚走开了,鞋跟轻快地踏过硬木地板。
我的思绪转向晚会,然后自然地转到公务员身上。维多莉亚的朋友几乎全是同事。公务员让我想到中国的古代官僚,想起亚洲人,想到蒙古人。我小心刮去脸上的泡沫,留了一点修面霜,扮成傅满洲 的样子。干得漂亮,我眯起眼睛。
“镜子、镜子,墙上的镜子,”我低声问,“谁是世上最可怕的人?”
我压低声音,从喉咙深处阴森森地答道,“你,成吉思汗·埃德,恐怖之王!你,用敌人的头骨修筑碑阁!你,在敌人的尸体上开怀畅饮!”我想象自己驾驭一匹鬃毛蓬乱的蒙古马,驰骋沙场、横扫中亚,一双凤眼横眉冷对脚下俯首顺从的富饶城市。
维多莉亚回到浴室门口,“埃德!”
“什么事,亲爱的?”我温顺地应道。
“埃德,给我做个解释!”她说道。
“没问题,棒棒糖!”我答道,我这么回答是让她确信我已经意识到了危险,接下来的是场公平的斗争,她不用担心觉得自己是在搞突袭。
“别酸了,你不一定非得回答!”
我倒掉苏格兰威士忌,把杯子放到水龙头下洗洗,插上一支牙刷,弄得像个普通杯子。烟头弹进马桶,烟渍用拇指擦掉。“我道歉!”我边说边疯狂地在镜柜里找漱口水,好去掉嘴里的酒味。
“埃德,你整天没事做,一点儿事都没,干嘛不在我回家之前收拾好呢?”
我漱了漱口,看到自己满脸白色的傅满洲面孔,赶紧动手刮掉。“呃,亲爱的,是这样,”我说,“你知道我多能出汗,而且这些小场合也让我紧张,所以我得把时间掐好,这我得承认。不过,到那些场合总不能汗津津的,我想一会儿到场的时候,身上的香体剂该是最香才好。你肯定明白……”
走下坡路的男人(2)
“闭嘴,出来!”维多莉亚不耐烦地说。
最后,匆匆检视一遍浴室,我打开门,向她展现我最拿手的笑容,就是“我乃没用的傻瓜、犯不着跟我一般见识”的笑容。失了业,手上有大把时间,我总对着镜子练习笑容。每种情况我都准备了一种笑容,手头这个是以往练习成果的忠实再现,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有一天出去散步,刚看见一条黑颜色、大块头的拉布拉多猎狗在人家门口拉屎,我俩马上便心心相映了。它龇牙咧嘴地冲我笑,身子还卖力地抖着。它的笑容中,既包含身体排泄之后的*,又包含调皮捣蛋之后的满足,还包含行为不端之后的羞臊,绝对合适我目前的处境。
“非常干净,一尘不染。”我郑重其事地说道。
“嫁给一个未成年人真没劲。”维多莉亚说着从我身边挤进浴室。“给我倒杯喝的,我渴了。”
我赶忙服从。回来时,恰好看见妻子悦目的臀部沉入洗澡水中。浴缸热气升腾,水汽缭绕。她向后躺下,胸部下沉,雪白而精巧的脚趾玩着水龙头。
“上帝啊!”她呢喃道,沉醉在融融暖意里。
我坐在马桶盖上,把玩起透明的圆杯,晃悠里面的琥珀色液体。我把杯子出其不意地递给她,开局一般地问道,“霍华德还好吗?”
妻子没有畏缩,却惬意地舒了口气,沉浸在浓浓的热气里。我觉得,这一举动就是所谓的铁石心肠。我从她脸上读到的,是一个经验老到、乐此不疲的奸妇的典型神情。这段时间,我一直怀疑奸夫就是霍华德,那个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心理学家,在省社会服务处工作。妻子总是工作到很晚,有几次我捏着嗓子打电话到她办公室,假装是个气头上的救济对象,总是霍华德接的电话。社交场合见面的时候,霍华德总是遮掩不住对我的蔑视,肯定是因为我是个蒙在鼓里的活王八。
“霍华德?哦,他挺好。”维多莉亚淡淡地答道,啜着饮料。她的身体在水里显得又细又长。有那么一会儿,我真觉得说她像尊雕像也没错。
“我喜欢霍华德。”我说。“哪天晚上我们该请他过来吃饭。”
妻子笑了,“霍华德不喜欢你。”
“哦?”我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你老缠着他给你诊断,他又不傻,你知道的。他知道你在背后笑话他。你这人太容易看穿了,埃德。你不喜欢谁就贬低谁的工作,你这么干我都看过一千次了。”
“我拒绝回答含沙射影的话。”我说道。
妻子有点不安,开始在浴缸里拍水。她不能太护着霍华德。
“他这人不差,”她说,“你说的也对,他有点呆板。但是,有时候呆板比完全不负责任来得强。倒是你,哪怕别人的行为只算得上一点点的理智,总要尽力去贬低人家。”
我知道,妻子正把话头引到找工作上面,她一般有两种路数,一是提起过去,说过去是一串无可挽回的灾难,二是提起未来。大体上,我觉得提到过去更安全,至少我觉得是。虽然她知道我骗了她,没说上次为什么被炒,但六个月过去了,她还没从我这儿挖到真相。
老实说,我被请出门是因为“习惯性不合作”。我曾找到一份辅导成人进修方面的工作,但我一辈子都搞不懂那些术语,所以总在工作中给人留下很差的印象。大伙都在说“终端学习者”、“生活技能”,把我搞得六神无主。我刚搞懂一个词,便有人说这词的言外之意有问题,接着便发明出一个新的“价值中立的术语”。那地方是他妈的疯人院,我也只能跟着扮疯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走下坡路的男人(3)
不过,我得承认,这工作有一点让我喜欢。办公室经常没人,他们都到社区“体察需求”去了,我可以接电话。对每个打电话的人,我都轻快地问候一声“这里是知识学堂,我是万事通!”。孩子气,我承认,但很好玩。可惜,没等遇到一位真实生动、有血有肉的终端学习者,我就被解雇了。很显然,外面社区里有成千上万这种人,都是麻烦。有一次,开会商讨如何对付这些人的时候,我用了一点五角大楼的行话,是从“晚间新闻”里偶然听到的。我的建议是如果逮住一个这样的人,应该用“极端手段终结”他。
“顺便问问,”妻子假装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