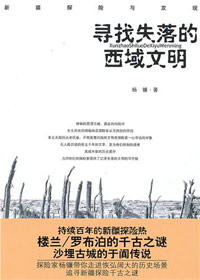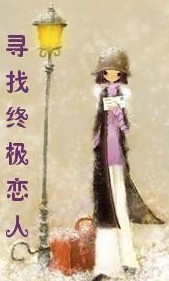寻找北大-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填空,竟有很多人答不上来。但小钱先生教我们的时候仍不改其旧,还对我们说,好的作品,要多读,最好能背下来,而且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记忆力还好。又告诉我们,当年他在浙江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对他说,一个人20岁以前能背下来的东西,基本上这辈子都不会忘。后面基本上就很难有如此好的记忆力了。我掐指一算,只剩三个月了,很是有些悲切,于小钱老师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的确,对于学习古代文学,多读多记多背,总是没有坏处的。张健老师后来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也坚持让我们多背,说现在的教育让大家不要死记硬背,这不对,小时候趁着记忆力好,就应该多“死记硬背”点东西下来,考试出了整整一面的背诵题,结果我答得惨不忍睹。这与小钱先生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
记得那个学期期末考试之前,小钱先生安排了答疑。当时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大约都是抱着能套点什么题出来的目的去的,去了就问,老师,这次考试考什么?不考什么?小钱先生含糊其辞地应付了几句,他们也不好再问什么,就在那儿坐着,一言不发。只有我跟小钱先生扯些与考试不相关的事情。小钱先生突然问,大家有把某个作家的集子完整地读过一遍吗?我说我读过陶渊明的集子。小钱先生又问,完整地读下来了吗?我说是的。小钱先生面露微笑,啪地一拍桌子说,好啊,这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虽然我这次考的是杜甫……我当时没缓过劲儿来,回到宿舍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你啊,拐着弯地就把考题套出来了。我一想。哦,好像是这么回事。结果期末真的考了一个与杜甫相关的大题。但我答得并不好,枉费了那日小钱先生的夸奖,至今仍觉得有些惭愧。
孔庆东
吴晓东先生曾经在课堂上说过,他当年刚进北大中文系的时候,就有一位师兄在那栋宿舍楼上窜下跳、以“教唆”为主要任务,这个人就是孔庆东。正如吴晓东先生所言,老孔在学生时代就是个活跃分子,当了老师更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关于老孔的事迹可谓铺天盖地,如果以后为中文系的老师们编一部《世说》,老孔肯定要占据相当大的篇幅。新出的一本《北大文学讲堂》里面就有老孔的一篇讲稿,基本是实录,老孔很多幽默的言论被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了,那次课我是听了的,现在看到这个讲稿仍觉得非常有趣。但今天且不说老孔的幽默,且说说老孔严肃的一面。
第一次接触老孔的文章还是高二的时候,抱着一本《47楼207》笑得前仰后合,后来老孔又写了不少书,但我觉得都不如那本《47楼207》。从那时候起就觉得老孔是个很好玩的人。后来老孔总说自己不幽默,又说自己的“满纸荒唐言”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我在一次课后跑上去问,您的《47楼207》写得那么有趣,辛酸在何处呢?老孔很沉重地对我说,你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北大和现在的北大更是不一样的。我突然发现老孔确实是个严肃的人。
我进中文系以后好像一直没看见老孔开过专业课,猜想大约是老孔太有名了,专业课课堂都要挤爆,肯定影响教学质量。老孔已经连开了四五个学期的通选课,从鲁迅讲到金庸讲到老舍讲到中国现代戏剧,面向全校本科生尤其是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讲得十分通俗易懂,也坚持了他写文章的一贯幽默的风格,课堂一直很火爆。有一次我发邮件跟他说,您课堂里恐怕是看热闹的人居多吧。他很严肃地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确实,看热闹的人是多数,但是真正的人才往往是从看热闹的人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既要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也要照顾看热闹的俗众,不能蔑视和抛弃他们。我时常听到一种对于老孔的批评,说他上课只讲笑话不讲学问,我觉得这大约是没有听懂老孔的课,我去听过,我觉得不仅仅有热闹可看,也还是颇有门道可听的。至于老孔的这种讲法,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也不宜妄加否定吧。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陈恒舒:先生(6)
老孔有时候看起来很“愤”。讲现代文学,跟当下的状况已经算是拉开一点距离了。但他总是坚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动辄把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某人某事拉出来嬉笑怒骂一番。用他自己的话说,乾嘉诸老也未必不关心现实,只是我们现在把他们解释成“纯学者”而已,不关心现实,什么学问都是做不大的。当然,老孔并不是个一般的“愤青”,他号称要坚持“韧的战斗,不求胜利,只求好玩,在‘韧’中体会战斗的快感。这样战斗,或者会更加持久,也更加不怕失败。”老孔写了那么多文章,嬉笑怒骂,或许正是他所谓“韧的战斗”吧。所以老孔的“愤”,我宁愿把它理解成一种强烈的现实感,记得第一次听老孔的课,他挥舞着手臂对我们大呼:“你们现在如果还在为将来的衣食考虑,这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你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我想,这也会是一句激励我一生的话。
李家浩
我在大三上学期选修了李家浩先生的“《说文解字》概论”。第一周上课之前,我去得早,趴在第一排睡觉,突然听见一个炸雷般的声音,我噌的一下就从桌子上窜起来了,当时没听清说的是什么,后来回味了一下,大约是“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李先生每次上课几乎都是如此,闷着头不声不响地进来,不声不响地拿出讲稿,一点预备动作都没有,直接把音量开到最大。这样倒也好,上课听着这么大嗓门的讲授,无论如何是不会打瞌睡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李先生是湖北人,口音极重,南方人听着还好,北方的同学头几次课根本听不懂。记得第一次课课间休息时,一位北京的同学上去跟李先生说,您的口音我实在不大适应,能看一下您的讲稿么?李先生笑呵呵地把讲稿递过去,说,不好意思,我的字比较潦草。那位北京同学翻了两页,又还了回去,说,我还是听您讲吧。
李先生自己的讲稿写得潦草,但写板书绝对是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正如传说中他治学的态度一样严谨。尤其是一些近似图画的古文、籀文和小篆字形,他都要照了自己的讲稿画了又画,改了又改,半点也不马虎。每讲一个例子,必旁征博引诸家之说,写满满一黑板,最后参以己见,有根有据,谁要是有这门课完整的笔记,当是一份极好的学术范例。可惜我当时太懒,很多繁琐的东西实在不愿动笔去记,现在想想,实在是后悔死了。
李先生在学术上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据说有一次给一个本科生指导毕业论文,很多先生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都是很宏观地给一些意见,李老师却批改得极为细致,让那个学生七易其稿,眼看第二天就可以交定稿了,那学生才松了一口气,晚上突然接到李先生一个电话:“我刚刚又发现一则新材料,你明天过来,我们把它加进去……”我想这位师兄当时肯定要崩溃了,但能得到这样一位老师如此悉心的指点,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幸福的事。
李先生有时候也很“愤”,记得有一次他瞪大了眼睛在课堂上拍着讲桌大吼:“做老师的怎么可以敲学生竹杠呢!”至于什么缘由,全然不记得了,仿佛当时是很突兀地就冒出这么一句。李先生还很忿忿不平地说过他在图书馆的一次经历。他说自己当初给朱德熙先生当助教的时候,到图书馆善本室去查一条重要材料,去之前怕会碰钉子,还特意拿了副校长的批条。结果却遭到一个管理员的无端阻挠,盘问了一大堆,最后很不情愿地答应了,末了还问了一句:“你不查不行吗?”李先生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李先生自己也笑了,笑得十分无奈。“我再不敢去图书馆了,尤其是善本室。”他会对他的每一届学生讲这句话,差不多讲了该有一二十年了吧,还是那么“愤”——其实北大的善本室大约已经不是这种情形了,葛兆光先生说他那会儿可以把线装书借回宿舍去看,我上个学期去那儿,竟也借阅到了清代的抄本。记得几个月前看过一篇漆永祥先生的文章——《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写他在苏州图书馆的遭遇,其实很李先生很像,也是求书一观而不得,甚至遭到工作人员的百般奚落。文章写得义愤填膺,后来此事被称作“苏图事件”,还颇引起一阵学术界的轩然大波。漆先生最终也没能看到他想看的书,想必至今乃至将来的很多年内也会为这件事而“愤”。不过从这种“愤”里,我确实看到了真正的学者们对于学术的挚爱。
。 想看书来
陈恒舒:先生(7)
上次看见李先生还是暑假去帮忙整理古文字资料室的时候。当时那个资料室长期没有人管理,杂物乱堆,尘土满地,狼藉不堪。我们才进去没一会儿,李先生到了,一进来二话不说抄起门口的一杆拖布就开始拖地,我赶紧上去抢,我说李先生您不用亲自动手,我来就行,谁知李先生手攥得那么牢,竟然抢不下来。李先生还一边把我推开一边笑着说:“我简单弄一下就好,我简单弄一下就好。”说是“简单弄一下”,我却看见他弓着腰在房间里忙活了半个多钟头,其间我又几次想把拖布抢下来,竟未遂。这又实实在在地让我对李先生又崇敬了一把。
上个学期,裘锡圭先生和沈培先生去了复旦,一度传闻李先生也要走,但李先生最终留下来了。这个学期开了两门课——“文字学”和“说文解字”概论,每周六个学时,辛苦得很。我突然想到了罗大佑的两句歌词:“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是的,我又想起了李先生上课时的目光,那样专注而执著。
张鸣
张鸣先生是个绝可爱的人物,相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这么说。或许对于中文系别的老师大家会由于个人的喜好有不同的褒贬,但是对于张鸣先生则是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好。
第一次见到张鸣先生是在2003年中文系的元旦联欢会上。张鸣先生穿着一袭灰色布衫、一双黑色布鞋出现在会场的时候,很多高年级的同学都起立鼓掌,甚至欢呼,我们这帮大一的小娃娃们则眼前一亮,心说中文系竟然还有如此古怪的人物。晚会进行到中段,张鸣先生在有一次为他而起的欢呼与掌声中走向会场中央,说我今晚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要唱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当时都一愣:知道宋词当年就是用来唱的,但没想到今天还有人能唱。结果他是真个唱了,第一次听的感觉怪怪的,因为用的是古曲,是民国时候杨荫浏先生从古代的曲谱转译过来的,但因为新鲜,也还是跟着鼓掌叫好。后来听张先生讲宋元文学史,讲宋词的时候也在课堂上唱过,后来还举行了一个“唱词会”,那时候才渐渐听出一些味道来。2005年的元旦联欢会上,张鸣先生又一次登场了——据称他从未错过任何一次中文系的元旦联欢会,每次必出席,出席必唱词,这次唱的好像是姜夔的一首,甫一开口,布置得颇现代化的会场竟弥漫起一种庄严肃穆的古典气氛。张先生的白发、灰衫、布鞋在浅蓝色灯光的笼罩下更显出一种古代书生的雅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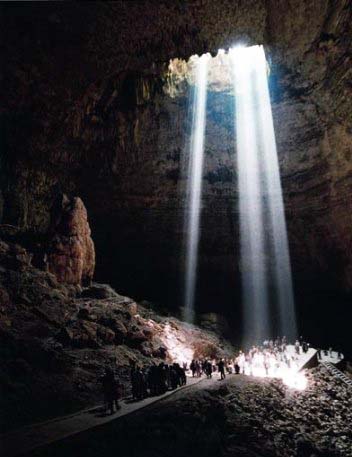
![[剑网三]寻找帮主夫人大作战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16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