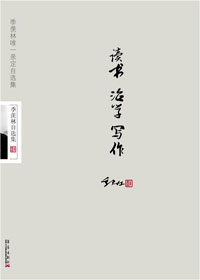���顤��ѧ��д��-��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Ĺ����������һ����ȱһ���ɡ����DZ������˵�߱��������һ���ġ���ˣ������г�ֵĻ�������������������������Ļ���Ϊ�ҹ��Ļ����������²ż汸���˲ţ�����Ϊ������⣬����Ϊ�������������������죬�������ڵأ��������ĵ������Ե�δ�������������һ���У���һ����ͼ����Ե��ر�ͻ��������ͼ�����ȫ����ѧͼ��ݵ��̳�����������֮���ԣ�����һ��֮˽�ԡ�����Ϊ��Ӧ�øе��������е��Ҹ���
�������ǣ�����ȫУʦ��Ա��ȴ����������������ϡ�����Ҹ���˯��������DZ���Ŭ��ѧϰ��Ŭ�����������Լ�������һ�������������������һ��һľ��һɽһʯ���������ǵ�ͼ��ݡ�����ͼ��ݵIJ���ӯ�ܳ䶰��Ȼ������Ӧ��֪����һ��һ����֮���ף�һҳһ�ŵ�֮ά�衣����ȫ�山���˱���ʮ����ϧ���������������ǵ�ͼ��ݲ����г��õ����������ǵĽ������Ҹ����м�ʵ�Ļ�����Ը��ȫУͬ�ʹ���֮��
����
�Һ������ѧ��1��
1991��11��6��
����Ҫ��̸�Һ������ѧ����ֱ��һ��ʮ��ʷ����֪�Ӻδ�̸�𡱡�
�����Ҵ�Сѧʱ����ʼѧϰӢ�ģ�������ֻ��ʮ��ɡ���ʱ�һ�����ʲô����ѧ��ֻ�������ʵؾ��������ѧ�ܺ�����ѡ��ǵõ�ʱѧӢ���ǿ���ģ�ʱ���������ϡ����������ҵļ������ֻ����ҹ�κ��ںڰ��У��߹�һƬ��������ҩ���Ļ��裬��ɫ����ҩ��ͬ��ɫ��Ҷ�ӻ�����һ����ɫ�������ƺ�����ǹۡ������Ժ��ڼ�ʮ��������������У�ѧϰӢ����ͬ��������ҩ������һ�𣬳�Ϊ�����Ļ��䡣
�������˳��У�Ӣ�ļ���ѧϰ��ѧУ�����쳣������������������һ����Ϫ����У�ᡣ�������죬�������죬���������������ǰ�Ķέ�̣�ʮ����㣬��ֱ���˼��ɾ������ǵ�Ӣ�Ľ�Աˮƽ�ܸߣ�����д�����ģ������ٸĶ�������һ�ʹ������Լ���дһ�顣����֮�ڣ���������������Ժ���ѧϰӢ����ͬ������У��һλ�Źֵ���ʦ����һ��Ҳ���������Ļ���ɡ�
�������˸��У��Լ��Ѿ�ʮ�������ˣ���Ȼ����ѧӢ�ģ��ֿ�ʼѧ�˵���ġ����˴�ʱ���ſ�ʼ�������ѧ������Ȥ���������������������Ӣ�Ľ�Ա���������Թ��Ľ�Ա������ǰ���꣬���ϵ���ɽ����ѧ������С����Ľ�Ա������������ͩ���ɹ������ң��Լ����ļ���������ɽ����ѧ���˽�ʦ������ѧ��д���ģ���Ȼ���������ģ����Ҿ���ģ��ͩ���ɵĵ��ӡ���֪��ôһ�����ҵ����ľ��ܵ����Ĵ��ࡣʲô����������೩�֮������ﳣ����������������Ǽ���Ĺ������������һ�꣬���ϵ���ɽ������ʡ�����С���������ئ�Ұ���ѧУ��ַ���ˣ�����Ҳ���ˣ�������ʦ�����˶��﷼�����ң��������١���ҲƵ�ȵȣ��������������ҡ���ҲƵ����ֻ���˼����£��ͱ�����ͨ�����ӵ��Ϻ������þ�׳���������Ժ��Ƕ��﷼���������ǡ����DZ���Ӣ��ϵ��ҵ���������һ����ƪС˵���������ɵIJ��ˡ���³Ѹд�����ԡ���ͬ³Ѹͨ���ţ�ͨ��ȫ�Ķ����ڡ�³Ѹȫ�����С�����Ȼ�̹��ģ�ȴ�������ѧ�������ڽ�ѧ����Ȼ�ὲ�������ѧ�ġ��Ҵ�ʱд���Ķ����ð�����֪��ôһ�����ҵ��������ܵ�����ʦ�Ĵ��ࡣ�����Ҵ����������һ�����ĵ������У���д������ͬ��һ��ͬ�������루�����뱱����ѧϵ����ȫ�ࡢȫУ֮�ڡ����һ��ʮ�߰����������˵�����Ǽ���Ĺ����������Ժ���Ȼ��˼�뻹�й�������Ҳֻ������С��������ѧϰ��ѧ�����е�ȻҲ�������ѧ�ľ��ģ�������ȷ�������ˡ�
��������ʱ�ڣ��������ձ�����������궩�������������ѧ���顣����һ����Ӣ���������ֵĶ�ƪС˵���������ַ�������е�һƪ���ƺ�û�����ꡣ��ʱһ������ֵ���������һ���µķ�Ǯ���ҽ�����ʳ�����¼���Ǯ��д�ŵ��ձ�ȥ���飬�鵽�ˣ���Ҫ����ʮ����·���̲�ȥ���������������������飬����ֱ���õ�ͨ�鱦�����е���죬�����ݡ���֮���ҵ���Ȥ�Ѿ�ȷ������Ҳ��ȷ�������Ժ�ѧϰ���о��ķ���
���������廪�Ժ���ѡ��ϵ�Ƶ�ʱ��֪������ʲôԭ��������һ����Ѫ���������ѧ��ѧ���߾��á�Ҫ֪���Ҹ��ж������Ŀƣ�����û��ѧ����ѧ����ѧ������ѧ��������ʮ�֣������ijɼ���ѧ��ѧ��ǻ�����֮�����Ը����Ȼ��ա�һ�ȳ嶯֮���ҵ���������ƽ����������������ʵʵ�������ؼ���ѧ�����ѧ�ɡ�
�Һ������ѧ��2��
�廪��ѧ������ѧϵ��ʵ��������Ӣ����ѧΪ�������ڣ���������һ���ˣ�����Ӣ�イ�ڡ���������һ���ŹֵĹ涨��ѧϰӢ���¡��������������κ�һ�֣���һ�꼶ѧ�����꼶���ͽ�ʲô���ר�Ż������ĺͷ��Ĵ���ĸѧ�𣬶���һ��Ӣ��һ��������J����˹���ġ�������ƫ�������ɼ�Ӣ�ĵ�ר�Ż�ͬ���ĺ͵��ĵ�ר�Ż�����ȫ�Dz���ͬ�ն���ġ�����Ŀγ������ո�����ѧ����������ѧ���ִ���ƪС˵��ɯʿ���ǡ�ŷ����ѧʷ������ʫ֮�Ƚϡ�Ӣ������ʫ�ˡ��й�Ӣ�ġ���ѧ�����ȵȡ��̴�һӢ�ĵ���Ҷ�������������˹����⽻�������̴�����DZ�����Miss��Bille�������ִ���ƪС˵������ɶ���Ӣ���ˣ����̶���ʫ֮�Ƚϵ�����嵣�����������ѧ������ɶ��������ո�����ѧ�������أ�Winter������ŷ����ѧʷ���ǵ�������Jameson�����̷��ĵ���HollandС�㣬�̵��ĵ�������������ˣ�Ecke����ʯ̹����von��den��Steinen������Щ������ڵ�ˮƽ������ô����������������;�������е�Ұ��̸����ζ�������������ʱ�䣬�ջ������һ�ѡ��һЩ�����ĿΣ������DZ����������ѧ������㡵ķ�����ѧ�����������Ԩ��ʫ�ȵȣ�Ҳ��������֣�����л���ĵĿΡ���Щ�γ�ˮƽ���ߣ������������������Ļ�����һЩ�γ̣������������ᵽ����һЩ�����Ρ���
�����������ѡ���п��Կ����������廪��ѧ���꣬��Ȥ���൱��ģ����ԡ���ѧ����ʷ���ڽ̼������漰���ˡ����ǵ���ר�Ż���ѧ�����Ӵ�һ���ģ�һֱ����ĵ��ģ����д���Ļ�����Ӣ�ģ���Ŀ��The��Early��Poems��of��H��lderlin��ָ����ʦ�ǰ��ˡ������Ѿ��Dz���������ˮƽ�Dz��ߵġ������ڼ䣬����д��ɢ�����⣬�һ������˵������ġ������ͻ����µ�ʱ����������ġ�õ���Ƕ�ô��������ô���ʺǡ�������ʷ��˹��Smith���ġ�Ǿޱ�����ܿ�ѷ��H��Jackson���ġ�����һƪ���衷������˹��D��Marquis���ġ��ز�ū�Դ�������Ų���Sologub����һЩ��Ʒ���ɶ����ֵ�һЩʫ�����С�õ���Ƕ�ô��������ô���ʺǡ�������������һƪ���衷����Ǿޱ���ȼ�ƪ�����ˣ�����Ĵ�Ŷ�û�п��������������ڶ�û���ˡ�
������ʱ�ҵ���Ȥ��������������ν����ʫ���ϣ�����Ҳ�з��硣��ʫ���ŷ������ɣ���������ʫ����������ɣ�������κ�ʲô���ƶ��У�ֻ�Dz��ؽ�ʫ��̩��������ŷϳ����ɵģ����ĵ�����û����˵���ҡ�����ϲ����ʫ���Ƿ�����κ����������÷�ͱ���ʱ��ά�����ȡ�κ�������ţ����������֣�������������������ϡ�������ҵĿ�ζ�������ҷ������ڵ���ν������ʫ�������ܻ������ǡ�Ӣ�����ˡ����Լ�����dzª����ѧ����������Ҫ���˽⣬���ֻ������һ�����˽⣨��ʵ���Լ�Ҳ�����þ��˽⣩���Ǻα�Ҫ��ѧ�����أ����⣬�һ�ϲ��Ӣ������ν���ζ���ѧʫ�������й�����ϲ�������������ģ��ƴ�������ɽ����أ��δ��Ľ���ʯ������Ӣ������Ψ���ģ�������廪���ġ�����Ⱥ��������ڡ�
�������������ڼ䣬��ͬ����ɮ��嵣������Ӵ��Ƚ϶ࡣ�������������һ������������ʱ��д������֮������¸����������������ྩ��ѧҹ��֣����������ͬҶ��������Ҳ�нӴ�����������Ӣ�ģ�ϲ��Ӣ��ɢ�ģ���Ͷ�����á���дɢ�ģ�Ҳ����ɢ�ġ�����һƪ���꡷��������Ҷ�йصġ�ѧ�ġ��ϣ��ܵ����Ĺ�����Ҳ�������Ķ��ӡ��ҳ���ͬ����ͬ�������ɮ��������Ӱ����֮�ݡ�������ˮľ�廪֮�Ҿ��ڹ��������档��Ҳ������ҹ�ƹ��������ߵ�ѧУ�����ĺ���С����ɢ������������������������������ɫ����������������õ��ɾ���
�Һ������ѧ��3��
�����廪ʱ���ѿ�ʼ�����ķ�����Ȥ����������������ķ�����ѧ���������ҵ���Ȥ�������ڵ�ʱû���˽����ģ����Կ������Ը��������ʵ�֡�1935������ҵ��˵¹���͢�����ſ�ʼ���߶���ʩ���أ�Wald��schmidt������ѧϰ���ĺͰ����ġ����ִ����ˣ�E��Sieg������ѧϰ���Ӻ��»����ġ�������ѧ��Ʒֻ���ڿ�ʱ��Ϊ���Խ̲���ѧϰ�����������ս�������߶���ʩ���ر����Ӿ������������֮����������ڿΡ���λ���ϵ���ʦ���кͰ������ܰ��Լ���һ��ѧ�ʺ����г����������������������ꡣ���Ⱥ�����ҷ��ӡ������衷���»��������ѧ���棬�������ұȽ����ѵ�̴���ġ�ʮ���Ӵ�������һ��������ʫд�ɵ�С˵ʵ�ڷdz��Ź֡���ͷһ�����ϴʳ������У���һ����Ҫһ������д�ij���ϸ�µ��������ˡ��һع��Ժ�֮���Է��롶ʮ���Ӵ�����������������γɵġ���ʱ����Ҫ���о�������ģ�û����Ͼ����������ѧ��������Ҳû����Ȥ���ڵ¹�ʮ�꣬û�з����һƪ������ѧ������Ҳû��д��һƪ��������ѧ�����¡����ڻ���������Ҳ�ƺ�����û���뵽Ҫ�о�������ѧ���ҵ���Ȥ����ȫȫת�Ƶ����Է��棬ת�Ƶ��»����ķ���ȥ�ˡ�
����1946��ع����ҵ�����������������Ȥ����������ڵķ�����ĺ��»����ĵ��о�������ȱ����������ϣ��������С��ҵ�ʱ��һ��ںţ����������ж���룬�Զ��ٷ�������˼��˵��������ʲô���ϣ��Ҿ���ʲô�о��������ɸ���Ϊ����֮���������Ҷ�ô�����ģ�Ҳֻ�������ˡ��Ҿ����������������������ѧ��Ʒ�ġ���ų��ڣ��ҷ����˵¹�ŮС˵�Ұ��ȣ�����˹�Ķ�ƪС˵������˹��С˵���ҷdz�ϲ��������Ů�����е��쳣ϸ�µıʴ�����淴����˹�Ķ�����ʵ��������Ķ�ƪС˵�ҡ��Ժ����ַ�����������涵ġ�ɳ�����ޡ��͡�������ʪ���������ˡ�����顷��һЩ��������ġ��������¡��ȡ�ֱ����ʱ���һ���û����־ר���о������ѧ�����������ڵĻ�����ӡ�Ļ���ϵʷ��ӡ�ȷ��ʷ����Ŭ�����飬�������ϡ�50�����������дһ�����ƴ���ӡ��ϵʷ������ٶ���д�ɣ���ϧ��ѭδ����ʮ��ƽ��У����ϱ���������һЩ����������һЩ��������Ȥ��Ȼ�ˡ��ںƽ�֮���������ѱ����ڵأ��������������÷����������ֲ������������£��װ��˷������С�ף�����һ����ռס�Լ������Ķ����ܿ��ճ־õķ��빤��������Ҳû�뵽�������⡣��ѡ��Ľ������ӡ�ȴ�ʷʫ����Ħ���ǡ�����Ŵ�1973�꿪ʼ���ڿ��ŷ����ص绰֮�࣬���ַ��롣��һ��Ҫ����Ѻ�ϡ�����ʱ����һ���ʵ����Ͻ����쳣���ѣ��Ҿ������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