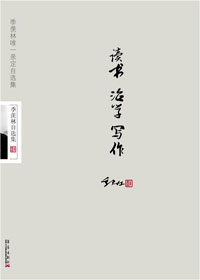读书·治学·写作-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当年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简化字,写的都是繁体,今天的青年读起来恐怕有些困难。但是,我一向认为,今天的青年,如果想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如果想做一点学问的话,则必须能认识繁体字。某人说的“识繁写简”一句话是极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把简化字推广到什么程度,绝不能把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都简体化了,那是无法想象的事。读点繁体字的书是事出必要理有固然的。我的日记在这方面对青年们或许有点帮助的。
以上就是我影印日记的根由。
文章的题目(1)
2001年11月23日
文章是广义的提法,细分起来,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几项:论文、专著、专题报告等等。所有的这几项都必须有一个题目,有了题目,才能下笔做文章,否则文章是无从写起的。
题目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不出两端,一个是别人出,一个是自己选。
过去一千多年的考试,我们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作文,都是老师或其他什么人出题目,应试者或者学生来写文章。封建社会的考试是代圣人立言,万万不能离题的,否则不但中不了秀才、举人或进士,严重的还有杀头的危险。至于学术研究,有的题目由国家领导部门出题目,你根据题目写成研究报告。也有的部门制订科研规划,规划上列出一些题目,供选题参考。一般说来,选择的自由不大。20世纪50年代,我也曾参加过制订社会科学规划的工作,开了不知多少会,用了不知多少纸张,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规划终于制订出来了。但是,后来就没有多少人过问,仿佛是“为规划而规划”。
以上都属于“别人出”的范畴。
至于“自己选”,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自由的。然而实际上也不尽然,有时候也要“代圣人立言”。就是你自己选定的题目,话却不一定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话也不一定能尽情吐露。于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八股”,只准说一定的话,话只准说到一定的程度。中外历史都证明,只有在真正“百家争鸣”的时代,学术才真能发展。
特别是有一种倾向危害最大。年纪大一点的学术研究者都不会忘记,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某一些人大刀阔斧地批判“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这些人大概从来不看学术杂志,从来也写不出有新见解的文章,只能奉命唯谨,代圣人立言。
稍懂学术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学术上的新见解总是最先发表在杂志上刊登的论文,进入学术专著,多半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学者都必须尽量多地尽量及时地阅读中外有关的杂志。在阅读中,认为观点正确,则心领神会。认为不正确,则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阅读既多,则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见解,发而为文,对自己这一门学问会有所推动。这就是“从杂志缝里找文章”。我现在发现,有颇为不少的“学者”从来不或至少很少阅读中外学术杂志。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一门学问发展的新动向,也得不到创新的灵感,抱残守缺,鼠目寸光,抱着几十年的老皇历不放,在这样的情况下,焉能写出好文章!我们应当经常不断地阅读中外杂志,结合随时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一心一意地“从杂志缝里找文章”。
我的处女作我的处女作
哪一篇是我的处女作呢?这有点难说。究竟什么是处女作呢?也不容易说清楚。如果小学生的第一篇作文就是处女作的话,那我说不出。如果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处女作的话,我可以谈一谈。
我在高中里就开始学习着写东西。我的国文老师是胡也频、董秋芳(冬芬)、夏莱蒂诸先生。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上比较知名的作家,对我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当时写过一些东西,包括普罗文艺理论在内,颇受到老师们的鼓励。从此就同笔墨结下了不解缘。在那以后五十多年中,我虽然走上了一条与文艺创作关系不大的道路;但是积习难除,至今还在舞笔弄墨;好像不如此,心里就不得安宁。当时的作品好像没有印出来过,所以不把它们算作处女作。 。。
文章的题目(2)
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来上大学,念的是西洋文学系。但是只要心有所感,就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往往写一些可以算是散文一类的东西。第一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目是《枸杞树》,里面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我十九岁离家到北京来考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走这样长的路,而且中学与大学之间好像有一条鸿沟,跨过这条沟,人生长途上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情况反映到我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我有点惊异,有点担心,有点好奇,又有点迷惘。初到北京,什么东西都觉得新奇可爱;但是心灵中又没有余裕去爱这些东西。当时想考上一个好大学,比现在要难得多,往往在几千人中只录取一二百名,竞争是异常激烈的,心里的斗争也同样激烈。因此,心里就像是开了油盐店,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但是美丽的希望也时时向我招手,好像在眼前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片玫瑰花园,姹紫嫣红,芳香四溢。
这种心情牢牢地控制住我,久久难忘,永远难忘。大学考取了,再也不必担心什么了,但是对这心情的忆念却依然存在,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一篇短文:《枸杞树》。
这一篇所谓处女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同我后来写的一些类似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仔细研究起来,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是有的,首先就表现在这篇短文的结构上。所谓结构,我的意思是指文章的行文布局,特别是起头与结尾更是文章的关键部位。文章一起头,必须立刻就把读者的注意力牢牢捉住,让他非读下去不可,大有欲罢不能之势。这种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颇为不少的。我曾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段有关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写《相州画锦堂记》的记载。大意是说,欧阳修经过深思熟虑把文章写完,派人送走。但是,他忽然又想到,文章的起头不够满意,立刻又派人快马加鞭,追回差人,把文章的起头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自己觉得满意,才又送走。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宋朝另一个大文学家苏轼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起头两句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古文观止》编选者给这两句话写了一个夹注:“东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头,起行数十遭,忽得此两句,是从古来圣贤远远想入。”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我现在暂时不举了。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是以多么慎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文章的起头的。
至于结尾,中国文学史上有同样著名的例子。我在这里举一个大家所熟知的,这就是唐代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这一首诗的结尾两句话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让人感到韵味无穷。只要稍稍留意就可以发现,古代的诗人几乎没有哪一篇不在结尾上下工夫的,诗文总不能平平淡淡地结束,总要给人留下一点余味,含吮咀嚼,经久不息。
写到这里,话又回到我的处女作上。这一篇短文的起头与结尾都有明显的惨淡经营的痕迹,现在回忆起来,只是那个开头,就费了不少工夫,结果似乎还算满意,因为我一个同班同学看了说:“你那个起头很有意思。”什么叫“很有意思”呢?我不完全理解,起码他是表示同意吧。
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一件事情与这篇短文有关,应该在这里提一提。在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曾翻译过一篇英国散文作家LP Smith的文章,名叫《蔷薇》,发表在1931年4月24日《华北日报?副刊》上。这篇文章的结构有一个特点。在第一段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整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耀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这是那个小城留给观者的一个鲜明生动的印象。到了整篇文章的结尾处,这一句话又出现了一次。我觉得这种写法很有意思,在写《枸杞树》的时候有意加以模仿。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写抒情散文 (不是政论,不是杂文),可以尝试着像谱乐曲那样写,主要旋律可以多次出现,把散文写成像小夜曲,借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幻想,我自己也尝试过几次。结果如何呢?我不清楚。好像并没有得到知音,颇有寂寞之感。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在形式方面标新立异者,颇不乏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一个有名的例子。现代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极少有人注重形式,我认为似乎可以改变一下。
“你不是在这里宣传‘八股’吗?”我隐约听到有人在斥责。如果写文章讲究一点技巧就算是“八股”的话,这样的“八股”我一定要宣传。我生也晚,没有赶上作“八股”的年代。但是我从一些清代的笔记中了解到“八股”的一些情况。它的内容完全是腐朽昏庸的,必须彻底加以扬弃。至于形式,那些过分雕琢巧伪的东西也必须否定。那一点想把文章写得比较有点逻辑性、有点系统性,不蔓不枝,重点突出的用意,则是可以借鉴的。写文章,在艺术境界形成以后,在物化的过程中注意技巧,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必须加以提倡。在过去,“八股”中偶尔也会有好文章的。上面谈到的唐代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就是试帖诗,是“八股”一类,尽管遭到鲁迅先生的否定,但是你能不承认这是一首传诵古今的好诗吗?自然,自古以来,确有一些名篇,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一点也没有追求技巧的痕迹。但是,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写这样的文章需要很深的功力,很高的艺术修养。我们平常说的“返璞归真”,就是指的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极难达到的,这与率尔命笔,草率从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决非我一个人的怪论,然而,不足为外人道也。
。。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
1985年7月4日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专门研究范围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在这一方面,他是蜚声世界的权威。他的老师是德国的梵文大家吕德斯教授,也是以学风谨严著称的。教授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但是,给我教育最大的还是我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按德国规定,一个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念三个系:一个主系和两个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两个副系是斯拉夫语文系和英国语文系。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