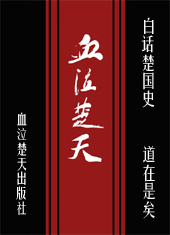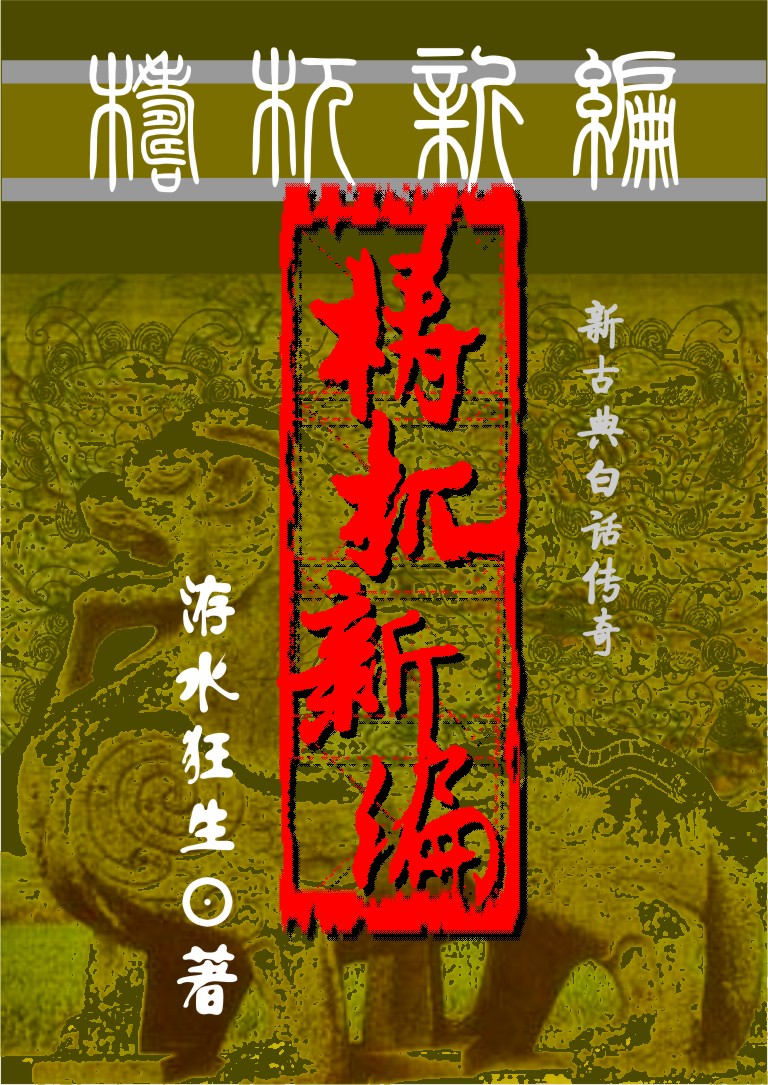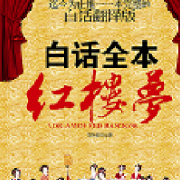������ʷ--Ѫ������-��1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Ͼ����s����֮����˷���¾���������֮����������Ӥ�루�ֳ�������¥Ӥ����Ϊ�Զ�֮��ĸ�ܣ�Ϊ�о����˷���ֳ�ʿׯ����������������Դ�Ϊ�Ͼ�������ף��ָ��ܣ��ֳ�֪ׯ�ӣ�����ͬ���ֳ�ԭͬ��Ϊ�¾�����ּ����˾�Υ�Ľ���������Ӧ���ǵ�֪��ׯ�����Դ�����֣�����ཫ�ڣ���ˣ���ҲϤ��ǰ����
�������������ָ�����������֣ƽ�Ͳ���ս�ˣ����ˣ�����ȳ����˺��ٷ�֣�����Ҳ��ͬ������Ϊ����ׯ���߱��¡��̡������¡��䡢���������ơ����ȣ���ׯ������֣�Ѷ���֮������֣������֮���е����̣��������С���Σ�ǰ����£���������֣������������ƣ�ͣ���Ծ�Ҳû��Թ�ޣ������г�������ũ������Ȼ�ճ���Ӫ�������ֺ��������¡����¡�ũ�¸������������ͻ���ٴΣ��J�������尽��Ϊ�������ξ��з���ǰ�����Ҿ���˾��ְ�������������н��������������ж������в���Ҫͳ˧������ܰ���������������У��ξ��з��������Ƶ䣨�ȶ����ƶȡ��������⣬����ͬ���������ۣ����������������ۣ�ѡ���Ե��У��ͷ��۹��ͣ���ʧ�����ÿͣ�������;�У������д��衣��ͬ�����в�ͬ�ķ��μ������𣬹��峣�õ����أ�������֪η�塣��Щ�������������Ʋ��ҡ���Ե��������С����ɡ���ʱ����ӡ���˳�ij����ͳ���������ܵУ���ˣ���ǿ������֪�Ѷ��ˣ����������������õ�ѡ�����ķ����DZȽ�ȫ������ģ��ڹ��ڳ���������ʷ�ϼ���ȱ��������£���һ�������������Եø�Ϊ���
����Ȼ������ս���ȣ��ȣ���Ϊ��˧���ǰ����֪�Ѷ��ˣ���֣���飬���˲��䣬������ͬʱ�������֮�ģ�ʧ���֮��������������ų����Ϊ�����Ǵ��ɷ���Ϊ���������ڳ����ԣ����������˶�ʧȥ������λ���������������վ���Υ��Ը����о������µĽ����ɺӣ�Ѱ����ս��
�����ȣ��ȣ��ɺӺ������������������ȣ��ȣ����ذܡ�����˽��Ȱ���ָ�����������Ϊ������ȣ��ȣ����ܣ���ʧȥ֣�������½����ֲ����ͳ˧����ܴ�����������������ȡʤ�Ŀ��ܣ�����ʧ���ˣ�������������������������������˳е����ܱ�һ���е�Ҫ�����������ʣ���ʱ���ǽ�����ӦΪ���ָ����ţ���Ϊ�������ָ����������ĽǶȳ���Ȱ���ָ����������ǣ�������ȫ���ɺ��ˡ�
���������ٿ�������ߣ���ʱ������פ����֣�����I��Ҳ��Ϊ�����������������������ش�������ӣ����о������أ�����Ӥ�룩��������ӷ������Ӳࣩ���Ҿ���ע�⣬������û������������н�������ֻ�н���û������ׯ�屾�����������ƺӾ��˾���������ʦ�ɺӣ�ׯ��Ҳ���ʹ��˾����������ʦ���潻�档����ׯ�����ҵ���Σ��������ݵ��游��ǰ��Ƹ³��٣����٣��ĸ��ף������ս������Ϊ��������˧���ͣ��ر��ȣ��ȣ�������ã��б����ʣ�Ŀ�����ϣ�ʿ��ز������������⣬��ׯ���Ǿ��������ָ�ֻ�ǽ�����ִ���������ս���ˣ��Ծ��ܳ���������������ڣ��������尽�����������ʦս��������ζ�����˵ʲô����ս�����ݣ����飩��֮������ʳ��������˼��˵�����ս�ܣ�ɱ����Σ���ʳ���ⶼ�������ֲ��ܾ�֮����λ�Ӧ����������֮�ݣ�����Ϊ��ı�ӣ����ݣ���֮�⽫�ڽ������ɵ�ʳ�������������ԣ�����ʾ�������dz�ׯ��������εķ�����Ҳ��Щ���ƣ�Ҳ���뱻�˼�Ц����ʱ���������尽��������������ϣ���ǰ��ǰ����ͷ�������ˡ�ʵ�����˾�����ׯ����æ�����ת��ͷ������פ�ڹܣ������������֮�����Դ�������
������ʦ�ɺ�֮��פ���ڰ����z����ɽ���������������֮����֮�䣬��ʱ��֣���ɻ���������ʦ��Ȱս����Ϊ���������ϣ�ƣ�������ֲ��豸��ϣ������֣�������������������ȣ��ȣ�Ҳ�ٴ�Ҫ���Ӧ֣�������������ս�������¾���������ȴ�ֲ�ͬ���������������ս��
���������Կ�ӹ������������ղ��ֹ��˶�ѵ֮������֮���ף�����֮���գ����֮�����Ե����ھ������ղ��־�ʵ������֮��ʤ֮���ɱ�����֮�ٿˣ�������ѵ��������͡�ð����·���ƣ�����ɽ�֡���֮Ի�����������ڣ������ѡ�������ν�����ȴ���ӷ�����Ի����ʦֱΪ׳����Ϊ�ϡ������£�����Թ�ڳ���������ֱ������ν�ϡ����֮�֣���Ϊ���㣨�����µ�λ�������ڵ��š�Ӫ�ȣ���������һ�䣬��ƫ֮����һ������ƫ��һƫʮ��������������ʮ�������ҹ���ݣ��������У�������֮�������ڻ衣�ڹ�����ҹ���Դ����ݣ�����ν�ޱ���������֣֮��Ҳ��ʦ�壬��֮��Ҳ��ʦ�����ˣ������ڳ�������֣���ӡ���Ȱ��ս���ҿ��������������������Ҳ�Ҳ��֣���ɴӡ�������������ʮ���꡷��
�塢���ϰܽ���2��5��3��
�塢���ϰܽ���2��5��3��
������������Ҫ���˼��㣺һ�dz����ι���ʱ������֮��Ҫ��ʶ���������ס��������գ�Ҫ�Ļ������壬���ֵĻ�˵�����ǽ̵�����Ҫ��Σ����ʶ��Ҫ����������֮���������������ξ���Ҳ�dz����������Ľ�ѵ�����Ⱦ�������͡�ð��·���Ƶļ��ܶ���ͳ��ѵ�䣬Ҳ����˵�����ӵ����ι������úã�����һһ��Ԧ��֣������˵�˳�ʦ�����ϡ����豸��ȱ�㣻���Ǵ�֣ͬ������������������ڳ�����ɵ¸����ص��ˌ���ʦ�壩���˿��Կ�������֣���֮��˴����������ɻ�����Ȱս�������dzֽ����������Է�ǿ�Ա�һ�������ַ�����������Ϊ���ģ��ı�ʤ��֣�����ıߣ�����֣��������
�������ǣ��о�����������¾������ͬȴ��ս��վ���ȣ��ȣ�һ�ߡ�
����������������������ԣ���û��������ս������һ�������⽻�����ׯ����������������ȥ�����߽��ˣ��䶨֣�������ԣ����漾��ʿ�ᣩ��ƽ��֮�����ĺ��֣�и����ң���������������˷�Ԧ����������Щ���ȴ���ȣ��ȣ���Ϊ�Գ��ƶ�������������ȥ�����漾��Ӧ��֮�ʣ�����תΪǿӲ����������Ŀ�ľ���Ҫ���߳�����ս�벻ս�����Ŀ�����뼤ŭ��ׯ�����Ӷ������ʹʹ���ظ�һ��������ʱ��������Ȼ�ɺӣ����ǽ��������߶��й��ǣ�������ս���Ͼ���������������������������ӣ�����ʧ���ˡ�
������Ȼ��ˣ���ׯ����������ͣ�����ʹ�ڵ�������ȥ����Σ��о�˧���ָ���ͬ���ˣ����һ��̶��˻������ڡ�һ����ս�ƺ���Ҫ�����ˣ�Ȼ������
����
���������ɵ���ȥ��ʦ��ս����һ��ս�Ŷӣ��������ֲ�������������������Ϊ���塣��������ǣ��ֲ�����ִ�Σ������³����ű�����������������ʦ���У�ɱ�˽���ȡ��������ַ�²���䣬֮�������ɿ�ݳ���ʻ����������������һ�ӽ����������ǣ��ֲ��ڳ�����������֮�����������Ľ������������ܿ���������ʱ�����ֻʣһ֧���ˣ��ֲ�������֧�����Ա�ͻȻ��������¹�������䱳�ϣ�����������Ŀ��������˱��������䡣ͬʱ�������³�������¹�����Ľ��ˣ�����˵����������֮��ʱ������֮δ������������ߡ���������������ǰ�����ǵģ�����������ֹ�ˡ��������ֲ����䣬�����ֻ�˵������ֵ�þ��صľ��ӣ��ͷ�����²���ǡ�
����������δ�ս�е�һ��С���������пɼ���������ʿ�ķ�ɡ�ӡ֤��ǰ���������������ӶԳ����ķ����жϡ�
�������������ڽ�����أ���Ȼ��κ蟺�����Ⱥ��ʹ��ʦ����������û�������Ը�˽�����������ģ���ǿ����ս��κ蟻�ϣ����ʦս�ܣ��S���ӣ��ˣ��ٿ������˳�ʹ�������ȣ��ȣ��豸���ȣ��ȣ�Թ�о�˧���ָ���ս��ս���˲��ˣ��������£������S���ӵĽ��顣
��������������Ϸ���Եı仯��κ蟳�ʹ��ʦ��ŭ�˳��ˣ����˵���������칳�ʹ��ʦ�������������Ϯ��ʦ���š���ׯ�����Դ���������칣���ʱ��ׯ�������������㣬������ҹ㣬һ����ʮ����ׯ���������ҹ㣬����Ϊ�������ɻ�Ϊ�ң���������㣬����Ϊ��������Ϊ�ҡ��ڳ�ׯ����ǿ�����£��������ɽ�֣������³���֮�������������칵ļ��ѡ�������Ҳ���ģ�κ蟺���칼�ŭ��ʦ�����������ܔ������Ӧ����ʱ�˵�κ蟹���������ܔ��ʻȥ�ij������졣��Ϊ�ǽ�ʦ�����ͻϮ���ͱ��ۻ��������ʦ����ʦҲ���£���ׯ��������ڽ�ʦ���������尽��ׯ�����ڵ�����£����Ͼ��ߣ��ȷ����ˣ�����ʦӭ������������������˳����ȹ���������������ߣ�ȴû���豸��û�뵽������ͻϮ�����ָ����˲�֪��Ϊ���鼱�������˾��úӡ�
��������һ��һ��������ս��̬�ƾ����̸ı��ˡ�������ׯ�����ڵij������ƽ����������뽫�Ҿܣ����γ£������¾����ƻݺ�˵�����ܣ����γ£��������Ͼ����������ú����ߡ������ϣ���ʦ��ߛ����������ߛ�����û�з���ʲô���ս����ֻ����Ϊ�������ս�ڴ˵أ�����֮��
����ʵ���ϣ���ׯ������û�н���ɱ�������������϶ɺӣ���ҹ��ͣ����ʦҲû��ȫ��ȥ�����ֻҪȡʤ�˾����ˣ��������������ս�������ɳ�ׯ������ߛ�����ĺ�Ӻ�������ʡԭ����أ������˵��Ի����Կ�������
�����˵�Ի������������������ս�ʬ��Ϊ���ۡ����ſ˵б�ʾ����������书����
��������Ի�����Ƕ���֪Ҳ�����ģ�ֹ��Ϊ�䡣�������̡������̡�Ի������ɸ꣬�ؙ���ʸ������ܲ�£�����ʱ�ģ�������֮�����������䡷��������Ի���ȶ�������������Ի������ʱ��˼��������������Ի���������ŷ��ꡣ�����䣬������꫱����������������ڡ������Ҳ����ʹ�����������¡�����ʹ�������ǣ����ӣ��۱�������������ӡ�������ꫣ����ܱ������н��ڣ��ɵö�������Υ�����̶࣬��ΰ��ɣ��¶�ǿ�������Ժ��ڣ�����֮����������֮�ң���Ϊ���٣����Է�ƣ������ߵ£�����һ�ɣ�����ʾ�����Ϊ�Ⱦ���������¶��ѡ�����ṦҲ������������������ȡ�侨�����֮����Ϊ��¾�����Ǻ��о��ۣ��Գ���������������������Ծ��������������ֿ���Ϊ���ۺ�����������õ�txt������
�塢���ϰܽ���2��5��4��
�塢���ϰܽ���2��5��4��
���������ǣ��˵������ׯ���ռ�����ʬ����Ϊ�������ʬ���������֮������ľ����֮����ʾ�书�ں����������һ�����±���ֻ�����Ɱ�����ʬ���ɵ�����ɡ���ׯ����Ϊ���䱾����ֹ�����˼�����ڣ�������ꫣ���Ҳ�������������������ڡ������Ҳ������ν���֮ս�������ڶ࣬��Ű�����±��������������ء��������ȱ�Ű�ֲ����ñ����ղ���������̸���ϱ�������Ȼ�ڣ���ô�ܶ�����������ƣ�ͱ�������̸���ϰ����Ը����е��ж�����������˳����ȻҲ�Ʋ��Ϻ����ˡ�������֮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