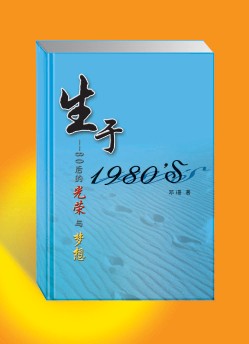80后--睡在东莞-第8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楚妖精完全是一种拼命的姿势,护着红薯,恶狠狠地一脚踢在男人最脆弱的地方,小五蹲在地上,刚要站起,楚妖精横跨一步,插了插腰,恶狠狠地对着小五一瞪眼,小五居然呆住了,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疯婆娘,你这个疯婆娘,你没有治了。”
楚妖精咬碎了红薯,嘴对嘴地向牛仔喂去。
过了中午,海浪变小了,双懿吃了一个红薯,伸了伸手臂,走到了海边,正准备下海,变天了,风起云涌,风浪又开始变大了。阿依古丽抓了抓双懿的衣袖,这一路上,这个新疆妹跟双懿已经有了感情,双懿回头看了看我们,又望了一眼楚妖精,长叹了一口气,一头跳进冰冷的海里。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周双懿像骄傲地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几分钟后,倾盆大雨,像机关枪子弹一样砸下来,七爷惊呼:“遭了!”我们都没有去避雨,站在雨水中,眼汪汪地望着双懿被一个浪吞没,又被另一个浪吐出来,又吞没,又吐出来……渐渐看不见了。
我们都努力把眼珠睁得最大,可是真得找不到,雨水把眼镜玻璃弄得水雾缭绕,用手轻轻擦掉了一点,定睛一看还是找不到。
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
良久,我们转身走回地牢,谁都没有多说话。阿依一步三回头,突然惊喜地大叫一声,我们齐整地向后转,又失望了,远方跃起了一只海豚。
天越来越黑;越来越冷;地牢终于成了牢。妲己晕倒在了地上,红玫瑰递给她一块红薯,笨笨狗按了她半天的人中,才缓缓醒了过来。
七爷哈哈笑道:“琴王,你弹个曲子,给大家解解闷吧。”
琴王望着七爷勉强一笑,爬到琴边,清脆的音符飘了出来;乐曲很通俗;很多姑娘跟随着哼了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琴王弹到这里,手一涩,呆了呆,不弹了。
很多人想起了双懿,又望了一眼躺在地上牛仔,不少囡囡哭了。
红玫瑰道:“七爷,投降吧。”
七爷用枯枝扒着火堆,低着头,没有回答。
外边雨下得越来越大。我们像丐帮一样横七竖八地倒在洞里。
冬瓜道:“真他妈贼天!爷想喝一壶二锅头,要北京牛栏山出的。”
白素素小心翼翼道:“七爷,办个合资企业而已,我们还是可以控股的啊,这样下去大家都过不到明天了。”
七爷站起望了望最高处的电话,走了几步又坐下。
牛仔身子有些发僵了,我和楚妖精把他移得更接近火堆的地方,笨笨狗不顾楚妖精的白眼,时不时地把手指放到牛仔的鼻孔下。
夜深了,火苗的声音变得恍惚起来,我已经出现了一些幻影。
一道声音划破了长空,刚猛遒劲,如狮子吼,又如金刚吼,把大家都从睡梦和恍惚里惊醒。七爷抬着头,唱起歌来了,是陕西的秦腔,是陕西冷娃的秦腔,是《金沙滩》中杨继业的几句:“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家国……何惧死生啊……!”
我们都不再说话,也没有说话的气力了。但内心深处尽升起一丝莫名的力量来。
过了好一阵子,正当我们树立起抵抗的决心时,七爷嚎啕大哭,咬着嘴唇道:“大家伙,跟着我朱七受苦了。请再坚持一个晚上,我总觉得双懿这丫头不可能就这样没了。明晨,就明晨,如果没有奇迹,我……我就给龟头挂电话。”
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这不仅是周杰伦的歌。
楚妖精几次冲上去想打电话,都被西瓜拦住,我对着笨笨狗使了个眼色,这“二把刀”现在毫无疑问是妖精唯一信任的专业人员,楚妖精根本不看我的颜色,道:“牛仔没事,要死的话已经死了,只是他身体素质太好了,再熬一晚应该没问题,也可能马上就死了。”弄得楚妖精哭笑不得。
天蒙蒙亮,我们挣扎着爬起,海滩还是寂寥无人。岛中央树上用裤子编成的SOS的记号,还在左右摇摆,愁没渡江,秋心拆两半,怕有人是上不了岸了。
阿楚和红玫瑰打了起来,阿楚要抢红薯,红玫瑰不给。阿楚道:“这是我找到了,为什么不给我。”
红玫瑰不说话,但就是不给。阿楚力气大,抢到了手,阿楚放在嘴边,红玫瑰哭了,阿楚呆了一下,环顾左右,这一群人都两天没吃饭了,都带着狼般的眼珠子望着她。阿楚也哭了,她知道自己昨天多少还吃了一个大的,这批人都是颗粒没进,阿楚犹豫了半天,咬着牙扔回给了红玫瑰,哭着道:“我从来没饿过这么久,从来没饿过这么久,嗯,我再去找找。”
七爷叹了一口气,踉跄着向电话机走去,一群人跟随在他后面,三百来米的路走了将近半个小时
七爷艰难地把手抬起,拨起了号码,整个手指都是颤抖的,按最后一个号码时,阿楚从山后大叫道:“双懿!是双懿!”
七爷用力挂了电话。我们全场惊呼,七爷却突然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激起半卷尘土。
南瓜凄凉地大声叫道:“七爷……七爷……呜哇……”
蝴蝶兰也哭了,道:“不是……不是……”
七爷猛烈地睁圆了眼睛,大骂道:“哭丧啊,老子还没挂,一晚没睡,睡会还被你们吵!”
红玫瑰抹抹眼泪,递给他一个红薯,七爷转过身去,道:“去,给双懿。”
沙滩上,周双懿像一滩烂泥般倒着,衣服已经不成样子,昨晚风急雨骤,茫茫大海,真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个被冬瓜誉为生平所见最完美的背部,都是伤痕和青淤,双懿见到我们只会动嘴唇,已经发不出声音。
狼吞虎咽了一个红薯后,周双懿马上吐了出来,然后就吐出了很多海水,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次恐怖记忆,那种呕吐,简直触目惊心,感觉肝和胆都要被吐了出来,双懿,昨天还是一个绝色美女,现在就是一个垂死挣扎之人,吐得眼珠都快爆出眼眶。
冬瓜过去扶着她,良久,冬瓜被突然摔倒在地。周双懿怒视着冬瓜道:“谁让你扶我的!七爷,给澳门的电话打通了,但没用,他们说这里是日本领海,如果闯进来会很复杂,他们没有这个权限。”
我们伫立在风中,像一群亚细亚的孤儿,冰冷的绝望。
“但,我昨天晚上游到一个海岛上,正好碰到了一艘偷渡去日本的渔船,船长答应走了我今天上午过来救我。”
上岛的第三天,也就是公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十六分二十九秒,我们被一个专业偷渡的福建船长救上的船。
那一天正好的圣诞节,耶稣在一个马棚里呱呱落地,感谢上帝,感谢主,你是人类一座永恒的灯塔。
后来终于上岸了,七爷、南瓜、红玫瑰、琴王还有楚妖精,都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第七十一重返人间
那个福建船长姓施,很洒脱地一笑,五短身材,两眼却冒着精光。跑江湖又捞偏门的大多很四海,他对我们的来头,对我们为什么会像一群叫花子般流落在荒岛,统统不问,却早已安排了一桌饭菜,让我们感动了半天。
面对一桌饭菜,红玫瑰却还紧紧握着最后一个红薯,把她烤热,又不舍得吃。我们哈哈大笑,红玫瑰盯着红薯调皮道:“再看我,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吃掉。”说完,眼红红地,对我们道:“你们知道这两天最辛苦的是谁吗?是我,我可一直想吃这红薯,想得都梦见自己变成野猪了。”
白素素笑道:“哪有这么漂亮的野猪。”
红玫瑰紧紧将红薯又揣回自己怀里里。
这船长夹了一筷子菜。道:“昨天傍晚见到那位姑娘在海里游泳,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看花了眼,看见了传说中的美人鱼呢?哈哈,幸亏停下了船。我一听说这姑娘为了救自己的同伴,已经在海水里泡了几个小时,从一个荒岛游到另一个荒岛时,我就竖起了大拇指。这么有情有义的女人不多啊,当时我就应该来救你们,但干偷渡这行,约好了时间就没有办法更改航线,所以一做完事我就连夜赶回来了。”
卫哥很感动地取下了手腕上的手表,双手递给福建人道:“毛介卫,大恩不言谢,来东莞一定到家华酒店来,再酬谢。”
船长接过手表,轻轻一笑道:“卡地亚牌,瑞士名表啊。毛兄你小看兄弟了,这玩意儿兄弟好几房间。你送给美人鱼吧,这美人鱼我收了做妹妹了,你们可别欺负她啊!不过东莞那是个好地方,我一定会去的,哈哈。”施船长带着男人都懂的笑容诡异道。
七爷道:“也欢迎来北京,到了北京找朱七,只要是朱七办得到的,都给你办到,办不到的拼了命也给你办到。”
施船长敲了敲桌子,周双懿嘟着嘴巴,像妹妹一样给哥哥倒上了碗酒,施船长道:“嗯,在外边混靠的就是朋友,你们这些朋友我交了,如果各位来福建晋江,随便哪个沿海的村子,就说自己是施老大的朋友,自然会有人招待你们。”
李鹰道:“福建晋江,你和赖.....”卫哥瞪了他一眼,李鹰自知失言,收住了话语。
施船长毫不在意道:“他啊,害得自己家里真惨。他跟我是好多年的竞争对手,以前他比我混得好点,现在他比我混的差点。九四年为了一条航线,我跟他打过仗,现在他走了,我还真寂寞。”
听完这番话,我们全部肃然起敬。
我曾经在广州某文化局工作过,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文化局里面有一群半文盲,还有一些全文盲是高官的家属,说他们全部是酒囊饭袋有点冤枉,说一半是酒囊饭袋,绝对有漏网之鱼。倒是市井之间,真不缺豪爽的英雄好汉。
施船长望了望远出:“马上就离开日本的海域了,过了那个小冲岛,我们就安全了。”
我们全部端起了酒杯,可就在小冲岛,就在喝酒的时候,出事了,一艘日本大船,生生地拦在了我们面前,一个女人,带着一群拿着枪的日本女海警,跳到了我们船上。
施船长回身一手拿手枪,一手拨手机,被老江湖卫哥挡住:“施老弟,这还在日本,你不用为了我们这样,我们会有办法解决的。”
施船长把手枪放了进去,奇道:“见鬼了,从来没见过日本突然派出这么多女警?”
七爷苦笑道:“渡边和龟头太谨慎了,为了防我们的美人计,全部派女警上了。施船长,这没有你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就不要拖进来了,我们已经很谢谢你了。”
施船长道:“放心,只要不是大事,到时我去日本保你们出来。”
我们都不置可否。施船长很倨傲地坐在桌子上。
日本一个女警官说了一大挂话,翻译过来是怀疑我们的船不法入境,有不良动机,可能贩卖毒品,要带回警察局调查,叫男的都蹲下。施船长和七爷不理会她们,转身进了男厕所。
贩卖毒品?!这太毒了吧。我蹲在甲板上用眼角一瞟,突然脑袋发麻,有了一丝希望,那个带头的美女,是文子,在葡京跟我一夜欢愉的文子,龟头的女儿文子!
一夜之情会有情吗?
我走到了文子面前,文子看见了我,不是很意外,但也低下头,一言不发,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