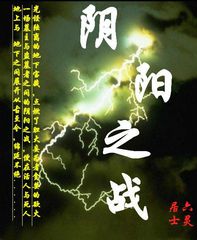天公不语对枯棋-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和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这种差距,恐怕正是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军队在所有对外民族战争中,基本上一触即溃、望风披靡,从无获胜记录的真正原因。人类战争史表明,武器装备的进化决定了战争的样式,火器的出现注定了冷兵器时代的终结。核武器的使用,也使常规战争的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装备落后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劣势装备的军队要打胜仗,关键在于军队自身的组织形式和精神状态。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对外战争全面胜利的,是抗日战争,但这毕竟是依靠盟军的反攻取得的。而真正打出自己军威的,是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锋中打成平手,迫使联合国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当然这是后话。而在 1894年,调军队上山海关前线时,据一位家居北京的目击者说,“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这同成千上万日本人舞着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赴战场,恰成对照。该目击者还说:
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黛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按,指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蹙额,戚戚然。这样的军队底牌,李鸿章完全清楚,住在二条胡同的翁同知晓吗?李鸿章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倡导者,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耗用了巨额资金,他也一直给朝廷以军队可恃一战的印象。及至战时,却主张妥协和忍让,这自然为翁同不能接受。在战争准备、战机捕捉、战役指挥上的诸多失误,李鸿章也难辞其咎。但洋务运动本来就是体制内部的修补,并未触动传统机制,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存危机。若以为只要朝廷上下皆有抗敌言论和作战决心,中国便能战胜日本,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算盘。否则,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岂不是用“爱国主义”的口号便能替代?李鸿章在1864年便发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呼唤,提出中国欲自强,必须学习西方。三十年后,他却回避与东洋近邻日本决战,他的隐衷,难道就是为了“卖国”?翁同是甲午战争时的积极主战派。从7月15日即丰岛海战开战前十天,便已奉旨与李鸿藻一起参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议朝鲜局势。他主战的出发点,是相信海陆军尚堪一战。但我们在整场战争之中,除了听他高唱主战宏论,以及在马关议和前力主“宁赔款,不割地”以外,未见其进行实质性的赞划和补救。这说明,作为想辅佐皇帝独振乾纲的 “后清流”官员,有心杀贼,无策典兵,不知道如何去迎接日本的挑战。进一步分析,也暴露出整个清政府中枢确不具备与日本相匹敌的具有世界眼光和手腕的政治家集团,比之于十年前中法战争时的决策圈和激扬文字的“前清流”,并无大的长进,这就是翁同们的悲剧所在。且翁同为人尖刻,自视过高,难以与人共事。马关议和后,兵部尚书荣禄在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密函中说:
失鹤零丁(4)
常熟(翁同)奸滑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宁(孙毓汶),与合肥(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应公事争执。
岂堂堂中国,其欲送之合肥、常熟二子手也。荣禄的话,显然带有他对翁同的个人成见,但也从一种侧面显示出当时高层官员对翁的看法。而“清流”前辈,此时闲赋在福州老家的陈宝琛,也在一首题为《感春》的诗中,含蓄地批评道:
一春无日可开眉,未及飞红已暗悲。
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幡连。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四
翁同无疑是爱国者。但在当时,最保守最迂阔的顽固派,其内心深处难道不也是充满忠君爱国情结的吗?至1894年年底,朝廷对军事局势已陷绝望,决定派张荫桓、邵友廉赴日议和。12月28日,“后清流”健将、御史安维峻不顾个人安危,上疏请诛李鸿章。奏称:
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以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贼之来,以实其言。
又说市井传闻“和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这篇奏疏攻击李鸿章,内容虽然多不切实,但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李误国的强烈不满。尤其把锋芒直指慈禧太后,说出了政界最为忌讳的内幕,堪称“后清流”的绝唱。但细想,又属与事无益,大可不必。但比翁同的另一位门生,吏部侍郎汪鸣銮攻击“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哉”的立论总算高明。安维峻的这番高论,使得怯懦的皇帝感到震骇和忧惧,决定将他拿交刑部治罪,经翁同极力劝说,改为革职发军台效力。据说恭亲王奕当日病假,不在军机。假满入值,指斥同人说:“此等奏折,归档了事,何必理他?诸公是否欲成此人之名?”而安维峻确也载名而去,“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著名镖师,北京源顺镖局掌柜大刀王五还亲自为他护驾,陪同前往戍所张家口,“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可见清议的社会声望和市场价格——刚直与爱国也是可以名利双收的。 翁同此时百感交集,又无能为力,恰好次日家中所畜一鹤飞失,特仿后汉戴良《失父零丁》帖,作《失鹤零丁》。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事简,闲步东院,一鹤既去,因作零丁帖求之。得于海岱门外人家,白金八两赎归。” 曾朴小说《孽海花》第二十五回,说章直蜚、闻韵高(即张謇、文廷式) “出了十刹海酒楼,同上了车,一路向东城而来,才过了东单牌楼,下了甬道,正想进二条胡同的口子,……忽望见口子外,团团围着一群人,都仰着头向墙上看,只认做厅的告示,不经意的微微回着头,陡觉得那告示有些特别,不是楷书,是隶书,忙叫赶车儿勒住车缰,定睛一认,只见那纸上横写着四个大字:‘失鹤零丁’。”讲的就是这事。书中还收录了“失鹤零丁”的文字:敬白诸君行路者,敢告我昨得奇梦。梦见东天起长虹,长虹绕屋变黑蛇,口吞我鹤甘如蔗,醒来风狂吼猛虎,鹤篱吹倒鹤飞去。失鹤应梦疑不祥,凝望辽东心惨伤!诸君如能代寻访,访着我当赠金偿。请为诸君说鹤状:我鹤蹁跹白逾雪,玄裳丹顶脚三截。请复重陈其身躯:比天鹅略大,比鸵鸟不如,立时连头三尺余。请复重陈其神气:昂头侧目睨云际,俯视群鸡如蚂蚁,九皋清唳触天忌。诸君如能还我鹤,白金十两无扣剥;倘若知风报消息,半数相酬休嫌薄。无疑,翁同在文中流露出他对辽东战场清军失利的关切,但这毕竟是访鹤的游戏文字,以翁同地位之尊,在国势危急之际,不在军机处谋划补救,却用街头大字报的形式来抒发情感,还是太戏剧化了些。所以《孽海花》中的闻韵高叹道:“当此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老夫子系天下人望,我倒可惜他多此闲情逸致!”更有人作对联讽刺说:
翁叔平两番访鹤;
吴清卿一味吹牛。
完全把他同“前清流”大将,时任湖南巡抚,自请出征辽东,得翁支持,带着大批金石字画和一枚“度辽将军”汉印上前线,又在田庄台大败而逃的吴大一块儿嘲笑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第一乐章,是仿效器物层面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提议者为林则徐、魏源,推行者为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一线工作的地方领导人,具体操作者多为捐纳出身的商人买办。中枢虽有慈禧太后、奕的支持,却未得到上层知识分子的关怀,甚至为羽毛洁白的士大夫所不齿。这就造成新旧嬗递的年代,思想界与操作层的完全断裂。激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大谈经世致用,其实也不过是清谈而已。实在说来,仅凭嘴上 “爱国”,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国平天下,确是于事无补。但仅重视器物层面的变革,而不注重人格精神的培养,依然驱使不了器物。在洋务官员和清流士大夫这样两大对垒阵营的折冲较量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后知后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负面影响显然更大。 从小在欧洲留学,精通多种外语,又在张之洞身边做了约二十年幕僚,被认为是清末民初有名“怪人”的辜鸿铭,1910年用英语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逸事》(The Story of A China Oxford Movement)。他在书中将“清流”比作19世纪30年代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发起的反对宗教中的新教倾向、主张恢复天主教思想和惯例的 “牛津运动”,称其为传统的儒学反对西方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保守主义思潮,宗旨是“号召全国遵照孔子的教义生活得更为严格”。尽管他将北京的翰林院比作牛津大学有点儿不伦不类,但他在宣统二年即对“清流”进行中外文化学上的比较研究,还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他坦承“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反对李鸿章——中国的帕莫斯顿勋爵”,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清流”,“是我们队伍中唯一的仍然绝对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人,相信中国的文明会战胜欧洲的进步和新知思想。”这就把“清流”的指导思想和局限性概括得十分明确了。在“清流”大盛的年代,辜鸿铭其实并未被人当作“清流”,但到1928年,他在北京大学做教授,依然拖着细细的辫子,倒使人对这位老夫子刮目相看。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失鹤零丁(5)
五
翁同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谜,是他的突然从政坛上被开缺。甲午战败对翁同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其后,他参与了总理衙门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交涉,再一次看清了弱国无外交的悲剧,这促使他鼓动皇帝变法。他以师傅的身份向皇帝举荐了康有为。到了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之风在北京极为盛行。康有为的主张颇得皇帝的欣赏。然而,就在皇帝准备摁动变法的按钮时,翁同却与皇帝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冲突。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么件事:
5月26日,皇帝向他索取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翁答:“与康不往来。”又说“此人居心叵测”。皇帝问:“前此为何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次日,皇帝再一次问起了康有为的书,翁同又如昨天一般作了回答。皇帝当即发脾气了。翁同说:“可以传总理衙门通知康进书。”皇帝不同意,“发怒诘责”,要翁告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传知康有为。翁又说:“张荫桓天天觐见,皇帝可以面谕。”皇帝仍不同意,翁同只得在召见结束后传知张荫桓。翁同与康有为的关系,我们现在所知的,一方面是翁同日记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康有为梁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