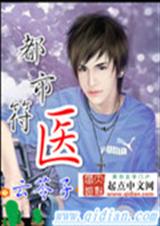都市红男绿女的情欲陷阱 全本 万云-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曾存在于稻田
我曾是蝴蝶或水仙
那一刻他被震撼了。诗的后面署名杜蔻。“豆蔻年华”,名字都透着美好。他发誓要认识这个名字后面的人,预感自己跟这个字体娟秀的女孩会有故事发生。经过打听,他很快就认识了那个瘦小但五官精致的女孩子。
操场边那棵大大的木棉树正开着红硕的花朵。幸好有木棉花,广州的春天才有那么点春天的意思。树下,他跟她第一次约会。那时候他感觉真幸福。她同意试着接纳他。他牵着她的手,绕着校园一圈又一圈,从日出走到日落,走到深夜。走了三年。有一天,走到一个围墙的缺口时他抱住了她,撬开她封闭的嘴唇。他解开她上衣的扣子,亲着她小小的结实的乳房,左边右边左边右边……
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狂热地喜欢上她。他是温暖的向日葵,跟着太阳快乐地旋转;她是掉进古井中的月亮,幽深阴冷地发着荧光。他们根本来自不同的两个世界。他的父亲是一个快乐的邮递员,是远近出名的孩子王,自行车后面常跟着一堆打闹追逐的小孩子。母亲在银行上班,家里总是飘着她开朗的笑声和有些走调的小曲。他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到大,就算有烦恼,也只是偶尔尝了一下糖,觉得不如蜜那么甜。而杜蔻,虽然她很少提及自己的家庭,从她只言片语中,还有她的老乡那里,他也基本知道了她的故事。
她的母亲是一个懦弱而暴躁的农村妇女。懦弱是针对她父亲,暴躁是针对所有其他人:情敌、邻居、村民,包括她唯一的女儿。她父亲是水果商人,在他发财之前,就跟村里好几个女人有染,常常是她母亲在地头井边找那些女人疯狂撒泼,互相撕扯头发、吐口水,然后自己的男人闻讯赶去,将她打得头破血流拖回家。她父亲的生意做开后,因为水果的地方性和季节性,开始整月整月地不回家,谁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他或许也给过家里一些钱,因为那两年她家买了很大一块地基,建了一栋二层的小楼,还有宽阔的后院。房子框架刚搭好,突然间又停下来,十来年再没有装修。她妈在没有装玻璃的窗上钉上了厚塑料膜,母女俩的日子就这么惨淡地过下去,父亲再没有回来过。
其实在小楼建成之初,她父亲还回来过一次。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家,还带了一个把头发烫成鸡窝的女人。她们家只有两张床,一张是杜蔻破旧的小木板床,另一张是她父母的。那些天那个女人一直住她们家,谁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后来终于有一天,她妈趁着他们外出,将那女人所有衣物、行李全堆到门口一把火烧了。那个女人又哭又叫,朝她父亲叫嚣着没离婚别去找她,气急败坏地走了。她妈自然又得到她父亲的一顿好打。这之后他再没回来了。
知道她的故事后,他胸中更多了爱怜。她偎在他怀里像一只被收留的流浪狗,常常没来由地抖动或低沉的呜咽一声。而且,她总是做噩梦,总是叫喊着救命把自己吓醒。她的室友对她颇有微词,常有人建议她去吃些治忧郁症的非处方药,实在排斥药物的话就多吃甜食:水果、巧克力、牛奶什么的。他从不相信她是不正常的,她只是缺少爱护而已。于是他在校外找了房子,每晚抱着她睡,她受到惊吓时,他把手掌摊开到最大,紧紧贴着她的背,告诉她有他在,不怕。那时他还只是学生,房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同时带了三份家教。后来他甚至觉得,他们的结合中,怜比爱更多一些。她永远是需要他照顾的对象。
他永远都忘不了第一次做爱的时候――那是他的第一次,也是她的第一次,卸去所有的包装,赤裸的他趴在赤裸的她身上,手盖着她的手,脚覆着她的脚,肚子压着她的腰。从此,他们是完全咬合的一对齿轮。却突然有那么一天,她偏离了他们共同的轨道,说她爱上一个谋面一次的网友,然后,她不辞而别。
循着她的通话记录,他很容易地发现了那个“上海网友”就是他的上司陈优。她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行迹,上海网友的故事,只是他们对外一致使用的“官方口径”。他甚至有些感谢她编的这个貌似离奇的故事,不然他那颗连呼吸都会疼的心,怎么有能力去应付熟人们的好奇。
接到杜蔻电话的那天晚上,他像被一把钢刀插进心脏,刺过脊梁,死死地钉在床上不能动弹。正好有朋友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女朋友跟别人跑了。朋友说,好事嘛!还没结婚嘛!这时候发现她是这样的女人,真及时!他忍着疼痛,像对方的回音壁一样喃喃地说,是啊,好事,没结婚,及时。朋友又说,你也不爱她嘛,表现得这么平静!过来,一块喝酒吧!他答应着,要翻身下床,却一脚踩空,结结实实地摔到地上。
可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再去找她。像她这样的女人,离开了就是离开了,不爱了就是不爱了,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只有两个面,不是正就是反,没有任何余地。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锁起了他们一起住过的房子,尘封了他们爱过的痕迹。还有,他爱上了唐沁甜公司附近的那个绿茵阁。坐在那里靠窗口的位置,运气好的时候就能看到,曾经的女友从门前走过去――她新租的房子就在这附近。
如果能看见她,就是那天绿茵阁为他上了免费的甜点。
他知道她过得不好。
因为爱上陈优的女人,没有一个能活得漂亮。
找了两个民工,花了四十元钱才把箱子弄到九楼。杜蔻不想那两个穿着肮脏衣服不刮胡子的民工踏进自己的小窝,在门口就付清了钱。
家里刚刚打扫过,简直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杜蔻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李遇柳那里取回这么一大箱沾满灰尘的东西。这只是一箱她想要丢掉的过去。李遇柳现在的那个女朋友好像……不管怎样,她比自己更爱他。她已经不配再对他提这个“爱”字了。
轻轻地打开箱子,一股灰尘扑面而来。她取出那个长长的盒子,那只成了肉干的手狰狞地抓在那里……来呀!她心里说,你不是总在梦里捏我的脖子吗,你不是说饶不了我吗?我活着,而你,只是一个死人。你对我没有办法了!她找来一只铁盆,将它扔进去,连着那些旧衣服。我要送你走了,她说。
她实在没办法向任何一个人诉说,这只胳膊不是教研室偷来的标本。那是她父亲的手。那只将她母亲往死里打的手,那只临死前恶狠狠地抓过来的手,那只挥舞在她每个噩梦里的手。
她永远不想回忆那被人指指点点的童年。父亲甚至在医院割痔疮时,都能利用短短的两天住院时间勾引上女人。他游手好闲,暴戾无常,可是他长着一副讨女人喜欢的面孔和讨女人喜欢的嘴。他将外婆给母亲的唯一嫁妆――两块银元偷了出去,给情人打了一条银项链。母亲的哭骂只是使得他将母亲一头按到满满的水缸里。要不是她大哭大叫喊来邻人,母亲那一次一定呛死了。从小到大,她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殴打,她看见他将母亲扯着头发拖到猪圈里,她看见他嫌菜太咸了抓起碗就朝母亲砸过去……有人说,世上是有神灵的,那时她总是跑到村里的祠堂去(那里摆着所有人家的祖宗牌位),求神灵保佑他死,让他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
后来他开始在外面做水果生意。她以为新的日子要开始了,因为常常可以整月整月地不用见他了。而他也给了母亲一些钱,让母亲张罗盖房子。房子快盖好的时候他回来了,带回一个流里流气的女人。母亲迟迟疑疑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付,到了睡觉的时候终于爆发了:那个女人爬到大床上,跟父亲母亲睡在一起!当然,母亲的反抗引来的又是一顿暴打。
她躲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软塑料鞋底抽打在皮肉上的声音,还有母亲的呜咽。那些日子里,母亲白天青紫着眼睛进进出出,晚上家里就开始上演着最无耻的戏。她在黑暗里抠着自己的大腿,强迫自己不要哭出声音。那年她十四岁,读初二。
新房子的地基下有一窝很肥的老鼠。她奉母亲之命买了一大包老鼠药。只一夜工夫,第二天洗脸架下、水缸脚下、床底下,到处躺着硕大无比的老鼠。
这剧毒的老鼠药,她不止买了一包。她甚至知道,十六周岁以下杀人不会负刑事责任。她犹豫着要不要下手。她从来都是聪明的、优秀的,年年成绩都名列前茅,这也是父亲乖张成性却从未动她一根手指的原因。曾听说他在外面夸耀自己娶了一个愚蠢的老婆但女儿还是只遗传了他的聪明。虽然他将女儿像狗一样养大,不抱她不背她不说一句柔软一点的话,但也从不打骂她。
直到突然有一天,母亲歇斯底里喊着“我不活了,我跟她拼了”,把那个女人的所有东西堆到门口一把火烧了。当然傍晚又是一阵哭闹,两个女人一个喊着“你这个骚货”,一个喊着“你这个烂货”扭成一团。然后父亲回来了,那个女人越发得势,哭闹着“不离婚别来找我”冲了出去。
那晚她以为母亲要死了。门上,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母亲的血。派出所的人对于她家的武装斗争,早就习以为常了。从前也有几次母亲在娘家人的帮助下将父亲扭到派出所的经历,结果只是回家后被父亲更凶狠地殴打。提出离婚也要打。反抗更要打。更糟糕的是,她们家的新房因为按父亲的要求“离公路近”,所以远离了村庄,喊不来人劝和、帮忙。不过就算是从前处于村庄中央,也不会再有人来劝阻了。十几年了,别人都被闹烦了。
杜蔻站在饭桌的后面,漠然地看着做着大幅度武打动作的男人投在墙上夸张的影子,那个魔鬼,像踢打一条狗一样,嘴里念念有词。她表情冷漠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拉开饭桌抽屉,当着他的面(当然他没空看),将两大包老鼠药拌进绿豆粥里。
打累了,他开始补充体力。他第一个捧起的就是那碗因为毒药太多颜色都变了的绿豆粥,但他没在意。他从来没想过他这种风流的人物会在这一刻死,以这种方式死。他原来的设想是死在某个细腰的女人身上,死于马上风。他三两口喝掉整碗粥,然后将筷子伸向炒鸡蛋,唯一的一碟菜。他把鸡蛋全吃完,脸色就开始变白,大滴大滴的汗掉下来。可以说,他其实还算条汉子的,他是个孤儿,九岁就开始上山背石头养活自己,手指头被轧石机砸断半根都没掉一粒眼泪,因为他早就习惯了伤痛和哭喊都没有人关心。他用残缺的手指指着躺在地上哭的那个女人“你……”然后,他倒了下去,眼睛终于转向了站在桌边那个冷漠的孩子。
“是你……”他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快……送我去医院!快!”他这个时候还带着命令。
母亲从地上爬进来,惊愕地望着用手臂紧紧抵压肚子、疼得龇牙咧嘴的男人。她一坐起来,鼻血马上就像簇拥而出的血蚂蟥,噼里啪啦地一条条掉到地上。
他用手抠住喉咙,想让自己将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可是无效。然后他又开始了哀求:“你们要抢救啊,要救我啊!”可是母女俩神情木然地站着,木然地看着他,像看着一只毒发的老鼠。
终于明白求救无效后,他开始向门爬去。门外四百米是公路,虽然天色已晚,又不是主干线,但偶尔会有车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