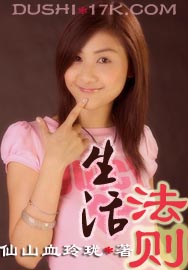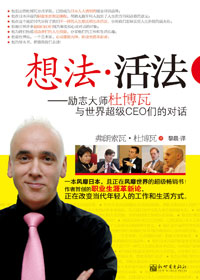活法-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王志提出的那些应该提到“点”而实际上又没有提到的“点”,再经过耿主编的旁敲侧击、适当补充,大多会让策划案的作者产生幡然醒悟之感,接下来虚心求教,从善如流,像海绵一样吸取对节目有益的营养,其他同事也不吝惜自己的观点,纷纷献计献策,希望能够帮他一把。这时,一个栏目组都在为一个节目贡献自己的力量,也许微不足道,但那种气氛让人感觉到所有的力量都拧在一起,向着一个方向努力,不达到一定的深度才怪呢。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面对面》序:在路上(3)
采访是整个工作流程中的重头戏,如果将《面对面》的采访比作是挖金矿,王志就是这个辛勤的矿工。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们,采访是一个很累人的体力活,这话不好理解,王志采访就是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地提问,这有什么累人的。电影《手机》里提到过一件事,当时电影的男主角严守一出席一本新书的发布会,他说原始的时候没有出现语言,人不会用语言来交流,要表达一个什么事情,只能手舞足蹈,既费时间又累人。王志采访的时候也有手势,但绝对称不上手舞足蹈,按理说不会累。但如果你这样表示出疑问,王志会看着你,很认真地说,那你来试试。
《面对面》节目的深度取决于王志提问的深度,如果某一个问题,王志问到了,那很好,编导在编节目的过程中就不会为缺少某一个部分内容而担心; 如果某一个问题没有问到,或者提到了但没有追问下去,那很难办,编导可能在节目中就要舍弃一部分内容了。每一次提问都是一次有力地挖掘,王志是训练有素的挖矿工,还在《新闻调查》当记者的时候,他的采访就得到了同事张洁的称赞,张洁现在是《新闻调查》的制片人,他说王志的采访有一个特点,告诉你吧,我不相信,要我相信,你就得经得起我的挑剔。曾经在一份编导提纲里,他提出来跟王志商量的问题大概20多个,但是采访一个半小时当中王志提出的问题是88个。
完成一期《面对面》的节目,王志需要提出多少个问题,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王志在采访过程中的提问必需能够支撑起一期四十分钟的节目,为此,他一直要沿着矿脉挖掘,目的是为了挖出金子。挖掘的过程是艰苦的,矿工必须确保始终在沿着主矿脉掘进,而且有的地方要仔细地掘进,否则就可能错过挖到金子的机会,这就跟编导熬夜、主编失眠一样,为了深度,记者必须要付出劳动,感到累人是自然的。闲聊开玩笑的时候,王志表示如果可以躺着采访的话,他很想躺着采访,耿主编也表示如果可以躺着开策划会的话,他很希望能够躺着开策划会,编导们凑热闹地表示如果可以躺着编片子的话,他们也很想躺着编片子。但是这种让人愉悦的精神假想仅限于玩笑,一旦涉及到节目,每一个人都会谨慎行事,形成节目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分裂”。
接下来由负责一期节目的编导拿出节目台本,记者采访结束,编导首先将节目文本写出来,这是一个“纸编”的过程,“纸编”是相对于在电视编辑设备上编片子而言,介质不同而已。台本出来后,首先交给主编审阅,台本一般都会经主编修改后再送到台里,而修改的次数视改稿后的效果而定,少则二三遍,多则五六遍,或者七八遍。
如果一个台本要经过多次修改,主编在编导心目中,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把关人,编导一边拿着被责令重新修改的稿子,一边想稿子怎么样才能让主编满意,间或想一想主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但耿主编对待任何人都一样,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语气温和,言之有物,每次都是对照稿子,一条一条地说,大到主题的挖掘、节目深度的体现,小到语言的顺畅、解说与采访的衔接,最终追求的目标还是“深入浅出”,让观众对节目感兴趣,又能从中获得有用的东西。
经过主编的修改之后,文本送到台里再审,现在负责审阅《面对面》稿件是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冰川,经过他的审阅之后,文本又会有一些修改,孙总用铅笔将修改的地方标示出来,让编导意识到文本中存在的瑕疵,再继续对其进行修改。
编导将按照最后审定的文本来编片子,其他栏目的电视人觉得做《面对面》的片子很简单,解说加采访,解说部分的画面不多,大段大段的对话又很好剪,基本上属于简单的技术活。这话传到《面对面》编导的耳朵里,他们反应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容易,你来试试。《面对面》的形态并不复杂,但编《面对面》的片子绝对不是按照文本上的句子来剪切、粘贴,或者根据解说贴画面。如何在编片子的时候保证对话时的自然状态,比如对话时语气的衔接; 如何让采访与解说的配合自然顺畅; 如何让画面传递出更加丰富的信息,《面对面》虽然不以画面取胜,但决不意味着不讲究画面的质量,这些都是编导要考虑,并且逐个解决的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编导才会觉得这将是一期有意思而且好看的节目,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
非线制作,编导将片子在对编机上编完之后,将节目素材上载到非线制作系统上,这个时候《面对面》的技术合成将和编导一起完成整个节目的制作过程,这个过程能是由数不清的修改所组成的,有编导自己的修改,有主编审片之后的修改意见,特别节目还有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审看后提出的修改意见,从节目素材上载开始,技术合成和编导就开始了修改之旅,直到节目可以下载到节目的播出带,才算熬到了头。节目播出了,并不意味着结束,接下来还有节目的评议会,收视率的公布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又开始报新的选题了,关于节目深度的技术操练还将继续。
春树:北京娃娃(1)
春树,北京人,1983年出生
2000年高中二年级时辍学,开始自由写作
2002年出版首部半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
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长达半天的欢乐》
王 志:你每次采访以前都提出要见一面。
春 树:才不是呢,我觉得这样特别浪费时间。而且我也不愿意跟人面对面的采访,我宁可他们给我发邮件之类的。
王 志:你会提很多条件,这个问题不能问,这个内容最好不要问,采访以前我们见一次面。
春 树: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嘛,而且这是说明我对你们节目的重视。
王 志:如果是真的问了你那些问题,你会真的跳起来走吗?
春 树:那肯定不会,我从来都不会,我肯定会说完所有的话,表达所有的,然后反败为胜再走。
王 志: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接受我们的采访呢?
春 树:《面对面》很有名啊。
王 志:有名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春 树: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应该接受采访,我有一种直觉应该接受。可以有好多人看到我吧。
春树受到公众的关注是因为她的小说。2002年,春树的小说《北京娃娃》出版。这部被称为是中国当代第一部以“残酷青春”为主题的小说,在文学界和教育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已经被译成十多国文字,在欧美和港台等地出版。2003年,春树的第二部小说《长达半天的欢乐》面世。
这两部小说以主人公自述的形式,讲述了春树从14到18岁间的生活经历。记叙了处在城市生活边缘的一群少年和他们脱离主流教育、喜爱诗歌和摇滚乐、经济困窘,在理想、情感、传统和欲望之间矛盾抉择的生活状态。
王 志:看过你的《北京娃娃》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印象,你中间所写的生活不是浪漫的,你自己用了一个词叫残酷的青春,而且我们的感觉是它现实得让我们有点儿吃惊。
春 树:残酷青春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为了宣传这本书提出来的,我当时也不喜欢这个词,但是我现在觉得也无所谓,只是一个词,是够残酷的,什么青春都够残酷的。但是我觉得我在当时退了学,辞了工作,乐队解散,恋爱失败,开始每天写小说,没有任何钱,在家里拿笔写小说,等了一年时间,换了十家出版社出版,这个过程实在是太超现实了,它是极其现实又不现实的,它居然实现了,最后这本书居然真的火了。
王 志: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发泄?
春 树:发泄也是一种,还有就是表达,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想法。仅仅是表达。像《北京娃娃》引起这么多争论说明它有一定典型性意义,现在那种叛逆、另类的青少年为数还是不少,有很多,而且它写了很多青春期的躁动、反叛,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
王 志:在你所谈到你的生活里面,大家看不到责任这两个字,只有你个人的喜好。
春 树:我只有对自己负责,他们为我做了什么,他们什么也没有为我们做,我为什么要为他负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喜欢的一个乐队,那个人也这么问他,你们为别人负责了吗?那个人就这么说的。
王 志:当有一天你长大之后,当你有一天成熟起来之后,大家会担心都是你这样的生活方式,都是你这样的观念。
春 树:你的意思是这个社会都应该是由什么样的人。
王 志:有责任的人。
春 树:然后?
王 志:对社会负责任,对自己也负责任。
春 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你说的这样的人。
王 志:没看出来。
春 树:好吧,我告诉你,拿我来说,如果我不写这本书,就是我对自己、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我要说出我的观念,是对社会的一种负责。
王 志:很多家长看了你写的书以后,他们也没有觉得春树是一个好人。
春 树:我不需要他们这么来认为,我只希望他们看到其中说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发生。《北京娃娃》整本书我认为是个悲剧,不是说我,是说那本书里写的那一段经历是个悲剧,我希望不要再发生那样的悲剧。
王 志:它的社会作用可能是负面的?
春 树:但是你没有看到正面作用吗。让我来告诉你,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我得到了安慰,我得到了理解,原来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样痛苦,原来她也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理解。他们看到了他们,他们也在经历的那种残酷青春。
王 志:有什么残酷的?你的青春有什么残酷的,能告诉我吗?
春 树:这是在那段最容易冲动的年龄,我们的思想还很混沌,而我们清醒起来,青春已经逝去,这就是残酷。
春树的作品让她成为“80后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谓“80后一代”指的是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在春树的书里,她和一些80后的朋友,有着不同于长辈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他们在互联网络上生存、结交,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行为规则,沟通着彼此关于生活、社会、友谊和爱情的观念。
王 志:你们标榜是80年代后,我们觉得这种年龄的差距并不能成为划分一群人的一种标准?
。。
春树:北京娃娃(2)
春 树:也不是我们标榜的,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提起80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