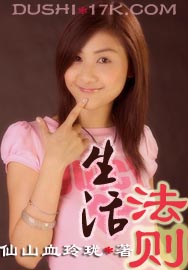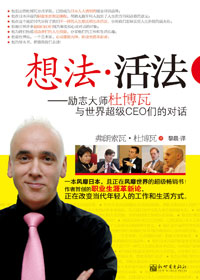活法-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面对面》序:在路上(1)
序:在路上
《面对面》栏目组
2003年1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团队——《面对面》,如今《面对面》已经走过了三年多的发展历程,此丛书记录的正是《面对面》栏目在成长道路上留下的足迹。
翻开丛书,每一个采访人物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一段难忘的经历,一种鲜明的个性,从他们的身上,您可以读到与我们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的无数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有的略显沉重,如“反腐败”,“防治艾滋病”,“打击毒品”; 有的轻松愉快,如“个性”、“青春”、“知名度”;但有了具体生动的人物作为这些关键词的注脚,有了王志对每一个关键词的深入探究,这些关键词都具有了深度新闻报道的分量和闪烁其中的人性光芒。在您翻开丛书点击这些关键词之前,不妨先认识一下《面对面》,了解一下《面对面》节目制作的大致流程。
《面对面》是一个新闻人物专访节目,新闻人物代表着“一面”,王志则代表着“另一面”,而且对于《面对面》的栏目来说,王志是不可或缺的“另一面”。有时在节目的评议会上,有的编导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说《面对面》的节目就分为两类,一类是观众想看某个新闻人物,一类是观众想看王志,就看王志怎么提问。
王志的提问让大家觉得最精彩的地方是质疑,质疑为什么会成为王志采访的风格, 2004年沈冰对王志的一次采访中专门就这一点提出了问题:
沈冰:质疑,很多人都说,尤其是我们的同行都会说,这是记者应该有的素质,但是现在大家一提到王志就觉得是质疑的典范。
王志:质疑是我的一种追求,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大家都可以用。
沈冰:大家通过你的节目,都有这儿一个猜测,王志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多疑的人,是吗?
王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不是一个多疑的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人家说主持人是话唠,我生活中间话很少的,我有时候是强迫自己说话,因为你要不停地说,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节目中间,我提的问题是很短的,我的话是很少的,能够不说我尽量不说。
沈冰:但一定要问。
王志:但是我一定要想。
沈冰:那你不觉得你活得太累了吗?对任何事情都要质疑?
王志:这是一种习惯,不累。我一天到晚不想问题,我不问为什么你就不累了吗?别人会认为你是个傻子,尤其是当记者的你要去告诉人家道理,你要去把人家看不到的东西展示给大家,你这点脑子都没有,你能当一个合格的记者吗?
沈冰:但是质疑它是一个万能的钥匙,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王志:质疑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态度,但是它更是一种手段,它把这两个点联系起来,把这个过程充分地展示给你,那你不解决观众这些心目中的疑问,那不就像过去唱那首歌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怎么个好法呢?正常人会这么说吗?但是那个年代不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我喜欢从常识出发。
沈冰:什么叫常识?
王志:这个概念解释起来是很难的。
沈冰:我想知道在王志眼中的常识是什么?
王志:比方说观众看到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这些常识就是说沈冰你来采访我,你是自愿的吗?还是领导的安排?这就是常识。不要先入为主,这是记者的大忌。只有通过这种质疑的方式,只有你从反面,用排除法把你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之后,我才敢相信这个天是蓝的,我才敢相信这个终点它是真实的。
探寻事实真相是记者的职责,而质疑是探寻真相时最有力的武器,有人把王志的采访比作是外科大夫式的,像在做解剖,一层层地解剖下去,直到发现事实的真相,不过王志本人更喜欢将自己的采访比作是剥洋葱,剥洋葱时会有一种强烈的刺激,甚至会让人流泪。
这种刺激不是新闻学强调客观、公正时的一本正经,不是循规蹈矩,反而有点类似于剑走偏锋,不按常理出招。当人们都在使用一种方式采访的时候(这种方式通常四平八稳),王志使用了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与众不同,而方式上的差异首先就造就了很强的形式感,而电视又是形式感很强的媒介。
《面对面》是人物专访,访谈占据了节目的大部分内容,记者与新闻人物两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交谈,用纯粹的语言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如果没有一定的刺激性,仅依靠谈话的内容根本无法达到理想的收视效果。但是质疑可以制造出谈话中的对立,让双方的观点发生碰撞,产生出一种戏剧性的效果,这样传播的效果会更好,观众也更容易接受。王志曾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质疑在访谈中发挥的作用,质疑就是将黑白两色放在一起,有了黑色的衬托,白色会显得更加白,如果你想突出白色,这种方式简单明了又十分有效。
电视是一个家用媒体,也是一个娱乐化的媒体,当人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想得到的是放松或者趣味。但很多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不明白这一点,因此很多时候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制作得这么好,而观众却不买我的账?节目的收视率就是上不去。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节目制作者把自己认为好的,强加给了观众。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站在观众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如果他们想更加轻松地了解信息,那么就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告诉他们信息,而质疑也就是一种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娱乐化的手段,质疑让《面对面》这档新闻人物专访节目有了娱乐性。
《面对面》序:在路上(2)
新闻并不等于娱乐,但新闻并不拒绝娱乐性,《面对面》也需要娱乐性的东西将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看完一个长度有40分钟的节目。新闻与娱乐又是一对矛盾,就好像前面提到了,质疑是新闻记者的职责,这是人们听起来就会感觉到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而到后面,质疑又成为一种形式感很强的东西,一种娱乐化的手段,听起来似乎已经远离了严肃的话题,但事实上质疑的确就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它的价值也就体现在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而王志懂得如何去把握这样的矛盾,并在《面对面》中使用到极致。
质疑是王志提问时的一种状态,但并不代表他提问时的全部状态,面对强势人物、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时,王志质疑的风格会显得更加鲜明,不过出现在《面对面》的人物并非都是强势人物或争议性的人物,因此,也并不是所有《面对面》节目都会去追求质疑,或者刻意要质疑什么,这个观点耿主编曾经反复强调,人有无限种可能,一个新闻人物专访节目的风格也有无限种可能。
王志的采访会因人而异,质疑只是他采访风格的一个方面,并不代表全部,王志有时候将质疑视为一种手段,他更看重和采访对象之间的交流,王志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最远的和最近的都是心的距离,《面对面》连接心与心的直线距离。”
一个新闻人物,他可能会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新闻人物节目中,但他出现在《面对面》的效果会不一样,原因何在?如果一个新闻人物是一个丰富的新闻矿藏,有的栏目来挖,可能挖了几下,挖到了几块金子就走了,但是《面对面》来挖的时候,会沿着新闻的主矿脉一直往下挖,直到将所有的金子都挖出来为止。《面对面》的编导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会追求一种感觉,如果某一个新闻事件中的人物被《面对面》报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这一个新闻事件上,其他新闻媒体无法超越我们的报道,深度成为《面对面》栏目里每一个人都追求的报道效果,而且“深度”已经如此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意识。
但电视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肤浅”的媒体,不少学者甚至喊出了“拒绝电视”的口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深度孜孜以求呢?如果一定要给电视的深度找出一个理由的话,责任是最好的理由。电视目前仍然是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古人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 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一个人在电视上说话的效果就如同一个人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传播面广了,影响力大了,不能不讲电视报道的责任,不能不追求电视报道的深度。电视机作为最大众化的消费品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即使是高学历的人在家里也会搁上一台电视机,他可以不看电视,但是他不能阻挡电视介入他的生活,他可以不接受电视对他的影响,但是无法阻挡电视影响他身边的人,高学历的人即使是有意将电视排斥在外,也无法回避电视对他生活的渗透,强有力的渗透。现在的青少年看着电视长大,他们会模仿从电视里看到的东西,电视人身上的责任感更加重了,越发感到追求深度的重要,这可以视为电视人的责任情结。
对“深度”的思考,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面对面》每一个节目的具体运作过程可以说是将“深度”付诸实践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看上去只是一个个的技术环节,又像是产品生产的流水线,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但这个过程充满了希望、失望、选择、放弃、肯定、否定等诸多矛盾的因素,而且这一切都从选题开始。
选题是这个流程中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每周二是栏目组例行的报选题会,制片人王志、主编耿志民和编导们一起,商议下一阶段节目的选题,也会总结回顾上一阶段《面对面》选题的质量。由于《面对面》是人物专访节目,人物选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节目的质量,选题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样的人物可以进入《面对面》的问题,而这些人物会对《面对面》的定位、前进方向和影响力等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面对面》的定位是有影响力的新闻人物专访,但是如何界定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不容易,找到大家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更是难乎其难。因此每次报选题的时候,每个编导的表情是不一样的,有的显得胸有成竹,似乎手里已经有了几个不错的选题,只等到报题会开始就准备进行大力推荐; 有的编导看上去有些底气不足,尽量放低姿态,或迅速地在脑海里搜寻一遍,看看有没有遗漏合适的选题。选题报出来之后,大家会开始激烈地争论,这个人物是不是真的适合《面对面》,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对,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就在争论的过程当中,有关节目制作的思路也逐渐清晰。
策划是确定选题之后的第二步,《面对面》节目的策划大部分情况下是共同参与,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启发,相互交流。只要没有外出采访的任务,制片人王志都会参与策划会,他是记者,也是策划案的使用者,所有的策划案都要落到他的手里。读完策划案,王志都会有话要说,做得好的策划案自然提出表扬,然后一起大家讨论,看还有哪些点可以完善; 做得不好的策划案虽然不会遭致暴风骤雨般的批评,但王志提出的那些应该提到“点”而实际上又没有提到的“点”,再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