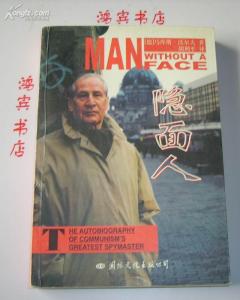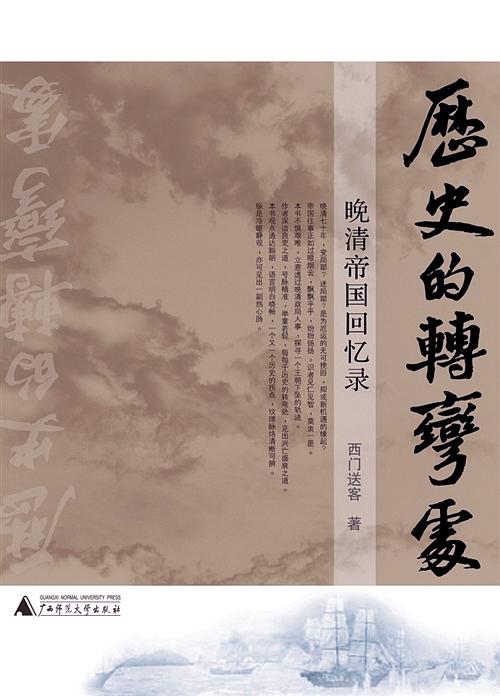靖任秋回忆录-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次约会,再加上后来在长官部的会面,我对袁都采取了不亲近的态度,侦查起了反证的作用。这之后他错误地认为他对我已??确切地了解了,认定我已??不是共产党了,才对我从怀疑转而采取相信的态度,才敢于向戴笠作保,并且在戴那里起了作用,采用升官许愿的办法对我进行收买,甚至也关系到我被捕后他们所以不能按共产党处理我的主要??因。这倒是我对他们应对的效果。我对岳也做了些工作,如请客吃饭,表示接近等,于是旧日关系可能就向好的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又??各种证明,他可能更加自信了。因此他对我的态度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二)以后知道我在洛阳被捕的同时,新五军在前方搜查我的住处,又在部队逮捕了几十个人,这肯定是孙殿英伙同特务严家诰主持干的。这说明孙殿英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变了。但是在我前方的住处也没搜查到什么我有关共产党的秘密,听说我的房东老太太连我的几本书也给收藏起了。党在我的组织关系问题上,布置是很周密的,我没有横的关系。在前方逮捕的这些人,有的不一定是共产党,总也会有共产党,但是在这些人中间,不会有一个人说出我是共产党的,因为我在新五军没有组织上的关系。连彭文过重庆去洛阳时,周恩来为了掩护我,都不让她带组织关系,只叫她到洛阳后和李锡九一人联系。这是正确的组织路线的胜利。因此他们的这一罪恶勾当,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又一次给我造成有利的作用。严家诰去重庆过洛阳的时间,在我被捕已有两三月之后,显然是在孙殿英部队完成这一罪恶勾当之后,是在前方搜查了我的住处,并逮捕了大批干部,审讯全未查出我有关共产党的材料之后,向重庆去汇报请功的。 对于我的情况,他们是一定要向戴笠反应的,这些事可能起到了实际作用。这两件事说明他们虽然认定我是共产党,但是毫无证据可言。从具体活动上,他们也很难对我进行追究,即以打朱怀冰为例,1940年邢肇棠跑了,我调重庆受训,我看基本是从这件事引起的。但是很微妙,??都不谈这个问题。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势必追究到孙殿英身上。他们顶多只能说我倾向共产党,对孙殿英起了影响作用,但是决定作为的还是孙殿英,孙不表态,我实际上也是不能自行决定的。这一点他们是能懂得的,所以他们不能对我进行追究,追究起来,我就要推到孙殿英身上,他们反倒不好办。我只能负这点责任。因为已??打响,仓促之间我在村外和他说了这句话,建议他走开,他不说别人不会知道,他说也说不出口。我在孙殿英那里的其他活动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他们对我的处理,一方面因为告发我的三条罪状缺乏事实,无所依据;再加在我被捕之前和之后,他们利用袁晓轩对我的侦查,搜查住所,在部队大批逮捕和审讯,毫无结果反而起了反证作用之后,无法肯定我是共产党,无法定罪;另一方面,即令如此,他们也并没有把我放过,依然对我不肯放手,仍然是长期监禁不放。而且我看对我的处理基本是在一战区解决的,因为转到西安以后,随即送到终南山脚的道峪监狱,再也无人过问。。 最好的txt下载网
狱中岁月(3)
在监部和政治部对于去看望的人都是有人监视的,去的人只是讲讲一般看望的话,有关案情的问题是不好讲的。岳烛远的情况不同。岳烛远在军法监部审问我以后,来拘留处看过我。这次见面他首先向我表示,他到南阳去了很久,最近才回来,逮捕我的事情他不知道。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以前熟人见面后的应付话。据解放后的文史资料了解,这次逮捕我的动力之一还有汤恩伯。据文强称,1941年*高潮期间,蒋鼎文初到一战区做司令长官,就和汤恩伯、胡宗南、戴笠商定对付*武装和地下组织的计划和布置,因而蒋到职不到两个月即逮捕了新五军副师长共产党员靖任秋云云(见《文史资料选??》第三十二??)。当时汤是一战区副司令,驻军正在南阳,岳是戴笠军统一战区的负责人,在戴笠和一战区合谋的活动中,不可能没有岳参加。岳烛远说的,逮捕我时他正在南阳,那就很有可能岳在南阳对我的问题和汤恩伯共同策划了的。当时我向岳表示,我这次是受了冤枉,孙加给我的三条罪名都不是事实,是没有根据的,首先我现在不是共产党,鼓动军队更没有事实,逗留不前更是笑话了,在我被捕前孙还有电报要我暂留洛阳可查,显然是陷害了。我当时要他帮忙,他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考虑这证明情况还不太糟,如果很严重,就是说他们已??掌握了什么材料,认定我是共产党,岳烛远就不敢去看我,要看我去就是收买或威胁、利诱。但是,岳烛远来看看我就走了,这可以供我揣测形势。
到1941年底,到了12月初的时候,就把我从军法监部拘留所转移往一战区政治部。从政治部的工作性质设想,很可能是到政治部解决“??有共产嫌疑”的问题,但是去政治部前和到政治部后,统没有人向我宣布去政治部的??因和到政治部以后要我做些什么,到政治部后我也只见到一位科长,这位科长什么也没和我谈过。这时政治部主任是陶峙岳。送我去时,有个带枪的兵押着,先到政治部办公处所在的一幢小楼去,在他们以外的院子里等着。以后出来一位主管我这案子的科长,瘦高个子,南方口音,瘦长脸,年近四十的样子。他们事先都是准备好了的,没有多讲什么,他便要一个警卫的宪兵排长把我带到和他们办公室对面的一处平房的地下室去看押。洛阳、西安有种地下室,类似窑洞的挖法,向地下挖很深,这里冬暖夏凉,有钱人家才能挖得起这种地下室。新五军洛阳办事处长王松筠的后院就有这种洞,可以避暑和防空。关的那间房子像是??来宪兵住的,两边摆四张床,以后这位排长和我一起住在这间房里,同住在这间房的记得还有一位。排长是北方人,河北口音,中等身材,只有三十以上年纪。科长把我交给宪兵时,同时叫他们给我送了一本三*义,一本建国大纲。我到那里,实在看不下去。看管我的宪兵排长也跟我住一间屋,他有好些小说,如三国、水浒,我便从排长那里借来天天看这些书。他们把我往这里一放又无人过问了,从我去到我离开,这位科长没有和我谈过有关我案情和思想的问题,政治部除看押我的一位宪兵排长外也只见过这位科长,再没有人和我谈过话,也没有受过审讯,这位科长和我见过两到三次面,统没有多讲话。家里可以去看,在一战区关着时,来人看还填会客单,在这里就到住的屋子里看。生活也不坏,每饭大概有一菜一汤,在送我去西安以前,由这位宪兵排长监视,出去洗过一次澡。可见形势对我还好。我当时想大概问题不像初来那时严重,他们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什么野蛮的刑讯,这与当时我还是一名国民党的少将副师长的身份有关,对有这样身份的人用刑,他们认为也不像话。但是,战区的执法总监部对犯人是用刑的。这以后我才第一次要彭文找皋海澜向这位科长说情。皋和我本来素不相识,但当时洛阳实在无人可托,利用皋是徐州濉宁县人,那时徐属八个县,在外称徐州同乡,皋当时是战区兵站总监,是一个旧军人,就以同乡关系去找他帮忙。以后皋回复说,那位科长说我看不起他,皋还推测说,是不是他想要点钱。我被捕后家中生活已很困难,更无钱送他,这件事就如此算了。
狱中岁月(4)
在政治部大约有一个月上下的时间。快到冬季,旧历十一二月了吧,岳烛远又去看我一趟,是那位科长送他去的,送到他就走了。岳烛远这次见面才说:这里反映,给你送三*义、建国大纲看,你不看,每天只看三国、水浒。岳说这话也不是认真怪我才说,只是随便说说。岳当时确实认为孙殿英有意加害于我,“*”中,他向专案人员说:“靖任秋是共产党员,我早就知道。”但在1941年见到我时他认为“新五军是戴笠向蒋介石担保成立的,内部有戴的军事特派员和随军调查人员,绝不会允许一个共产党员靖任秋充当他的师长”,“我断定他已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因此,我才敢于以黄埔同学的关系将靖介绍给戴笠,并请戴引见给蒋介石的”。岳还向专案人员说:“我感到孙殿英怕靖任秋走在他的前面(指1941年秋见戴见蒋),今后不仅不能为他所用,一旦发生事故,就有取而代之的危险,所以孙殿英才诬告靖任秋是共产党员”,“当时,我想孙殿英是个老狐狸,有意破坏军统局的威信,真是可恶已极”,“因而,我给了一个电报给戴笠,要求戴笠电请长官(指胡宗南)释放靖任秋????我又以全家性命保释靖任秋的函件,寄给胡宗南”。岳烛远因为当年有这些认识,所以才在这次来政治部关押我的地方看我。岳烛远也是在这次看我时告诉我说,最近要送我到西安去,他并诡称:你的问题到西安后就解决了。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并没有说明。实际无论是戴笠还是胡宗南都没有回答过他保我的函电。从岳烛远对我的谈话看,我到政治部以后的处理,岳烛远是参与了的。从他对我的讲话看,对他还不是不可以利用的,我大约是在这以后要彭文去找他设法营救的。
说到一战区政治部要把我解送到西安。我就做去西安的准备。
我的生日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就到了。加上,到西安看我就不这么方便,我生日那天,彭文搞了些菜,炖了鸡装在一个大瓦罐里送来,还把三个孩子都带上,大的伯文1931年生,刚刚10岁,二的玉仲只8岁,三的叔平就6岁多,她那时已??怀孕,大着肚子,就要生第四个孩子季洛。这天,她带孩子们来到我住的屋里,放下菜,我听见彭文对孩子们说:“你们开始????”起初我还不懂她说什么。见几个孩子听她说“你们开始????”就一齐跪下,给我磕头。彭文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不晓得你这次走,什么时候出得了监牢,让他们给你磕个头,记住你这个爸爸。”我听到这话,心里真是难过。这到底是生离死别吗?勉强忍住才没掉下眼泪。这个下跪磕头的告别,孩子们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磕头,实际上也是生离死别的一次(叔平附记:姐姐回忆,在去的路上,我们三个紧紧跟着走,路程很远,有十多里,天寒衣单,肚子也很饿,默默无声。妈妈说:“我们去看望爸爸,我们去给爸爸过生日,见了爸要给爸爸磕头。”????爸爸见孩子们都来了,很惊喜。待舅舅放下挑子,妈妈对我们说:“给爸爸过生日,你们开始吧!”我们三个就一齐跪下,趴在地上给爸爸磕头。妈妈站在一旁对爸爸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没有流眼泪,我们也没有哭,在那种时刻从没有见过妈妈流眼泪)。她要我给没出生的这个孩子留下个名字,靖季洛这个名字就是我和彭文分手时,在洛阳监狱里给留的名字。记得到西安道峪监狱后,做过一首打油诗:“洛阳抛妻子,长安作楚囚,重圆莺梦早,岁去春不留。”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