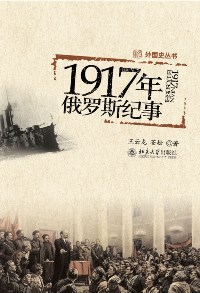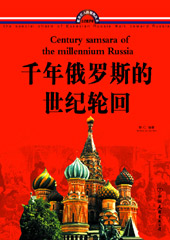从苏联到俄罗斯-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充满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当然,当时发表这类信不亚于给自己判死刑。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不过记录了过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对那些有意反思过去的人仍有裨益。被告律师没再发言。法庭判决利季娅胜诉,出版社应支付她全部稿酬。
前面说过,利季娅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打印了几份,在朋友当中传阅,但不知怎么被地下出版社印刷了,并很快流传到国外。但利季娅从未想在国外发表作品,她是为苏联读者写小说,希望小说帮助人民认识过去,反思过去。如人民都认清过去,那么过去很难重返。稍有重返的迹象,便会引起人民的警惕。然而自此,利季娅便成为作协的眼中钉,以后她所遭受的种种打击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1)
1965年开始了竭力遗忘个人迷信的后果并颂扬这一时期成绩的过程。所有出版物不再披露历史真相,采用逐渐减少最终缄口的手法。先披露一半,后披露四分之一,再后披露十分之一,最终什么也不披露了。新的一代对过去将一无所知,无法从父辈和祖辈的血迹中吸取任何教训。
请看1965年以后出版的书籍。
1965年,斯拉文出版了《肖像与札记》,其中谈到苏联驻法西斯意大利著名记者维克多·金:“在那些年代,金说过,他将活到人民起义绞死墨索里尼的那一天。金的预言实现了,但他没活到那一天。他无法预见自己出了骇人听闻的事。”作者没说出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金1937年被处决。1972年,发表了回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州第一书记贝塔尔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感人的话:“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纳尔奇克(州府)的街道上奔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奶奶们时常来到广场上贝塔尔的纪念碑前,望着贝塔尔的铜像抹眼泪。”作者应当告诉孩子们,爷爷奶奶之所以望着贝塔尔铜像落泪,是因为他们怀念这位1937年被处决的书记。是作者不敢写他被害还是编辑根据指示删去了?在1973年出版的由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巴赫金著的《诗学与文学史问题》一书中,序言是这样介绍作者生平的:“巴赫金出版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后便迁移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库斯塔奈市。”巴赫金为什么从资料丰富的列宁格勒迁往偏僻的小城库斯塔奈呢?难道那里反而比列宁格勒的研究条件更好?实际上,巴赫金因在研究中发表了独创见解而被流放到那里,作者不敢挑明。最可笑的是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介绍了。1973年,诗人文库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卷》,序言介绍了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平。他一会儿住在克里木,一会儿住在莫斯科,又住在彼得格勒,然后又回到克里木,接着又到第比里斯、埃里温、罗斯托夫、彼尔姆、阿布哈兹,最后来到沃罗涅日,创作道路至此中断。序言给读者的印象是曼德尔施塔姆酷爱旅行,像果戈理一样,只有在旅途中才有灵感,但序言偏偏漏掉曼德尔施塔姆旅行的终点海参崴。其实曼德尔施塔姆不是到各地旅行,而是被流放到各地,1938年病死在海参崴劳改营转运站。招致杀身之祸的是那首《我们活着,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这些序言,作者都只字不提。不掩饰他的生平,诗集便无法出版,这也算为出版诗集所付出的代价吧。
利季娅是苏联作家,也写过迎合政策的文章。她坦率承认:“说起来,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对每个人来说,总有一天真理会扼住他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灵魂。对我来说,这一天是在我亲爱的城市血流成河时来临的。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太晚了?当然晚了。农业集体化时我未睁开眼睛,但我一睁开眼睛便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我并非为了发表,只想记下丧失理智社会的一个方面。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我同很多人一样,萌生了发表的希望,但我的希望落空了。一旦我明白我国又开始剥夺记忆,我彻悟了:不论给我任何财富,我也决不出让我用痛苦酿造出来的成果。可以永远不印我写的一行字,就让我的创作构思永远无法实现。我也不允许从我著作中删除牺牲者的名字。”利季娅作出决定,但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不出书收不到稿费,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很多作家都作了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他们戏称这种让步为贴邮票,贴上邮票信才能邮走。利季娅也贴过邮票。1955年,她写过一篇评论日特科夫创作的文章《隐藏的遗产》。日特科夫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维克多·瓦维奇》,但他通常被视为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却认为《维克多·瓦维奇》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文学报》准备介绍《隐藏的遗产》,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提《维克多·瓦维奇》,因为法捷耶夫否定了这部小说;二,把标题改为《走进成人国度》。这篇文章便算作日特科夫作品集的序言。为了能使日特科夫作品集出版,利季娅接受了《文学报》的条件。后来她写道:“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是否只做过这一次让步呢?回想起来万分惭愧。我在1951年出版的《十二月革命党人——西伯利亚的研究》一书中,竟然歌颂斯大林宪法和斯大林对西伯利亚的工业改造,尽管那时我十分清楚宪法和工业改造的代价,但我仍屈从公认的贴邮票理论。”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2)
1966年,法院审判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人都判了刑。六十二位作家联名致信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认为量刑过重,要求减刑。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为此,利季娅写了《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投寄作协罗斯托夫分会理事会、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苏联作协理事会、《真理报》、《消息报》、《锤子报》、《文学俄罗斯》和《文学报》。利季娅公开谴责肖洛霍夫那些不负责任的话。她投寄作协和各报刊,公开表态,并准备承担责任,这在1966年算得上壮举。但没有一家报刊敢刊登她的公开信。肖洛霍夫是碰不得的。尽管肖洛霍夫看不起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不允许批评肖洛霍夫。当时地下出版社大量印发这封信,造成极大影响。利季娅同作协的关系更加恶化,并且双方都不再妥协。几乎丧失视力并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女作家同强大的作协对立,结果可想而知。
1966年10月,即《公开信》流传后,利季娅写了一篇回忆马尔夏克的文章,纪念他逝世两周年。她认识马尔夏克四十年,一起工作过九年,当然有值得写的东西。她把文章拿给儿童文学出版社,可编辑连看都不看。令她感到意外的是,作家出版社采用了。稿子发排前,编辑部打来电话,请利季娅删去两小段。第一段:“1937年至1939年,马尔夏克的几个朋友被捕失踪,他为受迫害者申辩,有时居然成功。”第二段:“岁月流逝,斯大林死后人们开始返回城市并获得新生。1955年,格尔曼在《文学报》上著文称赞三十年代马尔夏克所领导的‘列宁格勒’编辑部。马尔夏克读后对我说:‘仿佛打开砌死的门。”利季娅拒绝删除。稿子没有发表。
1966年,儿童文学出版社请利季娅为米尔奇克小说集写序。这是一部讲述童年的小说,故事发生在沙皇时代,是作者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米尔奇克是位老同志,十月革命时期任工兵苏维埃代表,参加过左派社会革命党。米尔奇克30年代发表小说时,责编正是利季娅,所以她是写序最合适的人选。米尔奇克的儿子也请她写序,写写渐渐被人遗忘的父亲。利季娅碍于情面答应了。序写好后,出版社社长看了极为满意,但要求删去下面的一段话:“1938年米尔奇克被捕。马尔夏克的编辑部被捣毁,有的编辑被逮捕,有的被撤职。”社长说:“我们是儿童出版社,何必让沉重的过去给他们的生活蒙上阴影呢?”利季娅拒绝删除,序无法使用,影响了小说集的出版。利季娅不仅得罪了出版社,也得罪了米尔奇克的儿子。同年4月28日,利季娅收到出版社的一封信:“作为责编,我很痛心,您不肯删去序言中的一段话。我知道您的指导思想,但您也应为读者想想。您的拒绝使读者无法阅读同小说如此和谐的序言。祝您和令尊五一节快乐,春天和欢乐的节日快乐!”最后这句话使利季娅十分恼火。什么“春天和欢乐的节日快乐”?她回了一封不客气的信,摘译如下:“您隐瞒了我们争吵的真正原因,因为您的信是用公文纸写的。印着出版社印章的公文纸既无法坦诚地谈论恐怖期间的牺牲品,也不敢提到您必须遵从的删除它们的指令。我则用普通信纸以私人身份回信。没必要隐瞒问题的实质。我同出版社的争论并非有关‘一段话或一个句子’,而是有关人的鲜血和人的言论自由。您预定出版的小说集的作者米尔奇克是位卓越的作家和我的挚友,一位老工人和两次革命的参加者,在斯大林暴政时期同千百万无辜的人一样被杀害。下一代人,被害者的子辈和孙辈该不该知道这一切?我坚信应该知道。对暴行不仅应抽象地讲述,还应通过具体人的命运来讲述。这是活下来的人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利季娅的拒绝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包括米尔奇克的家属。“他们向我解释,如保留您的序言,对很多人来说便保留了这个人的生动形象。您拒绝删除,出版社只能用简介代替序言,读者便看不到他的形象了。只要在括号中标出作者的生卒年月,删掉这段话读者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利季娅毫不动摇,因为她知道没有她的序言,书仍然能出版。同日特科夫的书不同,没有她的序言书未必能出版,所以那时利季娅只好妥协。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3)
1967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在国外发表,上面有人下达指示:禁止再版利季娅的旧著和发表她的新作。1968年斯大林逝世十五周年之际,利季娅写了一篇题为《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的文章,投寄《消息报》。文章自然没登出来。文章较长,只能摘译其中的一段:“我想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研究这架机器如何把充满活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冰冷的尸体。必须对这架机器作出判决,并大声喊出。不能销账,在上面心安理得地打上‘销账’,而要解开其原因和后果的线团,严肃认真地、一环接一环地加以分析……千百万农民被划入‘富农’或‘准富农’一栏,被驱赶到荒无人烟的北方,驱向死亡。千百万城市居民被划入‘间谍、破坏分子和人民敌人’一栏,被关进监狱或劳改营。整个民族被指定为叛徒,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异邦。是什么把我们引入前所未有的灾难?国家机器为何扑向无还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