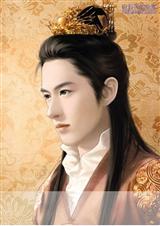һ��۹���-��1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š�
�������У��ڼĺ���֮��д�ţ�
����������������£���ȥ����һ���Ӷ�������Ѳ�����˵�Ϸ���ҶԴ˸о���Ȥ������ΪϷĿ���Ů���������а��ߡ����Ҳ�ǵø��߹��ң����������������������һ����ż��Ϸ����ȥ���Ҿ�Խ��Խ������ס�ˡ����Ǵ����ӣ�����̫����̫�����ˡ�
������һ��֪�������˹��ﰢ�ߡ��Ĺ��°ɡ���ʵ�����ˡ��������µĹ��£���д���������Ҳ�ı�ɸ��輿���ǵþ�������һ��ϷĿ�����������¹�ӡ���Ҳ��������¡�һ�����а��ߵ�С�����һ���ֻ�ʱ���ӽ�����������һ��С�˺����ˣ�Ϊ���ٺ�С��������������������Ϸ��ͷ�������ֵ���ɫ����ͷ����һ����������䲻�����ڣ�����һ��С����Ϊ���ټ�һ�氮�ˣ��Լ�������ͬ�����¹ʣ�˵�����ǹֿ����Ĺ���������Ȼ����Ҳ�ǿ��ⳡϷ��ǰ��֪�����£�����һֱû����������������˹��ﰢ�ߵĹ��£���Ȼ����γ���һ����ɱ���ӣ�չ����������ǰ��ʵ������Ҳ�벻�����¡�
���������ţ����Ӧ��Ҳ���ù��˹��ﰢ�ߵĹ��°ɣ���Ϊ����������ƵIJ�ż�ݸ��������������Լ������������һ��Ҳͬ�鰢�ߵ������������Ͱ��ߣ�����ʱ����ͬ��ȴ��ͬ���ش�С��ʱ���������ͬһ���ֵ������ֵ��Ŷ���������ô����������żȡ�˸����ֽа��ߣ������ְ���ԭ���ڴˡ�
������Ȼ��ˣ��������룬ֱ��һǮ������������ǰ��������Ҳ�����뵽�������������ˣ�Ҳ���䵽���Լ�ͷ�ϡ�
����ȥ�����β����������߲�Զ�ĵط���żȻ������һ����ɱ���ӡ������¼�����Ӧ��˵����żȻ�İɡ���Ϊ���dz���������������һ�����и�������ӣ�Ϊ�˾�����������¼����������¼���������һ���������õ���������������ȴֻ��˵��żȻ���¡��ദ��ʱ�䲻������Сʱ�⾰�ɣ�������澹Ȼ������������������顣������ľ����Ǹ�����Щ�ģ���ô��������òҲ�ã�����ľ�ֹҲ�ã��Dz����ܸо���Ѱ���ĺ������ϵĸ���ġ����ǣ�����ֻ������Щ����ͬ��һ�ң�ֻ֪������������ķ�й���ߣ���Ū�����и��������ӣ��ʴ�СС�����������ᣬ������˵�����ű���ͨŮ�����ܸ��ܵ��ļ�ʮ�ٱ������������У������Ӵ��µ��Ǹ����Ĵ���̫Զ̫Զ�Ĺ������ض�Ҳ��������������ɡ��Ǹ�����֮ҹ������ڷ���ʱ��ס������������˵һ���������ɡ��������뵽�Լ���������˵�����ڣ�Ȼ���ǿյȵ����������ӡ�ֻ������ţ����ȼ�յø����ҡ������϶��Լ���ȫʧȥ��Ϩ���������;��֮�ʣ���̽ȡ����ı�����������Ҳ�������ɵ��ֶΡ�Ϊ����ȥһ������������Ҫ��һ��������棬Ϊ���ټ���һ�棬��ֻ��������һ����ɱ���ӡ�������ȴ�Ǽ��������ء����ҽ�������������ˣ�����Ǹ��ˣ���������ˡ��������ɱ����Ķ�����
������Ȼ����Ҫ������ô���ɵأ���������ˣ����㲻����ʵ�С����ң�Ҫ���Ǹ��峣��˵����������������ʵ�ϣ����������Ӳ��ں�˯�ĸ��岱����ʱ��˵�������ѹ����ˣ�Ϊ��治�������������һ��Ҳ���Dz����ܡ���ij���Ƕ���������������Ǹ�������ޡ�������ˣ����Ҳ�ض�����ԥ����ԥ�ġ�������ô�ɣ���ʱ������ˡ����Ű�ҹ��Ⱦ������棬���о����Լ�������һ�������ˣ������ܻ���Ϊ������͵������ء�
��������Ŀ�ģ���������ɺ͵�һ����ɱͬ���İ�����Ҳ�ǹ�Ϊ����һ�㣬���ø����ʬ��Ҳ�͵�һ��������żȻץס��һ������ס��һ��۹��������Բ����������Ҫ�ģ���ҲΪ��ͬ�����ɣ�ֻ�����������Ҳ���������ΰѽ۹�������������������һ�飬�����������˵��ֻ�����û�������������������һ����ѡ�
�����㵱֪������������֧��ɣ�����ʹ�����������ǻ۵���͵���˼Ҷ�Ŀ������ᡣ��˵����������Ҳ�Ȱ������ǻ�Щ�ɡ���Ϊ����ȡ���o��������ţ�����ʹ�˼�����ķ���������������Ҳ�벻���������ƴ���Լ���������ͬʱҲʹ����һ���˹�Ϊ��������ڷ�����
������Ȼ�����ٴ��������ķ��䡣��һ�������������ľٶ�̫���죬��ʵ�뵽��Щ��һ�����Ŷ����ˡ����ҺͲ�żһ����������Ļ���������ָ��ֻ������һ����ż������˵���Ͱ���һ������˼�����У����ʣ����������أ�����û�У���Ϸ��������ճ�ǰ���ϵ���¥�����Ӵ�ġ����쳹�������ӵ����죬�����������Ǹ�С�˵�����ĺ��С����Ҳ�����Ǹ������ô����ӵġ���һ������������Լ����֡������������д屻���˻��̡���淸�˺Ͱ���ͬ�������У������ϣ���Լ�Ҳ�õ�ͬ���Ĵ����������������������û������ͷ��Լ���
�������ʣ��һ���ˡ������Ϊʲô���Ǹ��������˽۹����أ�����Ϊ���������ĺ����ģ�ȷȷʵʵ�ذ���������������˵������ֻ��һ��ʮ�����С���������뵽�IJ��ԣ���ֻ�������뿴�����������ѡ�
�����Ǹ����Ӷ��Լ�����òһ��������Ҳû�У�����Ҳ����˵�������Լ���Ƭ�µ���һ����ò�������������ɱ�������Ǹ����ϣ���żȻ��������ǰժ�����۾������ҿ�������һ�������һ���Ϊ����һ�����أ����ǽ��ҽ���ס����һ�µĿ��ε��������ߣ����ٿ���˵�����ǹ�һ��ʮ�����С���һ��֮�¾ͻ�����������������ࡪ�������Լ�ȴһ��Ҳ����֪�������ң���Ҳ��Ȼ�����Լ���Ȼ���ζ���ժ���۾�ȥ�����ġ�����Ȼ��������û�����������࣬��ֻҪ����
�������������û�е�������������������Ǹ��ڵ�����ֻ�о�����ʮ������������ȼ�������ġ�
������һ��Ҳ��������Ϸ��İ��߲�ͬ�ģ����Ѻ��������ʱ�����һ��ƶ����Ů������������Ψһ��������ˡ��ھ�������ײ�����Ķ�����������Ѻ�����İ��ߣ������������һ�α���ȼ�����Ļ����Ҳ�Ǻ�Ϸ���Ѥ������ú�Զ��Զ�İ����Ļ�������Լ��ٻ١����ú��ĵƹ����Ȼ�����Ŵ��������һƬ��������Ϊ��ע������һ��������Ϸ��
�����Է�������ȴʲôҲ��֪����Ȼ�������������˵��ȴҲ���غ�ּ�İɡ�
���������µĻ�������ĬĬ���ԣ���Ȼû�������һ�껨Ⱦ�ۣ������Ĵ������������ӵ��ķ��Ȼ���������ֻ�м������ӵĶ̶�һ������
����������
��������
�������룬������һ��Ҳ���İɡ�����Сʱ�ļ��䣬ȫ������һƬ������ͷ��
�������ܹ���������������ģ�ʱ������ĩ�꣬��ĸ��һ��ᵽ���С��ס������ת��˵�Сѧ���꼶�Ժ�����顣����ǰ��Ҳ������ס���ҵĵ����أ�����һ��С������ļ������¡����Ҹ���ô˵�أ�������ֲɽ���Ԩ�äĿ����������ˮ�Ķ�����һ��ͷ��Ҳû�С�
�����ǵ���һ�Σ�����īˮŪ����һ����Ҫ������ͷ��һҳ����ƴ�������ī�յ��������ϳ����壻��ÿ�������������Сʱ����ʱ����������ƵĽ��������Ρ�
������Ȼ��Ҳ������һ�ж���Ϳ�ɺ���һ�ţ�����ī�յĿ�϶��Ҳ�������������������м������棬�һ�������Ƭ����������������
����ֻ���⼸�����棬������ʲô���壬���е�˳������Σ����Ҿ�û�취֪���ˡ�
�������µ���霣���������Щ�����ϵ�������ˣ��������DZ��ΪһƬƬ����Ƭ��ɢ���ڼ�����ͷ��
��������Щûͷû���ij�����Ϊ������̽Ѱ����û���ҵ�����ʱ����һ�����£���Ҳ��������Ϊֹ�ҵ������ˡ�
�����Һ���֪����
��������Ӧ��˵�����Ƿ�֪�����ɡ�
��������Сʱ��������һ���������ҵ����ڻ����������ġ�
����һ��Ů�˵ĺ�Ӱ�������ϵ�һ��ʲô��������������ƹ��������������ţ�����һ�����˵�Ӱ�ӡ������˵�Ӱ����������ƴ�����ӣ�Ů�˵�Ӱ�ӷ���ȫ���������������ز�ס����
��������Ӱ�Ӿ�����һ�𣬵���һ��Ȼ�����ҹ꣧���ŭ�˰����������������ҿ飬ĩ���DZ����ˣ��������Ľ���ˮ��I��Ȼ���ܻ��ڼ���������ģ�����棬Ȼ����������Ӱ����������Ŀֲ����ŸУ��ڱ���ʱ�Ľ���Ѫ�������ɺ����ɫ������Ȼ�ܹ���ô�����ؼ�������
����ɱ�˵����ҵ�ĸ�ס���ϣ��֪��ĸ���ֽ�����������Ѫ�����塣
����ĸ��Ϊ�η�ɱ�Ǹ����Ӳ����أ�����������˭�أ�
������ϣ���ܹ���������棬�ͼ��������������Ҳ���������ij���������һ�飬̽����ĸ�����ϵ��ǰѵ��е����塪����Ӧ��˵��������ҵ�������һ�С�
�������ĸ��ɱ���ˣ�����������ֵĶ��ӣ�����ҵ��������ٲ����µ�����ʱ���ͱ�Ⱦ���������ɺ���ɫ����ô���룬ȥ̽����������࣬��������һ��������ɡ�
����ĸ�״����뿪�Ǹ�С���ӣ����������ʱ��
����ʱ������ʮ���꣨1923�꣩��Ҳ����ֱ�Ӱᵽ���С恣������ȵ�����Ͷ��һ�����ݣ�
�����ڶ���ס�˽�������֮���ٰ�ؾ���粻Զ��С恣���ſ�ʼ��ĸ��������Ϊ���������ʱ��������Сѧ���꼶������˵�ʱ�ļ��䣬����ǰ̤ʵ���ˡ�
�������ǣ���ס������Ķ�������ֻ�ܼ���ƬƬ�϶ϵ��������£��ο�����ǰ�Ĵ�������£����ݷ���������ټ���һ���ξ��㣬����ģ��һƬ�ˡ���
������Ψһ������Ĵ�����ķ羰��Ҳ���������ĸ�ʱ����ĸ��ط������ģ���һ�������ģ�һĨ��ī���������������һƬʪ��Ĺ⾰�����������ģ���������ī��ˮī�����������ģ�����������ˮ�����������Ϊ�������أ���ĺɫ�������ˡ��������䱻���½�ʴ�ˣ�����̫����������Ҳ���������ջ��ڸչ��ɣ��ݱ�������������ɫ�ĵױ�����ϸ����������̳�ϣ���һ�����ӻ���һ�����ʤ����ӿ�𣬶�������ľ�����������أ��������������������ţ���Щ�����������ӡ����Ĥ�ϡ�
�������ݶ�����ۼ�����ͷ�ո�����ʱ����㣬��ʯ�߷������⣬�γ�һ�����ս�������������棬��һ��Ī�������������������ľ����Ӱ�¡�
����������һ�����ǵ��ɹ��á���һ������С���������µı����ݶ���
�����Ҿ����������µ�ס�ּ�Ұ���ܵĵճ��ӡ�
�������ڸ������ܣ����ҵļ�����ֻ����Сʱһ������������ȥ�����ӣ���������ĸ���ҿ�������Ƭ��˵���Ǹ��°ͼ�ϸ��˫�����ݡ���ë�污��ƶ�����ӡ�
����������Ƭ���ҵ������ĵģ�ĸ�״��������µ����������СС�������ţ��Ա�վ�ŵ���һ����ɫ���µĸ��ף�����Ҫ����ƣ��������ż����ʱ��������ʮ���꣬ĸ���Ƕ���ĸ������»�̫̫��ض���Բ�٣���һ�������ص���ǰ��ĸ��ײ�ͬ�������ۣ�����ãȻ�ؿ��������ϵ��Լ���Ӱ�ӡ���������ƬҲ���Կ�������ĸ�ļ����ü�������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