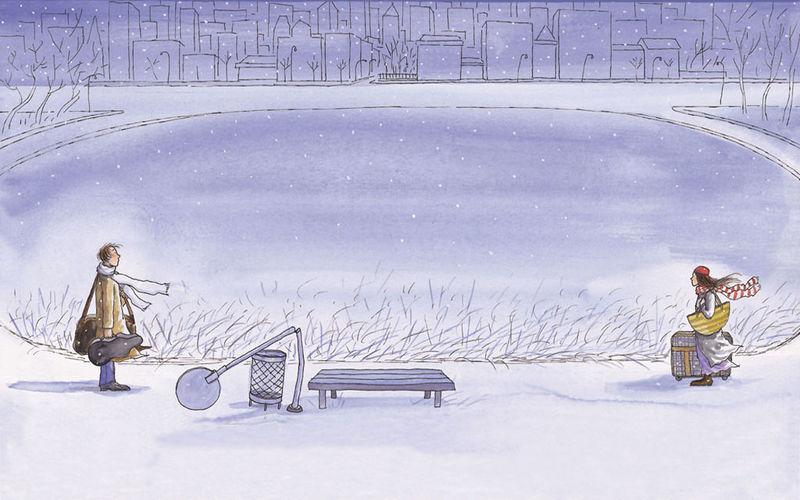向左,遇见花开-第6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事啊,我们能有什么事?”
“没事?没事也不带这样吓人的吧。”姚文夕被我们弄得有些神经错乱,伺候再也不肯来我家做客。
其实姚文夕不知道,我们向对方说谢谢都是发自肺腑,而不是出自礼仪,他跟我说谢谢是因为我从不追问他夜归的理由,以及他身上那种始终挥之不去的神秘香水味来源何处,以贤妻的姿态给足他面子;我跟他说谢谢实则是因为他再也不触犯我的底线,提及莫云泽及其相关的一切话题,也绝口不谈公事,以模范丈夫的姿态对妻子温柔呵护,体贴照顾……我们是如此的默契,一个眼神,一颦一笑,都尽量配合着对方,不触犯对方的隐私,对敏感话题睁只眼闭只眼。你演得天衣无缝,我演得滴水不漏,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大约就是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了。如果那对全球闻名的“史密斯夫妇”(即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看过我们的表演,也会自愧不如,生活才是真的表演啊。
不过偶尔也有穿帮的时候,比如费雨桥外出数天回来,送我礼物时说“特意在日本买的,日本才买得到哦,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可是包装盒上清晰地印着“Made In Paris”,他大约忘记了我的前男友就是法籍华裔,别的英文我不认得,“Paris”我无论如何也会认得的。
当然,好太太应该是装作不认识,并礼貌道谢的,我做到了。因为不知道下次我会不会穿帮,给他留点面子,他或许也会顾及我的面子。
果然不久,我也“穿帮”了。有一次小别胜新婚,我们在床上激烈地做爱,他的兴致似乎很好,做了一次,意犹未尽。半夜时他趁我疲惫地入睡又扯掉了我的睡衣,我迷迷糊糊地迎合着他,随他摆弄来摆弄去,哦吟喘息间我意外高潮,随口叫出:“云泽!”他瞬间石化,停止了动作,诡异地看着我,“你刚才叫谁?”
那一刻我已经清醒,紧张得连呼吸都快停止,寻思着他下一秒会不会甩我一巴掌,或是将我踹下床。
结果,他什么表示也没有,反而兀自笑了起来。
黑暗中那样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
“宝贝,我们继续。”
他果然顾及了我的面子。
不久就是春节,除夕夜下起了大雪,我们将偌大的公馆布置得喜气洋洋,我贴窗花,他就挂灯笼。我从未见过费雨桥如此人情味的一面,他挂灯笼的时候,他给身边人发红包的时候,脸上的笑容跟平日里西装革履的老板模样判若两人。做惯了精英的人,突然踩着梯子挂灯笼,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惊悚。
费雨桥还有更“惊悚”的一面,他亲自写春联。
这回我是真见识了,费雨桥居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平常我只见过他在各种文件上签字,除此之外要看到他写的字堪称稀罕。
那副春联写得苍劲有力,道骨仙风,让我怀疑费雨桥是不是拜高师学过。
他对自己的成果也甚为满意,于是拉我到大门口,请阿江给我们合了张影,特意把那副春联拍进去了。我抢过相机看照片,镜头中的我们喜气洋洋,跟天底下所有平凡的夫妻一样,眉目平和,笑容真切,仿佛瞬间就能到白头。
“嗯,这照片我要留着,将来给我们的儿孙看。”费雨桥也很喜欢。
我忽然有些感动,为这样一张照片。这样没什么不好,就这么到白头,相守一辈子,芸芸众生不都是这么过的嘛,爱情并不能当饭吃是不是?也许将来回过头再来看,也许我们是相爱的呢?岁月那么漫长,什么不可以改变呢?
晚上,我们要厨子做了一桌的美味佳肴,一起共享年夜饭。我们互敬香槟,向对方祝福新年。香槟敬了一杯又一杯,吉利的话说了一句又一句,说到后来没词了,我们就结束团年饭,到院子里放烟花。
绚丽的焰火绽放在夜空,将雪地都映得五彩斑斓,只是那种斑斓转瞬即逝,焰火终有放完的时候,雪地很快就恢复苍白。
即便是在黑夜仍然白得刺目,有些凄怆。
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回屋看春晚了,电视里一派歌舞升平热闹非凡,我们坐在沙发上边吃着零食边点评春晚的节目,一团和气恩恩爱爱。电视看得有点累了,费雨桥拿出一瓶1981年的红酒,要我陪着他喝。可是光喝酒也没什么意思,他提议可以玩玩小游戏,输了的人就喝酒。我问玩什么游戏,他想了想,笑道:“真心话游戏,如何?”
我不过愣了两秒就连声附和,“可以啊,你说怎么玩吧。”
“石头剪刀布,赢了的人向输了的人提问,对方必须说真心话,如果不想回答,就喝酒,如果回答令对方满意,对方就喝酒”
“好,我们玩吧”
游戏开始,开头是一些试探性的烟幕弹,什么“你做我的太太幸福吗?”“你娶我后悔吗?”“你有没有想过离开我?”等等,到后来问题越来越敏感,气氛变得诡异起来。他逮住一次提问的机会,问我:“你有爱过我吗?哪怕曾经爱过,偶尔爱过,都可以。你有吗?”说这话时他微微眯起眼睛,像一个猎人正在瞄准目标,我终于明白他玩这个游戏的目的了,他试图靠近我的内心。
没办法,我们都惯于演戏了,也许只有借助游戏才能探到对方的真心。我静静地望着他。窗外有轻盈的雪花飘落,又下雪了。
费雨桥的眼眸里平静无波。
令人窒息的沉寂。
最后,他说:“你不想说可以喝酒。”
我别无选择,只能喝酒。因为我必须遵守游戏的规则,不说则已,说就要说真话,可是我没发给他正面的回答。
“谢谢。”他轻声说。大约是我没有说出真心话让他难堪,他很体贴地顺手抽了张纸巾递给我,“还要继续吗?”
“继续。”这个时候退场就太没面子了。
烟幕弹放过之后,真刀实枪露出来了。又一轮开始时,我赢得了提问权,于是问他:“我并不是你唯一的女人,对吧?”
他嗤的一声笑,好玩似的瞅着我,当我是个幼稚的小孩子。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犯傻,这样的问题是男人都不会正面回答。
果然,他自觉地给自己倒了杯酒,跟我示意了下,“我喝。”
很优雅地喝了下去。
接下来的一局,又被他抢回了提问权,他问的是:“你是如何判断出我有别的女人的?要具体的事实。”把后路都堵死了,果然是商界精英的风范。
我也笑了起来,“猜的算不算?”
“不算,要事实。”
“那我喝酒。”我端起杯子就咕噜噜地喝下去了,我才不会告诉他事实,从而让他加以防范,虽然他并不需要防范我什么。我多贤惠啊,从不多问一句,睁只眼闭只眼,这样的贤妻还需要防范吗?费雨桥朗声大笑,笑得肩膀直耸,“你进步很快啊,费太太。”
“过奖,有个这么优秀的丈夫,我受益匪浅。”
“你今晚喝得有点多哦。”他晃着二郎腿,饶有兴趣地打量我,“脸都红了,还要继续吗?”
“你说继续就继续。”我心里哼道,“谁怕谁!”
“我要继续。”他兴致盎然,显然还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
接下来我连输了三局,其中有个问题他问的是;“你觉得我比……”他犹豫了下,“比莫云泽差在哪里?”顿了下,又补充,“不许喝酒,只能回答。”
又把后路堵死了。
我看着他没有出声,这算不算末日审判?
“这个……”我揉了揉太阳穴,“一定要回答吗?”
他的表情毋庸置疑,“是的。”
“你并不比他差任何东西,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他还要优秀,只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不是他,所以你们彼此无法取代,回答完毕。”我出人意料的镇定,指了指茶几上的杯子,“满意的话喝酒。”连我自己都诧异,我缘何如此镇定。
他低头沉吟片刻,抬起头时,眼神有一丝不可捉摸的恍惚。他微微颔首,“好,我喝。”说着他默默斟满酒,仰头喝了下去,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说得好,我不是他。”他自嘲地笑,“我认命了。”
我叹口气,觉得适可而止了,于是说:“够了,就到这儿吧,我们看看电视。”说着我拿起遥控器取消静音,刚好是新年钟声,电视里欢呼着跳跃着,彩带气球鲜花掌声笑脸潮水般扑涌出来,我轻轻放下遥控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初一我们睡到中午才起来,我在梳妆台前抹乳液的时候,听到他在露台上打电话,“价钱好说……我当然很有诚意……没有问题,我会给你安排妥当……”我真是很不懂生意场上的人,大过年的都忙活着做生意,赚钱有那么重要吗?
打完电话,他走到我身后,静静地端详镜中的我。
“你的脸太白,可以擦些胭脂。”说着他拿起大号的化妆刷,沾了点CHANEL的腮红扫在我的颧骨上,手法之熟练一点也不亚于专业的化妆师。我诧异地瞪大眼睛,他还会化妆?“嗯,这样气色就好多了。”他歪着头打量我,将我刚刚绾起的长发放了下来,“你不觉得这样很好看吗?你披着头发显得活泼些。”
我哑然失笑,这个男人,我是真的不了解他了。
他又从首饰盒里拿出一对珍珠耳环别在我的耳朵上,退后一步打量我,很满意地点点头,“唔,不错,珍珠很衬你。”然后从身后箍住我,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你不要笑,女人好不好看应该是男人说了算,你要相信我的眼光。比如我娶你,一定是我认定了你是我此生不二的选择才会在神甫面前宣誓,无论我们过去如何,现在,还有未来,我们是要一起走的。一辈子还很长呢,几十年,我们没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的,是不是?”
我凝视着镜中的他,一时间心潮起伏,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是想给我吃定心丸吗?
“四月,我爱你。”他将我的身子扳正,拥我入怀,附在我耳边呢喃轻语,“这么多年从未改变,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处理好我的事情,我只属于你。”
他温热的呼吸扑在我的脖颈,他的声音低沉暗哑,有一种奇异的气场将我包裹其中,让我忽然间变得很无力。我不能挣脱他,就像攀附在树上的藤蔓,没有了自身支撑的力量,我完全要依附于他才得以呼吸。我好像变得有些不像我自己,但是我还有别的依靠吗?除了我的丈夫,还有谁能给我依靠?哪怕他是个魔鬼,也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如藤蔓般缓缓伸出手回抱住他,“我相信你。”
“谢谢。”他仿佛是动容,箍紧了我。
“你以后能不能别说‘谢谢’。”
“唔?为什么?”
“怪生分的。”
他大笑,我能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愉悦,“OK,我们以后不说‘谢谢’。”
这算不算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次日下午,费雨桥驾车带我去他养父陈德忠家拜年。他管养父叫“德叔”,我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定期不定期地会去探望下,但我感觉他们的关系并不热络,甚至有些微妙,因为他每每提及德叔,表情就非常严肃,一切有关德叔的话题都是他的雷区。所以我从不主动问起,至于这次他为什么突然主动带我去见德叔,我不得而知,连问都不敢问。
路上,他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