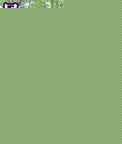流水迢迢下-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月落日升。
黎明时分,崔亮松了一口气,自最高的哨斗下来,一脸疲惫,仍打起精神嘱咐了田策和许隽一番,才回转中军大帐。
河西渠是河西府百姓为灌溉万亩良田而开凿的一道人工沟渠,宽约丈半,水位不深。崔亮耗尽心智,哨斗、传信烟火、尖哨、水网、刀藜全部用上,还派人在渠边不断巡回警戒,方阻住桓军大大小小上百次沿河西渠发动的攻袭。
见他入帐,宁剑瑜迎了上来:“子明辛苦了,前面怎么样?”
崔亮苦笑一声:“昨晚又偷袭了数次,好在发现得及时,挡了回去,现在消停了。”
“我去桥头,侯爷正要找你,你进去吧。”宁剑瑜拍了拍崔亮的肩膀,出帐而去。
崔亮走入内帐,见裴琰正低咳着,将手中的密报收起,微笑道:“相爷今日可好些?”
“好多了。但内力还是只能提起三四分,易寒那一拳,真是要命。”裴琰抬头微笑:“这几日,真是有劳子明了。”
“相爷客气,这是崔亮应该的。”崔亮忙道,又犹豫了一阵,终将心头那事压了下去。
陈安在外大声求见,裴琰道:“进来吧。”
陈安似一阵风卷入帐中,单膝下跪:“禀侯爷,粮草到了,共一百五十车。”
裴琰与崔亮同时一喜,裴琰站了起来:“去看看。”
陈安忙道:“侯爷,您有伤―――”
“只是肩伤,又不是走不动。”裴琰往外走去,二人只能跟上。
陈安边行边道:“据押粮官说,这批粮草,是河西府失守前就从京城运出来的,战报送回京城后,董学士是否会紧急送批军粮过来,他也不知道。”
长风卫簇拥着三人,穿过军营。正逢一批将士自前面镇波桥头轮换回营,见他们个个面带倦色,其中数十人身负有伤,裴琰大步上前,右手抱起已伤重昏迷的一人,长风卫欲待接过,见裴琰面色,退了开去。
裴琰将伤兵送入医帐,凌军医忙接了过来,语带责备:“你自己的伤都没好,怎么这样不爱惜身体?!”
裴琰看了看满是伤兵的医帐,目光在某处停留了一瞬,神色黯然,走出帐外。他拍了拍一名伤兵的肩膀,在众人崇敬的目光中,依然带着崔亮等人,走向后营。
三人查看了一番粮草,回转大帐,裴琰心情略略好转:“这批粮草,解了燃眉之急,只要能守住这河西渠,总有反攻良机。”
“是,桓军士气也不可能持久,这几日熬过去了,他们攻击的力度也有所减弱,看样子,咱们要和桓军在这里耗上一段时间了。”
江慈左手拎着药罐,右手提着药箱进来,崔亮忙接过,裴琰一口将药饮尽。
江慈看了看崔亮,犹豫了一下,崔亮接过药箱:“我来吧。”
江慈走到裴琰身前,轻声道:“相爷,该换药了。”
裴琰看了看她,并不说话。江慈微垂着头,替他除去上衫。
崔亮托着草药过来,替裴琰换药。裴琰瞄了瞄站于一旁细看的江慈,道:“小慈不是早已学会敷药了吗?怎么还总是依赖子明?”
崔亮笑道:“这药一敷上,我就得替相爷针灸,所以还是我来比较好。”
江慈递上银针,崔亮边扎下银针,边和声道:“你记住我下针的穴位,在这几处施针一刻钟,可以减轻伤口处疼痛,促进真气流动,生脉调息。”
江慈用心记住,见崔亮在裴琰腋下扎了一针,一时没看清楚是何穴位,俯身细看,看罢,一抬眼,正对上裴琰清亮的眼神。
她一慌神,手中银针未拿稳,往下掉落。裴琰右手疾伸,接住银针,送至江慈面前,嘴角扯了一下:“怎么,没吃早饭?连根针都拿不稳?”
崔亮反手接过银针,在裴琰后颈处扎下,笑道:“她肯定没吃早饭,听凌军医说,伤兵过多,医帐人手不足,军医和药童们忙得一天只能睡个多时辰,有时饭都顾不上吃。”
裴琰细细看了看江慈的面色,未再说话。
崔亮转身向江慈柔声道:“昨晚是不是又没休息?”
江慈点了点头,犹豫片刻,道:“崔大哥,若是腿部负伤,要减轻疼痛,舒缓经脉,得扎哪几处穴位?”
“得扎环跳、风市、阳陵泉、阴陵泉―――”崔亮在裴琰右腿处一一指点,江慈用心记下,笑道:“我先出去了。”
“好。”
崔亮望着江慈纤细的身影消失在帐门处,语带怜惜:“真是难为小慈了,一个女子,在这军营,救死扶伤―――”
他回过头,见裴琰面色阴沉,忙唤道:“相爷。”
裴琰出了一口粗气,眼神掠过一边木柱上悬挂着的满是箭洞的血衣,又黯然神伤。
崔亮心中暗叹,道:“相爷,人死不能复生,您这样日日对着这血衣,徒然伤身,对伤势恢复不利啊。”
裴琰微微摇头,低声道:“子明,我得时时提醒自己,要替安澄、替长风骑死去的弟兄报这血海深仇。”
崔亮劝道:“仇得报,但还是让安澄早日入土为安吧,他的灵柩,也停了数日了。”
裴琰痛苦地闭上双眼,良久,轻声道:“是,得让他入土为安了。”
他唤了声,长风卫安潞进来。裴琰沉默许久,方才最后下定决心,平静道:“今日酉时,为安澄举行葬礼,让长风卫的弟兄们,都参加吧。”
江慈浑身酸痛,将药倒入药罐内,向凌军医道:“凌军医,我送药去了。”
凌军医并不抬头:“送完药,回去歇歇吧,瞧你那脸色,你若倒下,咱们人手更不足了。”
江慈走至卫昭帐前,光明司卫宗晟挑起帐帘。卫昭正坐于椅中,执笔写着密报,抬头看了看她,也不说话。
江慈待他写完,将药奉上,卫昭闻了闻,江慈忙道:“今天加了点别的药,没那么苦了。”
卫昭一口喝下,仍是眉头轻皱:“我看倒比昨日还苦些。”
江慈不服:“怎么会?我明明问过凌军医才加的。”忽看清卫昭唇角微挑,眼神有几分戏谑之意,她劈手夺过药罐,嗔道:“我看,是三爷舌头失灵了,分不出什么是苦,什么是甜!”
卫昭看着她唇边若隐若现的酒窝,有些失神,旋即急速低头,将密报慢慢折起,冷声道:“叫我卫大人。”
江慈笑道:“是,卫大人。”她打开药箱,道:“卫大人,得换药了。”
卫昭轻“嗯”一声,江慈在他身边蹲下,轻轻将他的素袍撩起,又轻柔地将内里白绸裤卷至大腿上方。
卫昭握着密报,坐于椅中,一动不动,任江慈敷药缠带,呼吸声也放得极低。
江慈将草药敷好,缠上纱带,觉有些手痒,终忍不住道:“卫大人,我想替您针灸,可能会好得快些。”
卫昭仍是轻“嗯”一声,江慈笑道:“您得躺下。”
卫昭还是轻“嗯”一声,在席上躺下,顺手拿起枕边的一本书。
江慈蹲下,在他大腿数个穴位处扎下银针。当她在“阳陵泉”扎下一针,她温热的鼻息扑至卫昭腿上,卫昭右腿微微一颤,江慈忙道:“疼吗?”
卫昭只是翻着书页,并不回答。江慈细心看了看,见穴位并未认错,放下心来,低着头,柔声道:“三爷,以后,对阵杀敌,您好歹先穿上甲胄。”
卫昭视线凝在书页上,却看不清那上面的字,腿部,麻麻痒痒的感觉传来,直传至心底深处。帐内,一片静默,只听见江慈细细的呼吸声。
过得一刻,江慈将银针一一取下,又替卫昭将裤子放下,白袍理好,站起身,拍了拍手,笑道:“好了,这可是我第一次给人针灸,多谢卫大人赏面。”微笑着出帐而去。
卫昭凝望着帐门,唇边渐露一抹笑意,良久,视线自帐门收回,扫过那份密报,笑容又慢慢消失。
他慢慢拿起密报,在手中顿了顿,唤道:“宗晟!”
夕阳残照,铺在河西渠上,反射着灼灼波光。
田野间的荒草,也被晚霞铺上了一层金色,暮风吹来,野草起伏,衣袂萧萧,平添几分苍凉。
长风卫们均着甲胄战袍,扶刀持剑,面容肃穆中皆透着沉痛与伤感。裴琰身形挺直,立于土坑前,面无表情,只是手中的血衣灼得他浑身发烫,痛悔难言。
宁剑瑜与陈安,一左一右,立于他身后,眼见黑色棺木抬来,齐齐上前扶住灵柩。
悲壮的铜号声响起,十六名长风卫将灵柩缓缓沉入土坑。灵柩入土,震动了一下,裴琰悚然一惊,大步向前,单膝跪落在黄土之中。
甲胄擦响,长风卫们齐齐跪落,低下头去。
远处,不知是谁,吹响了一曲竹笛,是南安府的民谣《游子吟》。长风卫们多为南安府人氏,听着这曲熟悉的民谣,想着曾朝夕相处的人不能再返故乡,埋骨战场,俱各悲痛难言,终有人轻声呜咽。
裴琰难抑心中痛楚,血气上涌,低咳数声,宁剑瑜过来将他扶住。裴琰微微摇了摇头,宁剑瑜默默退开数步。
裴琰缓慢撒手,血衣在空中卷舞了一下,落于棺木之上。他猛然闭上双眼,平静道:“合土吧。”
笛声顿了顿,再起时,黄土“唦唦”,落向棺木。
夕阳渐落,飞鸟在原野间掠过一道翼影,瞬间即逝。
江慈回帐睡了一会,待恢复了一点精神,便又到医帐忙碌开来。
田策带着退下来的三万人死伤惨重,若非安澄率那万人抵死挡住桓军,便要全军覆没。伤员挤满了各个医帐,江慈忙得团团转。
直至黄昏,江慈仍在给伤兵们换药,崔亮忽在医帐门口唤道:“江慈!”
江慈应了一声,手中仍在忙着。崔亮再唤声,凌军医抬头道:“你去吧,崔军师肯定有要紧事。”
江慈将手中纱布交给小天,钻出帐外:“崔大哥,什么事?”
崔亮微笑道:“相爷找你有事,你随我来。”
江慈一愣,崔亮已转身,她忙跟上。二人走入中军大帐,见帐内空无一人,江慈转头看着崔亮,崔亮却微微一笑,并不说话。过得一阵,一名约十六七岁的哨兵进来,行礼道:“军师!”
崔亮和声道:“有没有发现异常?”
“报告军师,暂时没有。”
“嗯。辛苦了。”崔亮指了指一边:“喝口水吧,瞧你满头大汗。”
哨兵受宠若惊,这几日,长风骑在这位年轻军师的统一调兵指挥下,方挫败桓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而他层出不穷的防守手段也让长风骑大开眼界,个个心中对他敬慕无比,军师有命,自当遵从,握起茶杯“咕咚”灌下去,放下茶杯便倒在了地上。
江慈看得更加迷糊,崔亮却迅速除下哨兵的衣服,递给江慈。江慈这才想到这名哨兵的身形和自己差不多,虽不明崔亮用意,却也急忙穿上。
崔亮将她军帽压低,在她耳边低声道:“你到我帐中等我。”
崔亮再大声道:“你把这个送到我帐中去。”又学着先前那哨兵的声音含混应了声“是!”。
江慈抱着一大堆弓箭掩住面容,走出中军大帐,镇定地走入不远处崔亮的军帐。
不多时,崔亮过来,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掀开帐后一角,带着江慈钻进了紧挨着的陈安的帐篷。
崔亮再带着江慈从陈安帐篷后钻出去,迅速穿过军营,到达一处灌木林边。
他到灌木林后牵出两匹马,将马缰交给江慈,江慈愣愣上马,随着崔亮向南疾驰。
夕阳逐渐落下,江慈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