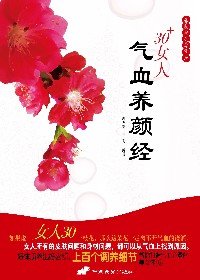绘蓝颜-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七钉
【正文】
楔子
夏国文平十年,秋。
夕阳西下,薄晖淡霞映照天空,南方小城莲州郊外的林荫道上,歪歪倒倒走来一个老叫花子。头发蓬乱,衣衫褴褛,满面岁月留痕,腰间斜挂酒葫芦,手中拿着一个豁豁牙牙缺了口的瓷碗,他闭着双眼,使一根小木棍有一下没一下的敲着碗边,摇头晃脑地念道:
“载还十里香风,闲却一钩明月,龙归沧海,船泊清河。可惜明朝,又是初六!”
道上除他之外再无别人,他忽左忽右,拖沓踉跄着前行,醉酒之相毕露,时而呵呵痴笑几声,絮叨话语不断:“初六,又是初六,没饭就去谭老爷家乞口饭吃,没酒就去谭老爷家讨杯酒喝!善心的好人啊……”
顺着林荫道向南晃半里,下路再行几步便到了那宽院高墙的谭府门前。
这谭府老爷据说少时也是家境穷苦,靠贩私盐起家,跑了几年单帮挣了不少银子,便回家乡来做起了丝绸生意。头脑灵活的谭老爷生意越做越大,家业越来越厚,很快便跻身夏国大富之家的行列,为人称道的是,他富而不苛,亲和有礼,不仅在莲州多处兴建祠堂,还不时接济贫家,虽无官职,却也为百姓所拥戴,威望甚高。
每月初六便是谭府施善发粮的日子,初始只是接济接济莲州城内的穷苦人,很快消息就一传十,十传百,谭善人的名声愈传愈远,每到初六这日,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乞丐就会将府舍围得水泄不通。老叫花子有先见,提前一日就来排队,先占个良位,免得到时挤不过那些成群结队的丐帮弟子。
谭府大门就在眼前,老叫花子眯开眼,看着府门“呃”地打了个酒嗝,晃晃脑袋,将眼睛又睁大了些,心中不免奇怪。谭宅门前一向有两个打马小厮守着的,今日竟没了人影,铜狮门扣上漓着些暗红之物,青漆大门开了一条小缝。他吸了吸鼻子,空气中那不寻常的浓郁之味让他不 禁打了个寒战,略凑近几步,隐隐听见内里传来笑声。
老叫花子呆愣一阵,手中小棍又敲将起来,伴着瓷碗发出的叮声,他踏上台阶,伸手推开宽大门扇,口中叫道:“谭家老爷夫人万福安康,常德又厚着脸皮来求口稀粥度饥了。”
说话时眼光已扫遍院内,紧着“啪!”地一声,瓷碗落地摔得粉碎。饶是一把年纪的老叫花子阅遍众生百态,看尽世间苍凉,仍被面前骇人景象吓得酒醒大半,膝头一软瘫倒在地。
血,触目皆是血!尸体,到处皆是尸体!
院内横着多具死状各异的尸体,趴着的,蜷着的,歪靠在阶下的;断肢的,断头的,胸前掏出窟窿的!男女老少,数十具之多,不知已死多久,只见他们最后定格的表情有恐惧,有挣扎,有痛苦,也有木然。
血,从不同方位的尸体处流出,流成一道又一道蜿蜒的红溪,汇合成一片又一片惊心的血洇。余暮金色霞光之下,大片暗红的血,断断续续的笑声,几十具冰冷的尸身与墙角沙沙作响的芭蕉,交织出沁入骨髓的诡异。这一刻的谭家,俨然人间地狱!
老叫花子口不能言,颤抖着伸出手点向院中,双眼已瞪到极至。他看见在那血泊正中,竟还立着二人,跪着二人。
立在左侧的是一个年轻的紫衣男子,他肤白如霜,眉眼细长,轻纱薄衫宽松垮在身上,唇角噙着一丝邪笑,如没有骨头般架着双臂,压靠在身边那人肩上,为何说压?因为他身边的人,只是个少年郎!十二三岁模样,黑衣裹身,表情阴冷,即使相距甚远,老叫花子还是感受到从他身上发散出的阵阵寒气。一双浓眉紧拧,星目显露恨意,死死盯着面前跪着的二人。
跪在黑衣少年面前的人低着脑袋,披在后背的发稍在白缎袍上淋拉出血痕,双臂软软垂下。虽看不见长相,但只从那穿着身形辨别,老叫花子也一眼认出那正是谭家的主人—谭文渊,不过他此刻动也不动,不知是死是活。
而跪在紫衣人身前的……竟是一个女娃娃!衣服已被血糊得看不清本来颜色,小小的身躯微俯,似在用手撑着地,高度不及紫衣人膝部,鱼鬟散了一边,脑袋时而仰起,时而点下,那断续的诡异笑声就是从她嘴里发出来的。
老叫花子哆嗦着指了几指,腿软得站不起身,只得单手蹭地惊恐的向门外挪去。
紫衣人瞥了他一眼,笑意愈浓,低头轻问黑衣少年:“被人发现了呢,你瞧我为你冒了多大的险,杀了他灭口如何?”
黑衣少年肩膀一抖,抬头看向紫衣人,微带怒意道:“你杀得还不过瘾吗?”
紫衣人吟吟一笑,玉白手指抚了抚少年面颊,挑眉转目,冲老叫花子懒洋洋地道:“老东西快些去告官吧,迟了可就追不到我们了!”
老叫花子屁 股已挪到门口,听得这话,两手赶紧用力撑地翻过门槛,双腿一缩连滚带爬窜至掩住的那扇门外,靠在门上按住胸口,惊魂不定,脑中浮出许多疑问,这人是谁?他为何要杀光谭家的人?那带着不屑,带着威胁的语气让老叫花子心悸不已,若不是武林高手又哪来这般自信?
院内半晌无音,突然传来“噗”的一声。紫衣人语带笑意道:“季凌云,你心愿已了,记得莫要对我食言哦。”
少年沉默。紫衣人又道:“谭家这不会哭只会笑的小女娃倒是有趣的很,可惜不是男娃,命短了点,你动手还是我动手?”
女娃娃仍在咯咯笑着,笑声断续更甚,几乎一笑一断,气已弱,声已哑。
良久,少年开口:“走吧。”
老叫花子一听他们要走,慌得拔腿就向林荫道奔去,横冲到路的那一边,顺着坡势卧倒草从中,屏息凝神,大气不敢多出一口,心中唏嘘不已,谭老爷一向待人宽厚,遇贫必济,老叫花子受他恩惠也不止一次,今日怎会遭此恶劫?只愿家中还有活口,能向官府道出那两个歹人一丝半分的线索,让谭家人不至枉死吧。
暮色渐沉,金霞已被云遮住,天空从灰蓝幻至深蓝、从深蓝幻至幽蓝,直到天幕中挂起了星星,老叫花子也没有等到那两人离开的动静。
身体已趴得僵硬,老叫花子欠起身来向谭府方向张望了一番,此刻天暗,什么也看不清晰,除去草中虫鸣,再无异常声响,思忖再三,他爬了起来,一步三顿再次移向谭家。晚秋凉风乍起,血腥味浓烈如锈,大门半虚半掩,安和热闹的谭府遭遇半日变故,瞬时成了凶宅。
别在门边向里窥视,院内没有站立身影,地上死尸仍在原位。确定那两人已离去,他扶门轻声喊道:“谭老爷,谭老爷?”连唤数声,满院死寂,正中一团昏白再无丝毫动静,看来已无人生还了。老叫花子不敢再往里进,心中又害怕又伤心,抬手抹了抹眼睛,低叹一声:“富贵累身,竟遭灭门,谭老爷,常德混泊莲州四载,亏得你数次接济,我却无能救你性命,眼看着你被歹人所害……唉,且带着家人一路走好吧,初一十五常德定去祭上一杯清酒。”
说罢话,老叫花子按下难过,欲行离开。刚迈一步,忽听身后轻微“呵”地一声。他惊骇转身,见院中尸首横杂处似有一物在动。
叫花子心中一跳,莫不是还有活口?慌忙三步并两步冲进院中,跨过几具尸身,伸手径直捞向那团昏白一侧,触到了后脑散开的头发,也触到了一个颤抖不止的小身体,再一探,脖颈温热,果然还活着!
老叫花子忙将她抱起,借星月之光,望见手中小人儿不过二三岁的孩提年纪,正是那方才跪地的女童,一张稚脸沾满血污,紧紧闭着眼睛,嘴中发出极轻极淡的“呵呵”声,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凄异之状,寸笔难书。
叫花子抑不住心酸,叹道:“是谭老爷家的小姐么?可怜你爹……”
话音未落,门扣忽地被人敲了两下,外传人声:“怪了,看门的小六子跑哪儿去了?”随着声音从门侧挑进一盏灯笼,闪入一个男人。老叫花子抱着女娃来不及躲避,直挺挺站在一圈死尸中与那人碰了个正着,暗夜昏黑,来人目光挪上挪下,对上老叫花子的眼睛,愣怔半晌,将灯笼一扔,拉魂惨叫:“杀人啦!有鬼啊!”掉头便向外窜去。
老叫花子猛地反应过来,出了一身冷汗,跟着那人脚步跑出府门,急步追上大路,已看不见那人身影,撕心的呼救声在风中愈飘愈远。
他低头看看怀中似昏睡过去一般的女娃,苦恼的摇头:“想是有人去报官了。可怜只剩下你一人,这该如何是好呢?”
女娃闭着眼睛,不哭不笑,无声无息,小手缩在胸前,蜷成了一个哀求的姿势。
老叫花子踌躇一阵,看向满天星斗,一声长叹:“被灭了门的孩子啊,未经风雨润,先被雪霜催,命虽苦,却不该绝,且随我去罢!”
将女娃身前搂紧,下路进林,转瞬消失在暗夜之中。
西城霸王
文平十八年,康州,春。
春分动市春草芳,年节将至,喜意满城,康州大街小巷人潮络绎不绝,店家摊贩生意异常火爆,百姓劳碌一年积下的银子,在这太平盛世里赶上过年的当口就再也存不住了,比赛似的置办年货,钱如流水般流入店家的腰包。开大店的赚大钱,开小店的赚小钱,就连路边摊也能趁着这个好时候发上一笔小财。
一个外地货郎挑着挂满琳琅的担子从城东转到城西,欲找个好地方设点开卖。行至福归酒楼门前,见那处人流密集,便放下担子,支起木架,张口吆喝道:“翠玉簪、珍珠链、胭脂水粉应有尽有,物精价廉,莫要错过好东西喽!”
吆喝了一气,看的人不多,买的人就更少,货郎闭了嘴,奇怪的看着人群都不约而同的朝着右侧涌去。
离他摊子右侧十步距离处,放置了一个铁皮炉子,炉上架着锅,炉边支了架小板车,有类似面团之物堆在上面。再往右几步,围了一堆人,不时爆发出阵阵叫好声。货郎看看四周,除己之外再无其他摊贩,刚才还有一两个蹲在地上卖蔬果面糖的,这会儿都不见了。货郎好奇顿起,那里又是卖的何物能让人这么捧场?听这起哄的动静,莫不是跑江湖卖艺的?货郎凑上前想看个究竟,无奈围观者太多,踮起脚尖还是看不真切,他拉住一个路人问道:“小哥,可知那方卖的何物?”
“春联儿。”
货郎更奇怪了,不过是卖个春联儿也能招来围观,也能让人哄好?难道是名家当街题字?正兀自琢磨着,身边突然“砰”地一声巨响,回头一瞧,首饰摊已被人砸翻,珠珠串串滚了一地,胭脂水粉四处散落。货郎“啊呀”叫出声来,指向罪魁祸首怒叫:“为何毁我生意?”
面前站了三人,个个身高体壮,彪悍非常,领头一蓄着络腮胡须的大汉一手叉腰,一手扛棍在肩,凶神恶煞地喝道:“谁准你在此做生意?这条街不许摆摊你不晓得吗?”
货郎一抖,刹时明白遇见地头蛇了,暗叹自己选址不当,忙从腰间掏出几纹钱递上:“请兄台笑纳,城东到城西几无空地,就让我在此卖上一阵吧。”
那大汉手一抬将铜钱隔开,瓮声笑道:“五纹钱?哈哈哈哈,老子不要,你快走吧!这里可不是你摆摊的地儿!”
货郎见他们态度强硬,三人寻衅似的一同围了上来,便也不敢再多说,只得俯身收拾东西,边收拾边抱怨:“唉,就欺负我外乡人,那处也有人摆摊,为何不撵?”
大汉眼光一瞟,嗤笑道:“那处摊子是我们的金主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