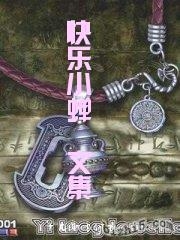撞上快乐-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注定会低估将来自己的感受会跟现在自己的感受有多么大的不同。
比较和厚今主义(2)
小结
历史学家用“厚今主义”这个词来形容用今天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倾向。虽然我们非常鄙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但是这些主义不过是在最近才被认为是道德沦丧的标志,所以,指责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蓄奴或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女性表现出优越感就有点像因为某人在1923年没有系安全带而逮捕他一样。然而,通过今天的视角来看待过去的做法绝对是泛滥成灾的现象。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曾经指出:“没有消除厚今主义的现成办法;它是很难从现代退场的。”好消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历史人,所以不用担心寻找这个出口的问题。而坏消息是,我们都是未来人,而当人们往前看的时候,厚今主义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对未来的预言是现在做出的,它们势必会受到现在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感觉(“我饿了”)和现在的想法(“那个大音箱听起来比小的好”)非常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自己以后感觉的判断。因为时间是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我们倾向于将未来想象成为稍加扭曲的现在,所以我们想象中的未来必然会看起来像是稍加扭曲的现在。当前的现实是如此实在和强大,所以想象只能被牢牢地拴在以它为中心的轨道上,永远无法真正逃离。厚今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无法意识到未来的自己不会以现在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了。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未来人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我们根本不能从以后我们要成为的那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对现实免疫(1)
我靠在背上好保卫我的肚子;
靠我的聪明好守住我肚子里的玩意儿;
靠我守住秘密好保持我的清白;
靠我的面罩好卫护我的美貌;
——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但是,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差点把这个头衔输给一匹马。威廉?冯?奥斯滕(WilhemvonOsten)是一位退休教师。1891年,他宣布他养的一匹名叫“聪明的汉斯”的爱马能够回答有关时事、数学和其他许多话题的诸多问题,而回答的方式就是用前蹄敲打地面。比如,奥斯滕可以让聪明的汉斯计算出3加5等于多少,而马会等到主人提问结束,敲打8下,然后停下来。有时候,奥斯滕不是口头提问题,而是将问题写在硬纸板上,然后举起来让聪明的汉斯看,而这匹马理解书面语言的能力似乎丝毫不逊色于它理解口头指令的能力。当然,聪明的汉斯并不能答对每一个问题,但是,它的表现比其他任何钉掌的家伙都好多了。它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很快就成为柏林的风云人物。1904年,柏林心理学研究所的主任派他的学生——奥斯卡?芬特格斯(OskarPfungst)非常审慎地调查这一现象。而芬特格斯注意到,如果奥斯滕站在聪明的汉斯身后而不是面前,或者奥斯滕自己也不知道问题答案的话,这匹马答错问题的几率就要高得多。在一系列实验之后,聪明的芬特格斯终于证明聪明的汉斯其实并不会阅读,而它能够读懂的其实是奥斯滕的肢体语言。当奥斯滕微微弓身时,聪明的汉斯就会开始敲击,而当奥斯滕直起身子,或者稍微歪一歪头,或者微微挑眉,它就会停下来。换言之,奥斯滕在最恰当的时间发出信号让聪明的汉斯开始或停止敲击,这样就造成了马能够回答问题的错觉。
聪明的汉斯并非天才,但是奥斯滕也没有招摇撞骗。事实上,他曾经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耐心地教授自己的马儿数学和世界形势,而当他知道原来自己是在自欺欺人时,真的感到相当的震惊和沮丧。这种欺骗非常巧妙和有效,却是在无意之间做到的,而奥斯滕并非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我们可以将心理免疫系统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称为“战术”或者“策略”,但是,这些词都不可避免的带有计划和故意的色彩。而事实上,我们却不能把人们当作是操控这一切的阴谋家,认为他们有意识地试图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积极的观点。研究人员指出,事实恰恰相反,人们通常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如果非要他们给出一个理由,他们却准备好了现成的理由。比如,在志愿者们看着电脑屏幕的时候,屏幕上闪过一个又一个单词,每个单词停留的时间不过几微秒,人们根本就无从知道自己曾经看到过这些词,也无从猜测这些词到底是什么。如果屏幕上闪过的是“敌意”这个词,志愿者们就会以消极的态度看待他人。如果屏幕上闪过的是“老迈”这个词,志愿者们就会走得很慢。如果闪现的是“愚蠢”这个词,他们就会在考试中表现的很糟糕。而事后,当他们被要求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判断、行走,以及在考试中有那样的表现时,他们不是说,“我不知道。”而是很快调动大脑考虑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我走得很慢”),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但是谬误的解释(“我累了”),而旁观者也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烹调事实时,我们同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而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刻意要得出正面的观点(“破产一定会有什么好处,除非我发现它,我就不离开这把椅子”),其实就种下了自我毁灭的祸根。一些志愿者欣赏了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春之祭》。一些人的任务是听音乐,而另外一些人则被要求一边听一边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在曲目结束时,比起那些只是听音乐的人,被要求努力快乐起来的志愿者们情绪要差得多。为什么?有两个原因。首先,也许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坐着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特意去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正面的结论。但是,研究表明,但凡我们有一点分心,这些刻意的企图就很有可能逆火,反过来让我们感觉更差。第二,刻意烹调事实实在是太明显了,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轻贱。当然,在未婚妻将我们孤零零地抛弃在婚礼圣坛前时,我们希望相信没有她自己会生活得更好,如果能够发现支持这个结论的事实(“其实她根本就不适合我,是吧,妈妈?”)我们的感觉会更好。但是,发现这些事实的过程必须感觉起来像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刻意的粉饰太平(“要是我们这样来提问题,而且只问妈妈不问别人,我几乎一定能够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一旦诡计被拆穿,曾经被人抛弃的这个污点就会在自己的可怜素质列表中显得非常显眼。积极的结论要令人信服,就必须建立在我们自信是诚实得来的事实基础之上。我们通过下意识地烹调事实然后有意识地消费它们来做到这一点。人们在餐厅用晚餐,而厨师却藏在地下室。这种无意识烹调的唯一好处就是它行之有效;而它的代价却是,我们因此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现在,请允许我向你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对现实免疫(2)
从向前看到向后看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曾经系统地研究过那些曾经被怯场的准配偶单独留在结婚圣坛上的人。但是,我很愿意用一瓶好酒打赌,如果你能够集合起足够多的差一点就成为新郎或者新娘的人并问他们是更愿意将这个事件称为“我今生遇到的最坏的事情”,还是将它称为“我今生遇到的最好的事情”,那么,他们中更多的人会选择后一种描述而不是前者。而且我愿意用一整箱这种酒来打赌,如果你找到的样本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而你的问题是,回顾过去,什么事情能够被看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情”,没有人会把“被抛弃”算进去。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想象中被抛弃的经历更加痛苦,而回忆中被抛弃的经历则更加浪漫。想象自己以这种方式被晾在那里,我们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对这个经历所有可能看法中最可怕的一个;然而,一旦我们真的经历过了这样的心碎,并且像这样在家人、朋友和鲜花商面前丢面子,我们的大脑就开始搜购一种没有那么可怕的观点了,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类的大脑是非常精明的购物者。然而,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购物的,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们会这样做。因此,我们漫不经心地认为,在回想此事的时候,我们对它的看###同预想它的时候一样的可怕。换言之,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改变,因为,通常我们并不了解改变它们的过程。
这个事实使我们很难预测一个人未来的情绪。在某项研究中,志愿者们得到一个申请工作的机会,这份工作的内容就是品尝各种冰激凌并给它们起好玩的名字,而且收入可观。在申请过程中,志愿者们的面试过程会被录下来。有些志愿者被告知,一位评审将会根据面试录像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而此人可以单独做决定(评审组)。而另外一些志愿者被告知一个评审团将会观看他们的面试记录,并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评审团组)。评审团组的志愿者被告知,只要评审团里有一位成员投票支持他,他就可以得到聘用,因此,只有在所有评委一致同意不聘用他的时候,他才得不到这份工作。然后,所有的志愿者都进行了面试,并且都预测了如果自己得不到这份工作会有什么感觉。几分钟后,研究人员走进来,很抱歉地解释说,经过认真考虑,评审或者评审团认为这个志愿者不太适合这份工作。然后,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们报告他们的感受。
快乐评审评审团评审评审团
被拒绝之前被拒绝之后
图19:被一位变化无常的评审拒绝的志愿者比被意见一致的陪审团拒绝的志愿者要高兴(右图)。但是,他们都无法在此之前预见到这种情况(左图)。
研究结果如图19所示。左边的圆柱显示,两个组的志愿者预期他们会感到同样强烈的不快。毕竟,拒绝算得上是当头一棒,而不管打这一棒的人是一个评审、一个评审团还是一群犹太正教拉比,我们都预期这一下会打得我们很疼。然而,右边的圆柱显示,当这一棒由一个评审团来打的话,会比由一个评审来打要疼一些。为什么呢?好吧,想象一下自己曾经申请做泳装模特的工作。要得到这份工作,你就必须披上非常暴露的服装在某个穿着3美元外套,眼光挑剔的傻瓜面前走来走去。如果这个傻瓜将你上下打量一番之后,摇摇头,说:“抱歉,你不是做模特的料。”你很可能会感觉很糟糕。至少要难受一两分钟。但是,像这样遭受单个人的拒绝,每个人都时常经历,在几分钟后,大多数人都能够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并继续生活。我们之所以很快就能恢复自如,是因为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可以驾轻就熟地利用这个经验中的模糊性,并缓解它的刺痛:“这家伙根本就没有认真看我出色的转体”,或者“他就是那种只注意身高而不注意体重的怪人。”,又或者“难道我要听一个穿着这样外套的人来告诉我什么是时尚吗?”
不过,现在请你想象一下自己在为一屋子的人展示泳装,其中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年轻人,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