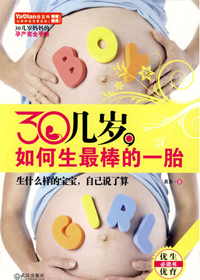最长的一天:我见证了诺曼底登陆-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戴维和你过早地离开,让我甚是遗憾。乐观的你错过了很多机会。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你在,我一准要委你以重任。但天意如此,悲叹也改变不了。克劳德以及你的老部下,个个表现出色。在此,我要特别表扬准下士罗伯特,他缴获了一挺宝贝得不得了的MG…34,他不止一次地用这家伙狠狠教训了德国鬼子。埃斯利下士也是一名战场上的好小伙子。对了,戴维,你不在,你的弟兄都尽了自己的职责。请记住,我始终坚信,一个命令反映的是下令者的智慧——这在24日得到印证。法尔福和孙雷两位上尉是昨天归的队,前者带来了你受伤的消息。听到你胫骨骨折,我深感惋惜。对自己的作战策略,我们深感满意。我只是想让你有所了解,空降部队看来是获得了各方的好评。我写了一份攻取两座大桥的详细报告,但愿这创造了我们团的历史,其实,这已经刊载在报纸上了!孙雷走后,马克表现得相当出色!
因为受了重伤,特迪法威尔在夺下大桥两个小时后阵亡。布里安如今接过了他的人马,看来他相当满意。切斯迪在紧靠我身边的战壕内阵亡,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损失。我算是死里逃生;托尼也许对你说过,一名狙击手为我的脑袋加了个戳子,一个贯穿头盔前后的洞;切斯迪阵亡的同时,我背上也中了榴弹片——但终不致命!
暂时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我仍然盼望着能回家给特丽过第二个生日。失去邓让我深感不安,不知如何写信告知他的妻子。我提议授予他一项大的荣誉,希望他妻子能得到。你别告诉其他人,我也推荐了你和桑迪,但你也别抱太大的指望,提议不过是程序的一部分。旅里也很支持。
祝你早日康复,戴维,希望这封信能满足你渴求消息的天性。
你的约翰。
乔伊斯很好——有空给他写信。
第31页 :
T奥特维
我们于11点半起飞。大概有36架飞机。起飞前,我走过全队飞机,一一叮嘱每一架飞机的每一位机长和全体官兵。我在裤子后袋里塞了瓶威士忌,喝了一口酒,绕着飞机转了一圈,准时起飞。我们平平安安地飞到了海岸上空。有人说没有防空炮火。这时在我们这架飞机的尾部附近响起了一声猛烈的爆炸,所幸我们没受到什么损失。我们跳伞的时候,又来了一次,站在舱门内的我受到了爆炸的冲击。站在我前面的士兵受到的冲击更大,像枚子弹一样弹了出去,但他没受伤。地面上有轻武器朝我们开火,看子弹的曳光就知道。我清楚地看见曳光弹穿过我的降落伞,我降落的过程中,伞没着火,但我以为自己会急速坠落——但这事儿也没发生。由于遭遇到轻武器的拦截,空降广为分散,再加上种种因素,人员散落在各地。德国人早就放水淹没了这个地区。有些地方,我要趟过齐腰或齐胸深的水。我碰到了几个人,副机长约翰伍德盖特,他和我想尽办法将士兵从这片淹没的沼泽中拽出来,可他们身背六十磅的装备,下吸力大的难以置信,我们也束手无策。仅仅在那里,我就损失了许多官兵。他们就这样陷了下去,淹死在水中。到了营集结地,我发现了我的通讯员,他跟在我后面跳的伞,仅仅在我后面一步,但先我一步抵达这里。他一直在等着我,他说,“首长,您大概只剩下50名官兵。”(不过)没告诉别人,我给自己预留了15分钟的时间,出发进攻炮台时,总兵力增加到150名,一度300不到。等我们从炮台出来,连我在内,仅剩65人。
(在集结地)到了出发的时间,我又多等了15分钟,集合了150人。去炮台的路上,轰炸炮台却无一命中的皇家空军,出人意料地在我们的路线上丢了不少炸弹,因此,我们还得在深达八九英尺的弹坑里爬进爬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这可不是件好玩的来到弹坑附近,听见有部队向这边开过来,我们赶紧躲进弹坑,德国人从我们身边径直走了过去。我甚至能伸手摸到他们的脚腕。他们根本没看见我们。等我到了集结地,也就是炮台外围的第二个集结地,由于只剩下这一小部分人马,我只能调整部署。我取消了用爆破筒在铁丝网上打开四个突破口,由此发动进攻的计划,我只炸开了两个,因为让大队人马穿越两个突破口,比少数兵力越过四个突破口更为理想。我派保罗格林威和一名连军士长先接近防御地带,他们的任务是躲在外面,偷听德国人的对话,数他们的烟蒂等等。他们爬过雷区,摸黑拆除了地雷的引信。这是一项非常需要勇气的任务,他们必须要做。幸运的是,虽然明月当空,但他们没有被发现。接着,他们爬了回来,背部着地,用脚后跟拖出了一条路,让我们顺着这条路前进。他们都被授予了勋章,这无须多说。
到了防御地带,我才获知此事,我当即重新做了调整,准时发动了进攻。我命两组突击队先后越过各自的突破口,从两面包抄。突击队绕到暗堡的正面,后面的钢门根本无法打开,虽说滑翔机为我们营运来了两门反坦克炮,但炮也给丢散了,不在手边。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从炮口所指的地方突破。一看出我们是空降兵,德国人就举手投了降。我能听到他们大喊“空降兵”。除了俘获的23人,这个据点的守军非死即伤,我们将23个俘虏带了出来。正如我对一名手下的军官说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从这里突围?该死的地雷还在那儿。于是我对德国人说,幸好当时我的德语还算流利,我说给我们带路,他们不肯。(但我命令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
突击队将手榴弹塞进了炮台的炮筒,除了留下一堆需要清除出来的弹片,根本奈何不了这些闪亮、光滑坚硬的铁家伙。但我们又下了炮的后膛,给扔得远远的,没有新的后膛,谁也别想发射这几门炮。虽说后来转移到下一个目标前,又无法留下一支占领军时,他们想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带着150个人进攻,连我在内,只出来65个人。损员并没有全部阵亡,有些人受了伤,但我们只能将伤员托付给医生。我们俘获了一名德国医生,表扬了他一番后,他返回炮台,帮忙救治我们的人。不过,我们也有德军伤员。德军伤员的人数和我们大致相当。
随军教士跟在我们后面,他和几名当地男子去了一座附近的小村庄,找来两辆德国卡车、一辆小汽车、两辆德军指挥车,我们将伤员抬上车,送往第6空降师。他们在车头打出了一面红十字旗,德国人将他们放了过去。(回忆录音实录)(此役授予奥特维优异服务勋章)
第32页 :
¥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JS希尔
我找了个用磷光物画了希特勒头像的足球,挂在我帐篷的上方,加拿大人对此是拍手称颂,我说我打算在飞越沿海守军的时候给扔下去,他们又送给我几块砖头,让我一并扔出去,这时,我已经来到机舱门口。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我向窗外望去,只见外面狂风大作。海面上到处是海马。我暗自思忖,我的朋友普莱尔帕尔默伯爵此刻正带领一支坦克营泅水渡海,我想到了上帝,乘着这架飞机,而不用待在泅水坦克里参战,我真是三生有幸。
我们总算到了目的地上空,到处都是高射炮火。高射炮并不是独独冲着我们这架飞机来的,但很猛。因此,红灯一亮,我已做好准备。绿灯一闪,我就操起砖头和画了希特勒头像的足球。该我跳伞了。你得为自己定一个位,记得当晚多云,但月亮刚刚穿出云层,足以方便我定个位。糟糕的是,我落进了迪沃山一片淹没的山谷,远在原定降落地点2到3英里外,我落进了4英尺半深的水中。稍稍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后,记得我听到了第一声枪响。听到第一次交火时,我还泡在水中。随后发现,是我手下的一名卫兵误射了另一名卫兵的大腿。这么一来,我又多了一个累赘。身为一名职业军人,我在作战服的裤子上部缝了60包茶袋,当然,茶袋除了泡茶,别无它用,我用了4个小时才蹚出那片水域,泡了一路的凉茶。
不过,降落在那片淹没的山谷和低洼地的人还有很多,有的沟深达10到15英尺,许多兄弟溺死在当天夜里。不过,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人手一根的帆索帮了大忙,我能救起和召集的人,全部拴在一根绳子上。
此外,这片山谷在淹没前设置了障碍物,因此,你还得一边蹚水,一
边防着水下的障碍,单凭自己一个人,你根本没办法通过,但要是借帆索一起往外蹚,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不管怎样,这些障碍没把我们怎么着。我们总算越过障碍,四个小时后,我们上了被水淹没山谷的岸,来到预定伞降地域的边缘。四个小时后,召集到和拴在一起的,连我在内拢共42个小伙子。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派原定攻占伞降地域的加拿大军拿下设在这一区域边缘的敌军最高指挥部,俘虏敌人军官;又派出一名军官查明了这里的方位。加拿大军占领了伞降区域,端掉了敌军指挥部,但附近的暗堡给他们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因此我想,对了,关键是要接近原定捣毁的炮台,梅维尔炮台。就这样,我带着一帮散兵游勇出发了,我始终记得,我派了两名军官,驾一艘安装了8英寸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在战斗最初的48小时火力协助我旅。他们来了,当然,还有我的一条空降狗,欢天喜地地跟着我和训犬员。就这样,我们出发了,天还没亮,刚刚转白,我们走在一条横穿泥泞的沼泽地的小路上。这是一条很窄的小路,是仔细查看了地图才找到的。我们赶往9营的阵地。没多久,军舰开了炮,你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美的焰火。场面振奋人心,但接着就不那么振奋人心了。一阵恐怖的噪杂声,我身经百战,知道这噪杂声是怎么回事儿,我们遭到了低空飞行的飞机轰炸,进退维谷,两边都是水。
我大喊一声,卧倒,我身边是9营迫击炮排排长,他扑倒在地。我扑在他身上,一声惊心动魄的巨响,一切都过去了。一枚200磅的炸弹,这绝不是闹着玩的,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遭到了轰炸。我意识到自己中了弹,灰尘和泥土裹着火药和死亡气息扑面而来。伤亡惨重,我一抬头,见路上有条人腿,我心想,老天,那是我的腿,接着我又看了一眼,腿上穿了只褐色的靴子,我不许手下的人穿褐色的美军跳伞靴,我知道,穿这种靴子的只有躺在我身下的彼得斯。这么说,那是他的腿,不是我的,我很幸运。活着的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我警卫排的排长,我压在身下的彼得斯当场阵亡,因此,我心想,你命真大。
四周躺满濒临死亡和身受重伤的小伙子,一名指挥官应该怎么做。是留下来照顾他们,还是继续前进,答案当然是,身为一名旅长,我只能继续前进。但走之前,我们为每一名伤员注射了他们随身携带的吗啡,又尽量从阵亡官兵身上找出一些,留给了生者。
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