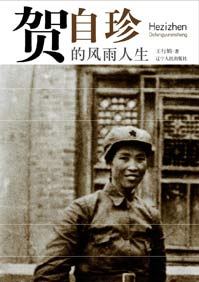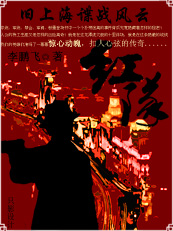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房门,让空气穿过安静的长长的走廊,自己端着一杯茶,走来走去地想,从前的老主人,一家人住在这里,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中午时分,大多数大楼里什么人也没有,你正好可以在那里出一会儿神,想想从前这里的整洁,晚上这里的拥挤。
也可以走到从前张爱玲在静安寺边上的公寓里,去看那里的电梯。五十年以前的电梯,听说从来没有换过,是老的奥斯丁。电梯还是走得很稳,只是如果你是在楼上的话,你看不到现在电梯正在几层楼,因为电梯的显示还是从前的样子,像半个钟面,每一层楼,在钟面上都有一个小红点表示着。一根红色的铁针在电梯上下着的时候,随着它的上升,慢慢地指到二楼,三楼。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它不再动了,红色的指针指到顶楼以上,它坏了。于是,等电梯的人把头凑到门边,靠听声音的大小来辨别它的方向。
在那里,听钢缆吱吱叫着,总是要想到从前那红针转动时候从容的样子,还有电梯在你要上去的那一层停下来时,那红针处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叮”。
要是你可以走到老公寓的里面,当然就看到更多的东西了,看到棕黄色的长条子地板,踩了八十年了,一打上蜡,还是平整结实,油光可鉴;看到厚重结实的房间门,褐色的好木头,上面的黄铜把手,细细地铸着二十年代欧洲时髦的青春时代的花纹,用了上百年了,还纹丝不乱;看到浴间有妇女专用的清洗盆,水流像喷泉一样从下而上;看到走廊的一面嵌在墙里的穿衣镜,在暗处照着人,水银定得那么好,玻璃压得那么平,隔多远照人,也不走样——
那时候,真的从心里要说一句:从前的上海,是有过精致的好日子啊。
只是你真的走在那里面,坐在那里面,还要闻到陈年的油气,旧木头气,灰尘气,食物气,马桶前面的一小块地方日久积累下来的尿臊气,浴缸下水泛出来的肥皂水汽;你还要看到高大雕花的天花板上黑白莫辨,花纹里全是灰尘,像耳朵眼里全是耳屎,宽大的厨房里通体全是黄褐色的陈年油烟,遇上的灰尘,就在上面一缕缕地吊着,像圣诞树上挂小东西的绳子——
那时候,也是真的从心里要说一句:怎么把房子住成了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最喜欢在初冬的雾夜,街上的人静下来以后,自己骑着自行车在老城一带慢慢逛,他说,那时候,夜色把老房子的颓败掩住了,雾模糊了许多东西,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走在几十年以前的上海,一切都是新的,好的,美丽的。他就是那一类上海怀旧的年轻人,心里满是为自己故乡而起的沧桑。他们当然也知道怀念租界时代是不对的,于是他们不说这个词,他们说“三十年代”。
上海的每栋老房子的拆除,淮海路被移走的每棵梧桐,美国快餐在上海的每个分号的开张,他们都是最坚决的反对者。
有时候他们不被年老的上海人所理解,有一个在上海最繁华的时期在法租界住的老上海就说过,那时候他在街上玩,堵了走过来的外国人的路,曾被那个人“去”的一声,好像是赶狗。那个声音给了少年的他深深的侮辱,所以他说,不知道那样的心情,怀什么旧。
是的,看上去,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真正看到过从前的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没有真正生活在那样把外国人当作一等公民的故乡,他们怎么可以怀旧,又凭什么怀旧呢。
现在的孩子,没有看到外国人是怎么欺负中国人的,也没有看到从前的社会到底有怎样的不平。他们看到的是从前留下来的房子,是最美的;从前生活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是最精致的。而他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女人没有香水、男人不用讲究指甲是否干净、街道上没有鲜花的匮乏的时代,所以他们就这样靠着对旧东西的想象而成了怀旧的人。
这城市破败而精美的建筑,就是他们怀旧的理由。
。 想看书来
房屋十年记(1)
我写《1993年上海大拆屋》时,街上成堆的建筑垃圾和路边翻修到一半的房子,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标准风景。我最记得那些正在翻修的房子,应该说它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房子,工人们忙碌着拆除房子上的违章搭建,加固摇摇欲坠的阳台,清洗外墙上几十年的积尘,那些房子,隔着毛竹搭起来的脚手架看,好像一张女人的脸,上面还留着撕到一半的面膜。修到一半的房子,特别是外墙粉刷到一半的房子,有种狼狈而惊愕的表情,那个表情极像面膜卸到一半被人撞见的女人。这样的风景,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
就在那时,偶尔路过了徐家汇。偶尔见到从来都紧闭门窗的修女院,竟然大门洞开。我为此大吃一惊。那里是天主教修女的静修院,一向与世隔绝。小时候,我来这里参观万婴墓的时候,曾听到过她们唱圣诗的声音。小孩子很怕修女、教堂和神父,以为他们背地里都喜欢吃小孩的眼睛。路过修女院时,女孩子们都紧紧挤在一起,全身的鸡皮疙瘩。这时,从涂满黑色柏油的篱笆后,传来了修女们的歌声。女孩子们被歌声惊吓到,像一群鸟一样尖叫着,四下逃去。那时我很小,但因为曾经吓得要死,所以一直记得那个修女院。
在接近修女院时,我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褐色木门上,钉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谢绝访客”,那字写得端庄谦卑,使人想到五十年以前的人。经历过*的大字报运动以后,中国毛笔字里这种清秀恭敬的精神,已经永远消失了。
直到已经来到了宽大的走廊里,直到从修女们的小图书馆窗前,再次看到那道涂了黑柏油的篱笆,我还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走进修女院来了,直到我看到木门上贴着的耶稣像。画片上的耶稣是如此清秀温存的青年男子,如此充满爱意,却丝毫没有男人的进攻性。我在翡冷翠乡间的小教堂里也见到过类似的耶稣像,那时只觉得意大利人的可爱,可在这老修女宿舍的门上再见,却突然被感动了。这耶稣,让人只想爱他,怜惜他,追随他。修女们几十年在这大房子里静修,从不出门,直至老死。原来,就是这样的耶稣陪伴着她们的漫漫一生。推开房门,里面已经搬空了。徐家汇渐成闹市,于是,修女们搬离,教会将修女院租借给了商家。这就是我可以走进来的原因。
房间里很暗,因为关着木头百叶窗。那木头百叶窗早已腐朽,几乎散架,所以只能关着,靠窗框的力量维持它们不散架。
房间里还残留着老女人干燥的气息和处女的洁净与单调。墙上的涂料已褪尽了,裸露出涂料下面的水泥。水泥也龟裂出无数细小的裂缝了,让人想起满是皱纹的手背。壁炉早已废弃,天花板如今是深灰色的,高高吊下来直接插在塑料插座上的灯泡。老修女们在自己床头贴了更多耶稣和圣母的画片,画像上的圣子和圣母,都有比拉斐尔笔下甜美得多的眼神。那不是艺术中永恒的神圣,而是人间轻抚人心的甘甜与完美,它们更像年画。如今单人木床搬走了,被遗留在床头墙上的旧画片,因为显得哀伤,而神圣起来。那时我想,要是修女们了解到那些小女孩当初是如何的怕她们,她们会怎么微笑一下。
修女宿舍和小图书馆的尽头,是她们的小礼拜堂。在空无一物的小礼拜堂里,我竭力回忆小时候听到过的歌声。她们是在这里唱的吗?这里让我想起意大利乡间那些温存明朗的小教堂,这里有种多年修女们祈祷的歌声遗留的温存气氛。有些小教堂,比著名的大教堂更能保留祈祷时人心的善意和诚挚,因而保留着一团暖意。如今,我依稀能感受到修女们的歌声,它像回忆中的某种精神性的物质,你能感受,但无法触摸,也无法形容。我那时突然想,也许女孩子们尖叫着四下逃散,并不是真的害怕,而是感到了歌声的诱惑。
房屋十年记(2)
过了几个月,我再去修女院,已不得不沿着门口一大堆沾满建筑灰尘的电线走进去,整修开始了。教会派来看大门的老教友,此刻已被满面尘灰的装修工代替。就像当年老教友一定要我得到教会的许可,才能参观搬空的修女院一样,工人也一定要我得到东家的许可,才可在工地走动。于是,我见到了修女院的新东家,恒寿堂餐馆的老板。他是个谨慎的男人,问了许多问题,直至他看到我工作证上的名字,确定我写过《上海的风花雪月》,才起身,握手,亲自陪我去工地参观,并建议我在觉得合适的时候一定也写点这个房子的历史,并向我保证他不会破坏这栋房子,只会将它小心复原,使它更好看。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特地带我去了小图书馆。所有的百叶窗都集中在这里,由专门的工人修复。他点给我看绿色百叶窗上的贴条,小贴条上注明了每扇窗是从哪里拆下来的。
“也许我可以在原先的会客间里做一个小博物馆,展出这房子的原貌和历史。我收集了一些实物,还到档案馆去买了些照片回来。我知道老房子的价值。客人们等吃饭时,就可以先到小博物馆来看看。”他说,“小博物馆还可以出售老东西,要是客人觉得好,随手就能买回家去。”
“你还可以做些明信片。”我提议,“我读过一本台湾出版的书,名字叫一栋老房子的生命史,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其实,是我自己想为这栋房子做这件事。那些绿色的百叶窗将装回到窗台上,那些墙上的耶稣画片将消失在餐馆包间平整的墙上,那个温柔的小教堂将成为一间高级宴会厅。这栋老房子的生命史,如乱世中的人生一样充满转折,无法料想。
“明信片,是的。”他点头同意,突然笑了,“想想看,邮局里到处都是我们餐馆的明信片,传来传去。”
他带我经过走廊,去了后院,那里的篱笆已经不见了。
我这是第一次来到修女的园子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玻璃暖房,里面种着瘦小的玫瑰树。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一块黑色大理石碑倒在地上。然后,我认出来,它就是小时候我见到过的万婴墓的墓碑。整个童年时代,令我印象最深的旧上海,一是外滩的洋行大楼,二就是这块黑色的墓碑。我又感受到记忆无声的深处,修女们的歌声,以及小女孩们穿透树阴的尖叫声。它们如同关节那样,将这栋房子的过去和将来连接在一起,并让它们转动自如。
他说,他知道怎么小心修复所有的百叶窗,保留当年造房子时所有从欧洲进口的地砖,但不知道怎么处置这块墓碑。
“你可记得小时候的忆苦思甜教育?来这里参观育婴堂。”他问我。
是的。所以我说:“大概你可以将它放在花园里,再做一块碑,放在它前面,来说明它。”
他看看我,我想他以为我在说反话,但我却真没有。
临走时,他诚恳地给我名片,邀请我再来,他许诺会给我一张贵宾卡。
又过了几个月,我再次去修女院,那里已是上海老站餐馆了。当年修女们用的大厨房,现在是餐馆的厨房。跑菜的男孩们在那里穿梭不停。餐馆经营的是改良的上海菜。与他规划中的一样,走廊里当年的瓷砖都还在,而且已经擦洗一新。百叶窗都回到原来的位置,而且可以轻松地开关,小教堂保留了墙上原先的玫瑰花图案。我在二楼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