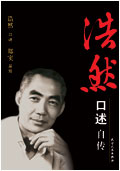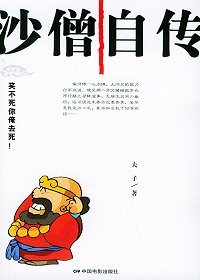浩然口述自传-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着我的头脑,使我难以忍受,更难以心情平复。
待几个青年干部把不满发泄完,告辞走了。我闷闷地坐了片刻,思考了一下,就捻亮油灯,铺上稿纸,一气起草了一篇题名《自己的“幸福”,别人的痛苦》的讽刺性小品文。
在这篇小品文里,我作了尽情的发泄,指名道姓,把刚刚听到的有关小秀的不道德的恶劣行为,全部暴露抖搂出来,给予了义正辞严的批判。当然把她勾引我的事隐去了……因为那事虽然没成事实,可传扬出去,对一个省报的新闻记者来说也不太好听,容易引起人们的胡乱猜想,影响我的名誉。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9)
对那件事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关键性的细节,我写文章时,有意识地做了手脚,省略了真相,完全是从自我出发,完全是为了维护自我而为的。这个秘密一直隐瞒了四十多年,同时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从来没有想过在小秀勾引我的这件事情上,我有没有责任。完全没有想,当时没有想,过几十年仍然没有想。1993年夏天我突然中风,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转移到密云水库的“云水山庄”休养的时候,有一次,一位一起在密云工作的老同志来看望我,谈起旧事,提到小秀。他说小秀还活着,活得不怎么样,当年挨了批评,受了处分,就下放到一家刚合营的手工业作坊当工人,直到年老退休。我听到这话,突然间在脑海里冒出一种“后怕”的情绪。当年,只凭着青年人的气盛就写了那篇指名道姓批评暴露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以后,小秀若是想不开而自杀,岂不是形成个始料不及的过失?虽然我也不会为此而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我写文章原本只求起到警告作用,不愿意造成这种悲剧!我不能不反省、不能不正视那场短促的纠葛,我意识到应该考虑自己的责任。假如我那时候没有“闹离婚”,没有“骑马找马”地寻找新的对象,就不可能对小秀萌发不该有的杂念。杂念萌发了,定会有所流露,丝毫不应有的杂念的流露,对不规矩的小秀来说,都是一种鼓励,她才会有“故技重演”的动作。我只批判小秀而不肯自省,并心安理得了几十年!人的自知之明如此难以做到,人的自私自利意识和下意识能够自欺欺人到如此地步,实实的可怕呀!而且,当年写那篇小品文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抨击那种不道德现象,而不宜针对某个具体的人。为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采访完,从密云回到采访组,收到妻子的信。信上写道:……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的工作顺利吗?我还上民校,入了团,孩子学会说好多话。我给你做好了一双鞋,是我给你送去,还是给你邮去?你来信说明白。你要小心身体,不要老想那件事。那件事你一定要那么办,我也不难为你,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你高兴就行。我就带着孩子在家里过一辈子,饿不死……看到这儿,好似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我的心脏使劲儿地揪扯了一下,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两眼一阵子发黑,脑袋嗡嗡作响。
几个月来,心紧似铁地拒绝和我离婚的妻子,今天这封亲笔书信,却突然松动了,表现出出乎意料的灵活性。事实上,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向我退让了:你一定要离婚,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带着孩子在家里过下去……
凭着我对妻子为人和性格的了解,她这样地把话说出来,她就一定会这样做。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刚刚两岁的孩子,在那偏僻的靠山小村熬日子、守活寡,这是一条多么苦难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呀!她是在封建意识很浓的家庭里长大的,接受的是“三从四德”、“好女不嫁二夫郎”的教养,加上农村当时那十分严重的旧风俗和旧习惯势力,如果我们真的离异了,她绝不会再另嫁他人,她会留在王吉素村,守着儿子过。同时她那固守老传统、老规矩的父母和至亲们,也一定会支持她走她选择的这条路,不容许她选择新的路子,对于已然固定了的生活模式,绝对不可逾越和有所更改。因此,可以料定,她的人生道路至此就算定了型,今天就是她的今后。今后的她,今后的她们母子,那岁月将会是何等的凄凉和悲惨?
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就是因为父亲缺少正气和志气,有了外遇而不顾妻子儿女,不仅毁了他本身,也连累了我们。如今,我在婚姻问题上也产生了喜新厌旧的思想,这不是在父亲那条毁灭之路上重蹈覆辙吗?
我前思后想,越思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行为可怕,越想越觉得后果悲惨,因此越发悔恨,到了后来就抑制不住地趴在床上,无声地而又不断地流淌起泪水。
我给妻子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我问候她,问候岳父,问候岳母,问候我们的儿子。同时告诉她,那一双为我做成的新鞋不要邮寄,也不要送来,抽空我将请几天假,专程回家去取。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0)
在那封信上我没有表示忏悔,没有说一句“不再闹离婚”的话,一切一切,我都想用实际行动去体现:实际行动就是我痛改前非的决心。我的决心是此生此世再不跟妻子闹离婚!
不久我赶回蓟县那靠山小村家中去探望,跟妻子和儿子度过几天最热烈、最甜蜜、最愉悦快乐的日子。
很庆幸我那一次的翻然悔悟,保全了这个家,保住妻儿没受伤害,也保证了我自己在难逢的人生花季,应时地接受了雨露阳光的滋养,没有蹉跎岁月,没有悔恨终生。
6
由于一次采访失败,我被撤销了新闻记者职务,被驱逐出记者科,“戴罪”发配到读者来信科,干拆阅信件的工作。
读者来信科被人认为是整个编辑部最末流的科室,安排到这个科工作的人都是一些被照顾的病号或有孩子和家务拖累的妇女,以及那些刚从中学分配来不能担负正式工作的小青年。
干这种工作的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男性,其他同事无一例外地都是有小孩子的妈妈,又几乎都是楼上各科男编辑和领导干部的家属。只要下班铃声一响,她们就急急忙忙奔向北院的家,忙起她们的家务。我在办公室附近的公共食堂用餐,到同样距离不远的集体宿舍睡眠。在一块儿吃饭的都是没有家的印刷车间的工人,在一块儿睡觉的都是勤杂人员。我们做着不相同的事情,想的问题不一样,自然也没有共同语言。白天一上班就工作,晚上回屋就睡觉。同室住的那些没有事情做也没烦恼的单身汉们,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有的聊大天,有的讲笑话,无聊而又嘈杂。这情景常常使人烦躁得想从床上跳起来,骂他们一顿,打他们一顿,把他们一个不剩地都赶出去,只留下我一个人安静安静!
我没法读书写作,也没情绪读书写作,勉强地捧起书本,也总是走神儿,看不清字行,眼前只有黑糊糊的铅字,只有模糊的一片。我赌气地扔开书本,倒头大睡,睡不着就胡思乱想。
以前我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睡不着也想事儿。但是那时候想的都是读过的一些书籍所给我的某种思想启迪,可以深深追究的问题,或生活中看到的新鲜事件,遇到的独特和有趣的人物。现在睡不着,想的都是那些想不通的苦恼问题。越想不通越苦恼,越苦恼越想不通,最后只剩下苦恼的空虚,空虚的寂寞和无聊。寂寞无聊得特别害怕孤独,实在孤独得害怕。在这种情形下,就想家,如饥似渴地想家。如今我的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没了,然而可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完整无损的家,家里有个完全忠贞于我的贤惠勤劳的妻子,还有个伶俐健康又活泼可爱的儿子。在此时此地此种情形之下,唯有他们才是我精神的靠山和寄托,他们会给我急需的安慰和抚爱,使我逃避痛苦的风暴,有了安全港湾……
最后,我终于起了在保定、在身边安个温暖小窝的心意。于是立即出去租房,然后给妻子写信,让她先到北京,在那里换火车。
妻子既是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也是第一次来到首都,于是我特意在等乘火车的空隙陪她参观故宫博物院。我兴致勃勃地当向导,给她讲解我所知道的古迹。不料妻子对此毫无兴趣,走过一层大殿,就坐在玉石的台阶上说,你爱看你去看吧,我在这儿等着你。我说,我是专门陪你出来参观的呀!她说,这些没用处的老古董玩艺,喜欢也不能买,看一眼就行啦,腿走得太累……我听了这句话哭笑不得,只好扫兴地走出天安门,抱着儿子跟妻子一起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当天赶到保定。从此,我的妻子离开了生养她的那块黄土地,我也结束了只身漂泊的生活。除王吉素那古老的砖石房以外,我又有了自己的窝巢,自己的家。妻儿给这潮湿阴暗的房子带来了温馨、光明,使这个狭窄低矮的房子变成能够容纳我躲避羞辱、忘却孤寂、养愈精神创伤的所在,成了我独有的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
7
不久,我被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工作。我的女儿春水也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喜鹊登枝》一起,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1)
“大跃进”已然在中国大地开始了。“不为金钱而为共产主义写作”,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心声和行为。很多大作家在报纸上公开倡议降低或不要稿费。《喜鹊登枝》正在这时候出版发行,恰恰是赶上第一批降低了稿酬的新书。即使如此,我这本书还是得到每千字十元钱,没有印数稿费,得一千一百元钱。这是我平生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钱到手里以后,欢喜之余,我首先想到了那位给我“生了儿、养了女”的妻子。
节俭,是妻子一直保持不变的习惯,也成了她性格的组成部分。她的这种作风,不仅给儿子有榜样的作用,就是对我也同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用电,不论是安装上分户电表,还是按灯头数量收费,天色不黑到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谁也不准许开灯;事情办完,人走开一小会儿,也得把灯关掉。比如使水,不管公家花水费还是自家花水费,洗筷子洗碗,都得把水打到盆子里,用盆子里的水一遍一遍地清洗,决不允许把水龙头一拧开,哗哗地放着水,拿着碗筷一件件冲涮。吃剩下的菜与饭,从来不肯轻易倒掉,即使已经有点馊味儿,也要放些碱面,重新煮一煮、热一热,全部要吃进肚子里去。衣服更是坏了补,补了穿,一条棉裤的里子起码得由十块各种颜色的旧布片拼凑而成。身边的鞋子只有两双:一双棉鞋,一双夹鞋;破到再不能穿的程度,才肯买新的……
在《河北日报》所在地保定居住的时候,我曾经催她多次,并亲自陪她到商场里转悠了好几趟,她才买了一双廉价的黑皮鞋,扯了一块最普通的花洋布,亲自缝制一件旗袍穿在身上。我为了显着气派一点儿,拍照的时候,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给她戴在腕子上,把她别扭得胳膊都不知道怎么放。调到北京以后,住进了大楼,楼上还有外国人,妻子仍然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惯,不论吃的用的,特别是穿的戴的,依旧十分土气。
为这个,我很不满地对她说,你应该讲究点儿打扮啦!
妻子很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身上不光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