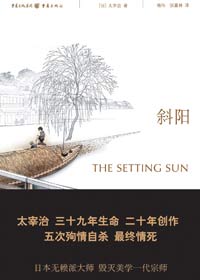�-��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ھƹ�����һ��İ���Ļ����������ֻ�п־塣�Ҿִٵذ���ֻ�첲һ����������һ�����ɿ���¶��һ�������Ц���ɾ���������ơ�����֮����ȴ�е���һ������ġ�����˽���Ƶ����ɡ�
������������ĥ���������ѧУ�ţ����ǡ�����
��������ѽ����û�����ţ����ֵط�����û�����ˣ����ǵ���ʦ���Ǵ�������Ȼ֮�У����������Ƕ���Ȼ�ļ���֮�У���
�������Ҷ�����˵�Ķ���ȴû�ие����ľ��⣬ֻ�ǰ���˼������Ǹ����������Ļ��ض�������������Ϊһ����ˣ�Ļ�飬����������õ���ѡ����ʱ���Ҳ���ƽ��һ�μ�ʶ��ʲô�����ʸ�Ķ���Ʀ�ӡ��������ұ�����ʽ���ྶͥ�����ڳ���������������Ӫ��֮�⡢��㯶�������һ���ϣ��Ͼ�����ͬ�ࡣ���ң�����������ʶ֮��ʵʩ�Ŷ�Ц�ij����Ϊ����ȫȻû�о��쵽���ֳ����Ϊ�ı��ҡ����������������ڱ�������Ȼ����ĵط���
������������һ�����棬�����ǰ���������Ļ���������������������������������������������������������еĹ����У����Լ�ȴ�����������°ܽ���
���������һֱ��Ϊ���Ǹ�����ˣ�һ���ѵõĴ���ˡ��������˸е��־���ң�Ҳ�������˾����ԣ���Ϊ�ҵ���һ�������Ҽ�ʶ�����ĺ���˵ʵ�����������Ҫ��ȥ�����糵�ɣ��ͻ����ƱԱ����Ҫ��������輿�糡ȥ���ưɣ�һ�������ſڲ���ͣ�������ź�ɫ��̺�Ľ����������·С�㣬���ֻ����η�壻Ҫ�ǽ��ݰɣ�һƳ������վ���Լ����������ʰ���ӵ���Ӧ�������ֻᵨս�ľ������ģ��ر��Ǹ�Ǯ��ʱ������˫����ΡΡ���֣����������˶���֮��Ǯ�ݸ��Է�ʱ��������Ϊ����С����������Ϊ���ȵĽ��š����ȵĺ��������ȵIJ�����ֲ���ֻ�����Լ�ͷ���ۻ���������Ȼ������һ�ţ��������ҵ��ļ��������˰����״̬�����ﻹ�˵����ּۻ��ۣ���ʱ���������˽ӹ�����Ǯ���ֻ��������µ���Ʒ���Ҹ���������һ���ڶ�����ͷ��������ֻ�����������ڼ��д�����txt���������ƽ̨��
���˼�ʧ���ּ�֮����6��
��һ����Ǯ������ܥľ��һ��ȥ��֣����ξʹ���ͬ�ˣ�ֻ��ܥľ��������ɱ�ۣ�ٲȻ����ˣ���мң�ʹ���ٵ�Ǯ���ӳ����Ĺ�Ч�����ң����Խ�ͷ����ij�������һ�ž���Զ֮��������˵س����糵�������������ֻ�С����ͧ�����ֳ�һ��������̵�ʱ�����ִ�Ŀ�ĵصı��졣��������ʵʩ�ֳ�ʾ�������������峿�Ӽ�Ů�Ƕ��ؼҵ�;�У�˳·�յ�ij���ùݣ���һ���������һ�߳Զ���������һ�ߺ������ľƣ��ⲻ�����˻��㣬���Ե������ݻ������������ң�̯������ţ��ǽ����Ϳ����������Ǯ���˶��Ҹ���Ӫ�����������а��յض��Ե��������еľ��м䣬Ҫ�������صľƾ���������������͡��ڽ�����ʱ��������Ҳû�����Ҹе�һ�ǰ��IJ�����η�塣
������ܥľ��������һ��ô����ڣ�ܥľ��ȫ����̸���Է����뷨��ֻ���Լ���ƾ��ν�������ʹ��������ν�ġ����顱������Ҫ���ӶԷ��������������쵽������߶���������ĵĻ��⣬���ԣ���ȫ�ò��ŵ����������ڹ��ƣ����֮����������εij�Ĭ֮�С������˽���ʱ���������ģ�����Ψ�ֳ������ֿ��µij�Ĭ���棬���ԣ������챿���ҲŻ�ƴ���ذ��ݳ���Զɹ��ѹء�Ȼ������ǰ���ɵ��ܥľȴ���������������������ֶ�Ц�Ļ�����ɫ�����ԣ��Ҳ��ܹ������Ļ��������ţ������Ӵ�����ֻҪ��ʱ�ز�ƴ�ڻ������Ӧ���ˡ�
�������ã���Ҳ�����������ˣ��ơ����̺ͼ�Ů�����ܹ���������ʱ��ȴ�˵Ŀ����Եľ����ֶΡ��������ȷ����������뷨��Ϊ��Ѱ����Щ�ֶΣ����������Բ�ϧ�����Լ������мҵ���
�������������Ů������࣬�Ȳ����ˣ�Ҳ����Ů�ԣ������ǰ׳ջ��߿��ˡ������ǵĻ�����ҷ����ܹ��������ǣ���Ȼ���ߡ�����û��һ���������������ֱ�ﵽ�����˱����ĵز��������Ǵ����������һ��ͬ������аɣ���Щ��Ů�������ұ�ʾ����Ȼ��ɵĺ��⣬���Ӳ����˸е��ִٲ������������֮�ĵĺ��⣬������ǿ֮�ӵĺ��⣬��Ƽˮ���֮�˵ĺ��⣬ʹ����������ҹ֮�У��Ӱ׳ջ����ʽ�ļ�Ů���Ƕ������еؿ�����ʥĸ�����ǵ���ʥ���
����Ϊ�˰��Ѷ��˵Ŀ־壬���һҹ֮�����������ǰ����������ɾ�������Щ�����Լ���ͬ�ࡱ�ļ�Ů���ֵĹ����У�һ������ʶ�������Χ��ʼ��֪���������������ܣ�����������Լ�ҲȫȻû�����뵽��������ν�����ӵĸ�¼�����������ǡ���¼���������ֵ�����֮�ϣ������ڱ�ܥľ�㴩�����е��������Ҳ������Ȼ֮�࣬�����������˿��������˵��ͨ��һ�㣬������ͨ����Ů�����й�Ů�˷���������������������ij�������˵��ͨ����Ů��ĥ����Ů�˽����ı��죬����Ϊ����Ҳ��г�Ч�ġ��ҵ���������Ư����һ�֡����³��ϵ����֡�����Ϣ��Ů���ǣ����������ڼ�Ů��ƾ�豾���ᵽ��������Ϣ������֮���͡����Ǿ�����������ġ�������ʵķ�Χ�������ҡ����ӵĸ�¼������������������ͼ��������ı����Եø�����Ŀ��
��������ܥľ�ǰ����е�˵���Ƿ����ģ���ȴ���в��Ҷ����е���ͷ������˵���Ҿ������յ����ƹ�Ů��д���ҵ��������飻����ӣľ��ھӽ������Ǹ���ʮ�����ҵĹ������ÿ���糿ר������ѧ��ʱ�䣬���¿�����ȴ������ʩ�����������Լ��ҵ���ǰ�����е���ȥ��ţ�ⷹʱ����ʹ��һ�Բ������Ƕ���ŮӶҲ�ᡭ���������Ҿ�����˵��Ǽ��������ӵ�С����ڵݸ��ҵ��̺��о�ȻҲ�������У���ȥ�����輿ʱ���Ǹ�������Ů�ˡ������У���������ҹ����Ӫ�糵����������������Ȼ��˯֮ʱ�������У����������ݼҵĹ����Ƕ��������ϵؼ�������繲������˼�ż��������У�ij����֪������Ҳ�Ĺ���������ʱ������һ���ֹ�������ż�ˡ����������൱�����˱ܣ����ԣ�ÿһ�ε�����ʷ�������ѵ�ˮ��ͣ����һЩ��ȱ�Ķ�Ƭ��û���κθ���Ľ�չ�����ǣ���һ��ȴ�����ſڴƻƵ���̸֮�������в��ɷ���ʵ�ԣ����������ϵ�ij���ط�������ij�ֿ��Թ�Ů�����εķ�Χ������һ�㱻ܥľ�����ļһ����ʱ���Ҹе�һ�ֽ��������ʹ�࣬ͬʱ���ҶԼ�Ů����ȤҲٿȻ����֮��ʧ�ˡ�
���˼�ʧ���ּ�֮����7��
ܥľ���ڰ�Ľ���ٺ���ʱ�ֵ�������������Ҳ��Ϊ������֮�⣬��Ҳ�Ҳ����κα�������ˣ���ijһ�������ȥ�μ���һ������������������������о��ᣨ����ǽ�R��S�ɣ������ѼDz����ˣ���Ҳ����ܥľ����������˵����ϯ�������������###��Ҳֻ���������ҡ�������������һ�����ˡ��ұ����ܸ���Щ��ν�ġ�ͬ־����������������һ���������ӣ���������ϯ���Ǹ������ª�����꽲������˼�ľ���ѧ˵��Ȼ������һ�����ҿ�����ȴ�������ײ����������ˡ���������ȷ��֮�����������˵������������������һ�ָ������������Ķ�������֮Ϊ���������ɣ��־����Բ����⣬ν֮Ի�������ġ��ɣ�Ҳ�����ﲻ���壬��ʹͳ��Ϊ��ɫ������������Ҳ�Ծɴʲ����⡣��֮��������Ҳ�����������������Ϊ���������ĵײ�Ͼ�������ij�־��������Ǿ��õġ����ڹֵ�ʽ�Ķ���������һ�������ֵֹ�ʽ�Ķ������˺��µ��ˣ����ԣ������Ҷ�Ψ���ۣ�����ˮ���ʹ���һ����Ȼ��Ȼ�ؼ��Կ϶�����ȴ�����������������Ѷ��˵Ŀ־壬�Ӷ�������Ҷ���ܵ�ϣ����ϲ�á���������ȴ�Ӳ�ȱϯ�زμ�R��S����ƾ���䣬����������ͬ־����ٲȻ������ͷ�Ƶģ���������ף����������硰һ��һ���ڶ���֮��ij�������ʽ�������о��С������龰���Ҿ��û����������ǣ������Լ����õĶ�Ц���죬�Ի�Ծ###�ϵ����ա���������Ϊ���Ե�ʰɣ��������о��������־н��Ű�ķ�Χ�������ˣ��������ҳ����Ǹ�###�ϲ��ɻ�ȱ�ij������Щò�Ƶ�����������Ϊ�Һ�����һ���������������ҿ���һ���ֹ۶�ڶг�ġ�ͬ־����������ʵ������ˣ����ұ��Ǵ�ͷ��β�س�����ƭ�����ǡ��Ҳ��������ǵġ�ͬ־��������ȴÿ�αص���Ϊ��ҷ��׳���Ϊ����ǡ��Ķ�Ц����
����������Ϊ��ϲ����������ϲ�����ǡ����Ⲣ��һ���Ϳ��Թ��Ϊ��������˼������������������ܸС�
�������Ϸ������������СС����Ȥ����������˵ʹ���Ŀ���������ʵ���������ϳ�֮Ϊ���Ϸ�������Щ�����Ÿ��ӿ��£��Դ���Ԥ�е�ij���ޱ�ǿ�ҵĶ����������еĸ��ӹ�����Dz����������Ҳ�����������һ��û���Ŵ��ĺ��䷿�������������һƬ���Ϸ��Ĵ���ҲҪ����������ȥ��������������ȥ����Ҳ�ĸ���Ը��
������һ��˵���������������˵��ˡ�����ָ������Щ�����䱯�ҵİܱ��ߡ������ߡ��Ҿ����Լ���һ��������һ�����������˵��ˡ�������һ��������Щ�����˳�֮Ϊ���������˵��ˡ����ҵ��ľͲ��ɷ�˵�ر�����������ˡ������ҵġ����ᡱ����ʹ���Լ�Ҳ���������
��������һ��˵��������������ʶ��������������ϣ���һ������������ʶ����ĥ������ȴ�����������빲���㿷֮�ޡ�����������һ�𣬽�����ŵ���Ϸ���ѹ����������淽ʽ��һ�֡����ﻹ��һ��˵���������������˺ۣ�û�������ˡ������һ���������ʱ���ҵ��˺۱��Ѻ�Ȼ�������ҵ�һֻ���ϣ����ų�����ˣ��ǵ�û�������������ս��Ӿ磬������չ���˹������ÿҹ��ʹ�����ͬǧ���ĵ��������ǣ�˵��Ҳ�֣������˿�ȴ��ñ��Լ���Ѫ�Ҫ�����䡣�˿ڵ���ʹ�����ҿ����ͷ·����˺ۻ���������У��ֻ�������һ�㡣����������������˵�������˶�С������ַ�Χ�Եó�������˰��ĺ���⡣��֮������˵�����˶�������Ŀ�ģ�����˵�����˶�����Ǹ��ʺ����ҡ�ܥľ�����dz������ź�������������Ҵ����Ǹ�###�����ҽ������ҡ���ʵ��Ҳ��ֻȥ����һ�Ρ�����˵��һ���ӵ���Ƥ����������˼���������о�������һ�����ͬʱ��Ҳ�б�Ҫ�۲�������һ���������������ȥ�μ�###������һ����˼����קס�ҵ�����ȥ��������״����������������ʱ�����Ÿ�ʽ����������˼�����ߣ�����ܥľ�������ڰ�Ľ���١���ʱ�ֵ�������ڼΪ����˼�����ߵ��ˣ�Ҳ������һ��������Ϊϲ�����֡����Ϸ����ķ�Χ����һͷ�������е��ˡ��������ǵ���ʵ��Ŀ������˼�����������ͽʶ�ƵĻ�����ô��������ܥľ�������Լ��������ɻ�����ǵķ�ŭ���𣬲���Ϊ���ӵ���ͽ���ܵ�����ɡ����Һ�ܥľȴû�����ܿ����Ĵ��֣��ر��������Dz��Ϸ��������У���Ȼ������ʿ�ǵĺϷ������и��Ե���Ȼ�Եú��������࣬���Ե���ν�ġ�����������������Ϊǰ;�����ġ�ͬ־������ί�������ֹ��������ǿ��ŵظ���Щ��������һ����



![ǧɽ��б��[��һ�����ϳ�ƪ] (��Խʱ��)BY �����¹�ʤѩ����](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