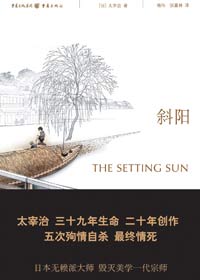斜阳-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间失格》手记之三(17)
我被那个有些腼腆地微笑着的年轻医生带着,进入了某一栋病房。大门上“咔嚓”一声挂上了大锁。原来这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去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我在服用巴比妥酸时的胡言乱语竟然奇妙地化作了现实。在这栋病房里,全部是发疯的男人。甚至连护士也是男的,没有一个女人。
如今我已不再是罪人,而是狂人。不,我绝对没有发狂。哪怕是一瞬间,我也不曾疯狂过。但是,据说大部分狂人都是这么说的。换言之,被关进这所医院的人全都是狂人,而逍遥在外的全都是正常人。
我问神灵:难道不反抗也是一种罪过吗?
面对堀木那不可思议的美丽微笑,我曾经感激涕零,甚至忘记了判断和反抗便坐上了汽车,被他们带进这儿,变成了一个狂人。即使再从这里出去,我的额头上也会被打上“狂人”,不,是“废人”的烙印。
我已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我已彻底变得不是一个人了。
来到这儿时,还是在初夏时节。从镶有铁格子的窗户向外望去,能看见庭院内的小小池塘里盛开着红色的睡莲花。又是三个月过去了,庭院里开始绽放出波斯菊花了。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家的大哥带着“比目鱼”前来接我出院了。大哥用他惯有的那种一本正经而又不失紧张的语气说道:“父亲在上个月的月末因患胃溃疡去世了。我们对你既往不咎,也不想让你为生活操心费神,你什么都不用做。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尽管你肯定是依依不舍的,但必须得离开东京,回老家去过一种疗养生活。你在东京所闯下的祸,涩田先生已大体帮你了结了,你不必记挂在心。”
蓦然间故乡的山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废人。
得知父亲病故以后,我越发变得萎靡颓废了。父亲已经去了。父亲作为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心际的、一种又可亲又可怕的存在,已经消失而去了,我觉得自己那收容苦恼的器皿也陡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我甚至觉得,自己那苦恼的器皿之所以曾经那么沉重,也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于是我顷刻间变成了一只泄了气的气球,甚至丧失了苦恼的能力。
大哥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对我的诺言。在从我生长的城镇坐火车南下四五个小时的地方,有一处东北地区少有的温暖的海滨温泉。村边有五栋破旧的茅屋,里面的墙壁已经剥落,柱子也遭到了虫蛀,几乎再也无法修缮了。但大哥却为我买下了那些房子,并为我雇了一个年近六十、长着一头红发的丑陋女佣。
那以后又过去了三年的光阴。其间我多次奇妙地遭到那个名叫阿铁的老女佣的强暴。有时我和她甚至还像一对夫妻似的吵架顶嘴。我肺上的毛病时好时坏,忽而胖了,忽而又瘦了,甚至还咯出了血痰。昨天我让阿铁去村里的药铺买点卡尔莫钦①,谁知她买回来的药和我平常服用的那种药,其药盒子在形状上就大为不同。对此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可睡觉前我连吃了十粒也无法入睡。正当我觉得蹊跷时,肚子开始七上八下的,于是急急忙忙地跑进厕所,结果腹泻得厉害。那以后又接连上了三次厕所。我觉得好生奇怪,这才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装药的盒子,原来是一种名叫“海诺莫钦”的泻药。
我仰面躺在床上,把热水袋放在腹部上,恨不得对阿铁发一通牢骚。
“你呀,这不是卡尔莫钦,而是海诺莫钦呐。”
我刚一开口,就哈哈地笑了。“废人”,这的确像是一个喜剧名词。本想入睡,却错吃了泻药,而那泻药的名字又正好叫海诺莫钦。
对于我来说,如今已不再存在什么幸福与不幸福了。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在迄今为止我一直痛苦不堪地生活过来的这个所谓“人”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视为真理的东西,就只有这一样。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今年我才刚满二十七岁。因为白发明显增多的缘故,人们大都认为我已经四十有余了。
后记
我与写下上述手记的狂人,其实并不直接相识,但我却与另一个人略有交情,她可能就是上述手记中所出现的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是一个个头不大的女人,脸色苍白,细细的眼睛向上挑着,高高的鼻梁给人一种硬派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美人,不如说更像一个英俊青年。这三篇手记主要描写了昭和五至七年那段时间的东京风情。我曾在朋友的带领下顺道去京桥的酒吧喝过两三次加冰的威士忌酒,当时正是昭和十年前后,恰逢日本的“军部”越来越露骨地猖獗于世之时。所以,我不可能见到过写下这些手记的那个男人。
《人间失格》手记之三(18)
然而今年二月,我去拜访了疏散在千叶县船桥的一位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所谓学友,现在是某女子大学的讲师。事实上,我曾拜托这个朋友给我的一个亲戚说媒,也因为有这层原因,再加上我打算顺道采购一些新鲜的海产品给家里的人吃,所以,我就背上帆布包往船桥出发了。
船桥是一个濒临泥海的大城镇。无论我怎样告诉当地人那个朋友家的门牌号数,因为是新搬过去的缘故,也没人知道。天气格外寒冷,我背着帆布包的肩膀也早已疼痛不已,这时我被唱机里发出的提琴声吸引住了,于是我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大门。
那儿的老板娘似曾相识,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十年前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似乎也马上想起了我似的。我们彼此都很吃惊,然后又相视而笑了。我们没有像当时的惯例那样彼此询问遭到空袭的经历,而是非常自豪地相互寒暄道:
“你呀,可真是一点也没变呐。”
“不,都成老太婆了。身子骨都快散架了。倒是你才年轻呐。”
“哪里哪里。小孩都有三个了。今天就是为了他们才出来买东西的。”
我们彼此寒暄着,说了一通久别重逢的人之间常说的那些话,然后相互打听着共同的朋友那以后的消息。过了一会儿,老板娘突然改变了语调问我道:“你认识阿叶吗?”我说:“不认识。”老板娘走到里面去,拿来了三本笔记和三张照片,交给我说道:
“或许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呐。”
我的天性如此,对于别人硬塞给我的材料是无法加工写成小说的,所以,我当场便打算还给她,但却被那些照片吸引住了(关于那三张照片的怪异,我在前言中已经提及),以至于决定暂且保管一下那些笔记本。我说:“我回来时还会顺道来的,不过,你认识××街××号的××人吗?他在女子大学当老师。”毕竟她也是新近搬来的,所以她倒认识。她还说,我的那个朋友也常常光顾这家咖啡馆,他的家就在附近。
那天夜里,我和那个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决定留宿在他那里。直到早晨我都彻夜未眠,一直出神地阅读那三篇手记。
手记上所记述的都是些过去的事了,但即使现代的人们读起来,想必也会兴致勃勃的。我想,与其拙劣地加以添笔,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让哪家杂志社发表出来更有意义。
给孩子们买的海产品,尽是一些干货。背上帆布包,告别了朋友,我又折进了那家酒吧。
“昨天真是太感谢你了。不过……”我马上直奔主题,说道,“能不能把那些笔记本借给我一段时间?”
“行啊,你就拿去吧。”
“这个人还活着吗?”
“哎呀,这可就不知道了。大约十年前,一个装着笔记本和照片的邮包寄到了京桥的店里。寄件人肯定是阿叶,不过,邮包上却没有写阿叶的住址和名字。在空袭期间,这些东西和别的东西混在了一起,竟然神奇地逃过了劫难,这阵子我才把它全部读完了……”
“你哭了?”
“不,与其说是哭,……不行啊,人一旦变成那个样子,就已经不行了。”
“如果是已经过了十年,那么,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吧。这是作为对你的感谢而寄给你的吧。尽管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但好像的确是蒙受了相当大的磨难呐。倘若这些全部都是事实,而且我也是他的朋友的话,那么,说不定我也会带他去精神病医院的。”
“都是他的父亲不好。”她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所认识的阿叶,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话,不,即使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



![千山看斜阳[第一部·南楚篇] (穿越时空)BY 满座衣冠胜雪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