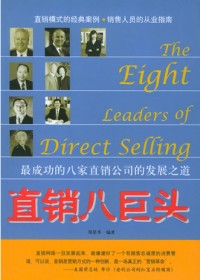王选的八年抗战-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80年代的日本,不仅仅只有一个森正孝。
1981年日本学者常石敬一从第二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军医少将等发表的《消逝的细菌战部队》的报告中,查明在活性出血热研究中所使用的“猿”,实际上是用中国人进行人体模型实验。这一发现无异于石破天惊。
1981年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在给《赤旗报》星期天版写连载小说《死器》时,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意外的发现让森村诚一万分震惊,为此他写下了长篇报告《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为了证明这些让人震惊的事情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得了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述,还查阅了原731部队干部的询问资料在内的美军的资料、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裁判的记录和原731部队干部的医学学术论文,将731部队令人震惊的恶行〃实况作了详细描述,使731部队的存在成为世人皆知”。《恶魔的饱食》一书在日本销售300万册,以其惊人的影响在日本民众面前揭开了731的黑幕。
森村诚一为此遭到了威胁和指责,有人劝解森村诚一不要冒政治风险,不如去写纯推理小说。
“一个作家应该关注社会问题,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追求人生真谛,这才是我的写作目的,是我生存的意义。……我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追踪战后731的足迹,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狂热的可怕和民族优越感的实质,不使此类错误重犯,在人类已经建立起来的和平基石上添上一块小小的石头。”森村诚一说。之后他和美国第一个揭露美日细菌武器交易的记者鲍威尔取得联系,获得了《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的翻译权,并继续写出《恶魔的饱食》(续)和《恶魔的饱食》(第三部)。
森村诚一的贡献是对日本公民进行了一次731部队的普及教育。这支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犯下极大罪恶的细菌部队,在战后销声匿迹地隐藏起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
从日本政府来讲,从战争结束的那一天起,就有意让这支部队隐匿起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为只有他们清楚,这支部队一旦为世人所知对日本政府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后果。
家永三郞,日本东京大家教授,日本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1945年受日本文部省之任编纂历史教科书《国家的历程》,1952年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教科书中,家永三郞写到了731部队。“日军在哈尔滨郊外设立了被称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用抓到的数千中国人和一些别国人做活人细菌实验并加以虐杀,这种残忍的勾当直到苏联参战才停止。”尽管记载是如此的简单而粗略,文部省也不允许在教科书里出现731部队。文部省对此的批语是“731写进教科书为时尚早,全文删掉。”
。。
追寻历史真相的人们(2)
另外,家永三郞被指责为“对民族爱得不够”,“把战争写得太阴暗,要写国民拼命支持战争的光辉形象”,要把“侵略”换成“武力进出”,修改多达290处。
家永三郞拍案而起,1965年6月12日将文部省告上法庭,诉其违宪。“审定制度违反了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精神”,并且审定给作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赔偿损害。
1966年,家永三郞的《新日本史》再审还是通不过,家永三郞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第二次诉讼。他要求法院必须澄清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侵略中国等八个历史问题。
“最近,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已经出笼登场,文部省站在肯定论的立场上妄图使战争光明化,并禁止我将战争写成黑暗的战争,给我的精神是沉痛的打击。在法治主义的名目下,国家本身违背宪法,这说明国家的无法状态。”家永三郞说,“我这样做是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最高利益。”
从1965年到1997年的长达三十二年的时间里,家永三郞面对的是强大的日本政府,面对的是日本否定侵略战争的势力和思潮。虽然他身为日本知名历史学者,但仍然势单力薄。为了历史的真相,他屡败屡诉。地方法院的一审败诉,二审败诉、三审败诉,家永三郞立即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是家永三郞在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对中国女性施暴这两点胜诉,家永三郞不服,再一次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修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日本侵略中国”、“日军暴行”等4处属于文部省滥用处理决定权,属于违法,赔偿家永三郞40万日元损失,但裁定文部省审定合法。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细菌战原告们走上了日本法庭,开始了又一桩跨世纪的马拉松式的为了历史真相的诉讼。这是历史的偶合,一个诉讼完结,另一个诉讼开始,但这一历史的偶合充满了象征意味。
32年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开庭,家永三郞已经从一个睿智的中年知识分子变成了八十三岁的老人。但三十二年来他始终站立在法庭上,以挑战的姿态面对强大的日本政府。在等到最终判决的时候,他已重病缠身。当他拄着拐杖出现在为他胜诉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有的人都起立为他长时间鼓掌。他说,他仍不满意这个判决,但他不可能第四次上诉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和精力了,但他决不会放弃战斗,直到生命的终结。
2002年8月27日,历时七年的中国细菌战诉讼败诉,之后的11月29日,八十九岁的家永三郞与世长辞。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为坚持历史真相而同日本政府斗争了四十载的史学家平静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中国的细菌战再诉讼又一次开庭。
中日双方战后半个世纪为了历史真相的再一次纠纷对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来说,并不能脱离干系。
1980年10月,美国记者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长篇报道《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第一个向美国人揭开了日美之间关于细菌武器的交易,以及在这种卑鄙的交易下美国替日本掩盖细菌战罪恶的事实。
美国记者鲍威尔是在中国上海长大的,他亲眼目睹过日军在宁波实施的细菌战。1945年他接管父亲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中国周报》。后因为《中国周报》上曾转载过新华社的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鲍威尔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受到长达七年的审讯。这件事反而促使他继续深入进行日本细菌战的研究,于是有了他的破冰之作《一段被隐瞒的历史》。文章发表后,美国著名电视调查节目《六十分钟》采访了他,这个节目在美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一下使鲍威尔所揭露的事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但这些只是一个开始。它还不足以让整个事件显露出来,也不足以让人们认识到其中的全部黑暗。因为这黑暗是彻底的,超出正常人想象的,就是所有人的想象都加起来,也不足以描绘完整的图景。
不只是王选、森正孝,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当听到“人体试验”、“人造鼠疫、霍乱、炭疽”的时候,都长时间地瞪大眼,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然后发出疑问: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美国人丹尼尔是1993年从BBC和NBC知道731部队的,他把他看到的新闻报道讲给周围人听,但没有人相信,人们说“太离奇了,不可能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见到,丹尼尔也不敢最终肯定,这样残忍的事真的有过。
“2002年我终于见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实例,这位妇女的脸烂掉了一半,生活完全毁掉了。” 丹尼尔说,“这么惊人的恶行,竟然六十多年无人提起,造恶者竟然没有一个受到惩罚,这是人们不相信的最主要原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王选,还原历史真相的未来人(1)
1995年,有三个义乌崇山村的农民,写信给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道歉和赔偿。“当时我弟弟拿了剪下的报道给我,一副非常郑重的样子,就像是说一件大事。”王选说,“看了报道,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崇山,我的家乡!”
王选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三个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反绑在树桩上,脚上戴着脚镣。中间的那个男孩只有二十来岁,剃过光头,头上长出青青而茁壮的小茬,整个脸饱满而健康,他的脸倾向镜头,正视镜头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好奇。和旁边两个垂头丧气的健壮的成年男人比较,他显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
王选看到这张照片就哭了,“在从东京加姬路的家里坐###的三个小时里,我脑子里不断出现那目光,这么健康的一个生命,就要拿去做活体实验!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王选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报纸上说到的两个日本人森正孝和松井英介,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崇山人,我有义务。只有我能把崇山话翻译成日语。”
1995年,王选找到了森正孝。
一个假日,森正孝和松井英介乘坐###来考察王选,“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历史的存在,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是历史的大规律轮回到了我身上。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
王选成了揭露会调查团的一名翻译。
王选和森正孝合在了一起,两股来自交战双方国家的、想知道历史真相的力量汇合在了一起。
来自日本、美国的揭露力量在逐渐强大,731和细菌战所包裹和封锁的铁甲在一点一点地剥蚀。但是,我们还看不到其核心的内容,因为它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国。实际的制造细菌战武器的地方,直接的受害者,直接的细菌武器攻击作战的证据,所有这一切必须到中国寻找。
而一说到中国,问题就来了。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为什么才刚刚过了半个世纪,历史就变得模糊不清?为什么中国人的追讨公平的行为会到现在才出现?为什么对中国人的侵害,中国人反而要到日本去打这场官司?”王选说,“1997年8月起,我随着国内来的细菌战、毒气战等受害幸存者,在日本从南跑到北,参加各地和平运动组织为他们举行的证言###,有数十次。日本人比较缄默,不太在公开场合发言,会场即兴的问题很少。到会的绝大多数又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思想观点立场都差不多,有点像是自己人给自己人上课。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地方被问了几次:‘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打官司?’”
这么问的人,还一定是圈外人。每当这时侯,主持会议或在场的日本和平运动人士似乎是觉得这么问不够友善或是有弦外之音,总是作为日本人先作出“正确”回答。比如说:我们日本人应该想的是我们自身的责任,不应该问中国人这样的问题。好心为我们挡了。但是善意并不能替代理性的思考。王选向记者讲了一段故事,故事中提问者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日本人想知道的,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想问的问题。
“有一回,在名古屋的一个###,有个年轻人坐在靠前的座位,一脸的思考,听得很认真,然后也问了这个问题。我看他不太高兴自己的问